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
Transcript of 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
-
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中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 1
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
中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
林佑貞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班博士候選人
摘要
尤金‧芭芭(Eugenio Barba)發現,不同文化中有成就的表演者之間都深藏
著展現舞台活力的秘密,亦即演員如何成為一種「在場」的形象,而這也是各種
表演技巧的根源。本文主要以芭芭提出的「劇場人類學」以及他和歐丁劇團(Odin
Theatre)所創造的「身體行動方法」(method of physical actions, MPA)為視角,
探究印尼爪哇傳統表演藝術的秘藝:透過《貝多優》的「身體行動方法」,訓練
表演者∕個人經歷將日常意識轉化到非日常意識狀態的過程。這不僅是完美演繹
這門藝術的關鍵,也可作為個人朝向靈性成長的不二法門。
本文第一部分先簡要爬梳《貝多優》的發展歷史,再定義「身體行動方法」,
* 本文初稿曾以〈印度尼西亞傳統表演藝術的秘藝: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作為一種身體行動方法〉為題,於上海戲劇學院主辦之「第二十屆人類表演學國際大會」以簡報方式宣
讀,2014 年 7 月 6 日。在此感謝《藝術評論》兩位匿名審委的寶貴建議,筆者儘量修正,但因囿於篇幅,期許未來能另文續論。
藝術評論第二十八期 頁 1-34(民國一○四年),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ARTS REVIEW, NO. 28, pp. 1-34 (2015)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ISSN: 1015-624 DOI: 10.3966/101562402015010028001
-
2 林佑貞
第二部分著墨爪哇傳統表演藝術對於意識轉化的詮釋,第三部分探討《貝多優》
作為一種「身體行動方法」的實踐面向,希冀能提供表演者∕個人一個可行的、
有效的自我訓練模式。
關鍵字:在場、貝多優、身體行動方法、意識轉化、劇場人類學
收稿日期:2014.9.30;通過日期:2014.12.08
-
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中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 3
聆聽音樂或欣賞舞蹈時,都牽涉到我們的肌肉,無論多麼地微小,無
論我們的身體多麼不動如山。當我們聆賞音樂,我們用身體創作音樂;當
我們觀看一支舞蹈,我們會隨之起舞。音樂和舞蹈影響我們整個神經系
統,不單只是身體或心智而已。難怪音樂和舞蹈在過去和今日都廣泛地被
應用,成為一種轉化的乘具。(Becker 1993, 22)
一、前言
美國著名民族音樂學者貝克(Judith Becker)於 Deep Listener: Music, Emotion
and Trancing 一書中強調,許多不同文化的民族各自發展出可行的身體技術用來
幫助個人∕群體「出神」(trance)或者經歷「意識的轉化」(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sciousness)。進入南亞、東南亞民族音樂的研究領域和田野調查長達數十載
的貝克,眼見表演者在演出的過程中經常進入到出神狀態,促使她不得不正視一
個事實,亦即一直以來受西方文化視為病理學領域的意識轉換或「非日常的」變
異狀態(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必須重新予以審視和檢討。她結合腦神
經科學去分析「出神者」的生理反應,主張意識轉化可視為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一
種適應性策略,對世上任何的社群關係都至關重大(Gold and Brinner 2007,
632)。換言之,人類面對生活種種而發展出來的「動作系統」,展現著強大的功
能,足以成為安身立命的乘具(vehicle)。
印尼爪哇民族從「內在性」(immanence)發展出追求近神的密契經驗,最
終達到「神人合一」的境界,這樣的觀念,早已深入日常生活的實踐,且充分展
現在傳統表演藝術的發展中。特定的《貝多優》舞蹈和甘美朗(gamelan)(樂譜、
樂器和音樂)同樣被爪哇民族視為自古流傳,擁有神聖之力的宮廷遺產「蒲薩卡」
(pusaka),它能夠彰顯皇室的威望,為社稷帶來長治久安的富足與繁榮,更可
作為表演者(舞者、演奏者、吟唱者)和聆賞者經驗意識轉化,通往內心澄明、
和諧境界的途徑。
-
4 林佑貞
1960 年代以降,無論是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對爪哇宗教的研
究,或是民族音樂學者貝克以甘美朗為研究主題,或是舞蹈民族誌研究者布列可
(Clara Brakel-Papenhuijzen)對中爪哇宮廷舞蹈《貝多優》的分析比較,或是社
會學者休斯富蘭(Felicia Hughes-Freeland)探討傳統表演藝術裡的女性角色與權
力關係等,他們或多或少都注意到爪哇民族著重精神修練的文化底蘊。然而,這
些研究鮮少觸及表演者精神淬鍊的實踐過程,抑或揭露精神修練與在展演中達到
最佳表演狀態(也就是演員的「在場」“presence”)間的關聯性。換言之,究竟
表演者如何能夠展現活生生的舞台魅力,同時又意味著個人精神修練的成果?個
別的表演者∕教師如何訓練自己和學生,經歷「意識轉化」的過程,進入最佳的
表演狀態?
芭芭(Eugenio Barba)與歐丁劇團(Odin Theatre)歷經半世紀的追尋和實
踐,不斷地建造、打磨屬於他們自己的小傳統,幫助表演者展現活脫的存有狀態,
直接吸引觀眾的注意力。芭芭與來自不同傳統的一些專家們通力合作,探討戲劇
行為的某些共同原則(Schechner 1998, 19),他發現,不同文化中有成就的表演
者都深藏著展現舞台活力(scenic bios)的秘密,即演員如何成為一種「在場」
(presence)的形象(梁燕麗 2005,80),而這也成為他和歐丁劇團念茲在茲的
劇場∕生活準則。本文將根據芭芭所提出的劇場人類學以及他和歐丁劇團所創造
的「身體行動方法」(method of physical actions, MPA,待下節詳細定義),探
究印尼中爪哇表演藝術的秘藝。透過《貝多優》的「身體行動方法」,訓練表演
者∕個人歷經將日常意識轉化到非日常意識狀態的過程,而這不僅是完美演譯這
門藝術的關鍵,也可作為個人朝向靈性成長的不二法門。
本文第一部分將簡要爬梳《貝多優》的發展歷史,再定義身體行動方法,第
二部分著墨爪哇表演藝術對於意識轉化的詮釋,第三部分以《貝多優》為例,探
討其實踐面向。希冀能提供一個得以跨越東方∕西方、傳統∕現代、藝術∕生活
對立二分的途徑,提供表演者∕個人一個有效的自我訓練模式。
-
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中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 5
二、《貝多優》的過去與現在
貝多優(bedhaya)同時意指舞者與舞蹈,是印尼中爪哇女性舞蹈類型之一。
最古老的《貝多優》起源於何時,已不可考。相傳第一批《貝多優》舞者是由七
顆從天而降的寶石幻化而成,圍繞著天池進行了《貝多優》舞蹈。天上的神祇們
為了能盡興地觀賞舞蹈又不失天神的尊榮,紛紛長出許多眼睛,例如:印度教梵
天神(Sang Hyang Brahma)就長出了四隻眼睛,雷神(Sang Hyang Éndra)更長
出了百隻眼。1
約於十三世紀滿者伯夷王朝(Majapahit, 1293-1478)時期,爪哇宮廷裡即出
現了許多女性舞蹈,《貝多優》因此得以在此基礎上順勢發展(曾薇霖 2010,23;
Sumarsam 1995, 20, 54)。1755 年,伊斯蘭馬塔蘭王朝(Mataram)在殖民國荷蘭
的離間下,簽訂《吉揚帝條約》(Perjanjian Giyanti),正式分裂為日惹(Yogyakarta)
和梭羅(Surakarta)兩皇室共治的局面。相較於荷蘭人的西方基督教傳統,《貝
多優》不僅作為爪哇民族認同的指標,也是日惹和梭羅皇室爭奪伊斯蘭馬塔蘭王
朝正統繼承者的關鍵。兩宮廷各自擁有並發展獨特的《貝多優》舞碼,目前史料
上記載最神聖的儀式舞蹈《貝多優》,分別指稱日惹宮廷所擁有的《貝多優瑟曼》
(Bedhaya Semang)和梭羅宮廷的《貝多優卡達望》(Bedhaya Ketawang)。相傳
《貝多優瑟曼》和《貝多優卡達望》都是由成就馬塔蘭王朝盛世的蘇丹阿貢
(Sultan Agung of Mataram, 1613-1645)所創發,靈感來自於蘇丹阿貢或是他的
祖父新納巴蒂(Senapati)獨自進行祈禱、禪修時,與南海女神琪督皇后(Kangjeng
Ratu Kidul)相遇、相戀、締結婚約並分離的故事(Hostetler 1982, 129-133;
1 詳細故事可參考 Serat Weda Pradangga(1979)以及 Pustaka Raja. Serat Weda Pradangga(1906),前者是一本詳細記錄甘美朗樂團傳統的專書,Pustaka Raja 則是由著名的宮廷詩人朗喀瓦西塔(Raden Nagabehi Ranggawarsita)所撰寫的百科全書,基本上是民間故事與傳說的集合。
-
6 林佑貞
Tirtaamidjaja 1967, 32)。2
學習《貝多優》原屬於王公貴族(公主、王子)的特權,強調可作為培養健
全體魄與提升靈性的乘具,若是展演,往往也只在宮廷重要的儀式慶典上。十九
世紀中葉開始至二十世紀初,爪哇成為新開放墾殖的殖民地,許多的荷蘭人和歐
洲人紛紛到來,宮廷為因應眾多的外國賓客來訪,逐漸形成一波宮廷舞劇(dance
drama)表演的文藝復興潮(Parto 2001)。日惹宮廷於 1918 年率先開放民間教授、
學習和展演宮廷表演藝術,《貝多優》於是逐漸脫離儀式、宗教、封建政治的脈
絡,開啟了在民間蓬勃發展的契機。至今,無論是老一輩或中生代的舞者∕教師,
身處民間或宮廷,創作活力仍歷久不衰。經由個人的自由創作、私人委託或受藝
術節邀約而創作的《貝多優》,數量相當可觀。3
《貝多優》由九位舞者 4 演出,甘美朗樂團伴奏,加上爪哇古典詩詞吟唱。
若是屬於宮廷神聖的《貝多優》,則需要準備種類繁多的祭品,且需舉辦一連串
的祭祀活動,演出的場地為爪哇傳統開放式建築「演藝亭」(pendhapa)。九位舞
者以爪哇新娘的裝扮,5 先用長條蠟染布纏繞上身,再以艮奔衣(kemben)包覆, 2 由於口傳的關係,造成歷史文件闕如,以致起源說的版本眾多,但大致不出這兩個說法:蘇丹阿貢深夜獨自祈禱、冥思,回想起印度教時期的七位仙女舞蹈,進而受到啟發
而創作,並且獲得九大聖人之一的蘇南卡里嘉嘎(Sunan Kalijaga)的祝禱與協助而完成音樂的部分,再由南海女神琪督皇后親臨指導舞蹈的成形。或如文中所述,關於蘇丹阿貢
(或他的祖父新納巴蒂)與南海女神的愛情故事。貝克於書中分別爬梳以印度教、伊斯蘭
教和與泛靈信仰有關的起源傳說和神話故事(Becker 1993: 119-124)。亦可參閱布列可的分析(Brakel-Papenhuijzen 1992, 32-46)。
3 爪哇的表演藝術對於創作的概念與西方不盡相同,爪哇採用 “mutrani” 這個字,指透過模仿某一特定的典範(如有《貝多優》之母稱譽的《貝多優卡達望》)所進行的更新或再
創造(Brakel 1992, 82)。根據蘇蒂雅老師(Siti Sutiyah)的統計,她的先生薩斯(Rama Sas)也是日惹古典舞蹈大師,生前除了其他類型的舞蹈外,約創作了 150 支《貝多優》(蘇蒂雅,個人訪談,2013 年 9 月 19 日)。
4 印度教∕佛教馬塔蘭王朝時期,《貝多優》是由七位舞者模仿天上七位仙女的演出,但到了伊斯蘭馬塔蘭,也就是從蘇丹阿貢開始,《貝多優》開始由九位舞者擔綱。
5 根據薩頓(R. Anderson Sutton)於“Semang and Seblang: Thoughts on Music, Dance, and the Sacred in Central and East Java”一文的註釋,第六位蘇丹王在位時期(1855-1877,日惹的
-
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中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 7
形如西方流行的馬甲胸衣,露出肩、頸和雙臂。下身穿著由凱茵(kain)蠟染布,
一圈圈環繞而成的及地長裙,腰繫棉布長巾(sampur)。舞者隨著甘美朗樂音緩
緩地擺動手臂,雙膝向外微蹲不時轉換重心,變換各種動作與隊形(如圖 1)。6
圖 1 2002 年 10 月 7 日於日惹皇宮演出重建的《貝多優瑟曼》7
從《貝多優》的起源說可以清楚地看到爪哇人賦予它的重責大任:Serat Weda
Pradangga 一書明文闡述《貝多優》舞蹈的目的,除了作為驅邪、增進國家團結
與繁榮的工具外,還具備以下三個關鍵的目的(Becker 1993, 117-119; Brakel 1992,
38-41):
《貝多優》舞者確實如《貝多優卡達望》舞者一樣,一律以爪哇新娘裝扮演出。然而,二
十世紀初、甚至今日的日惹《貝多優》舞者裝扮已經改穿絲絨背心,頭冠邊綴一根長羽
毛。就筆者在日惹和梭羅的觀察,確實如此,只有少數較神聖的《貝多優》演出時,舞者
仍是新娘裝扮,例如:本文中提到的《貝多優卡達望》和《貝多優瑟曼》(如附圖 1)。 6 隊形與其意義於本文後半有詳細的分析。 7 截圖來源為帝亞(Alex Dea)所拍攝錄製的影片。
-
8 林佑貞
(一)獲取爪哇文化的知識,尤其是關於透過《貝多優》舞蹈引導朝向神秘的
合一之境(samadi)。8
(二)學習戰鬥列陣的知識,像是鳥的俯衝、飛翔的鷹,陰晴圓缺的月、鐵餅
列陣等。
(三)習得富含深奧、崇高意義的樂曲知識。
學習《貝多優》因此成為瞭解和實踐爪哇文化的管道,並作為皇室成員強健
體魄的軍事訓練,但其最終目的則在達到如古典舞蹈大師薩斯(Rama Sas
1929-1996)所言,透過《貝多優》這猶如禪修(meditation)的舞蹈過程,淨化
心靈並上達天聽(Sas 1979, 1)。
三、身體行動方法:劇場裡∕外意識轉化的技術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以下簡稱史氏)於 1906 年之後,即致力於培養演員的
「創意情緒」,認為這是通往人類心靈的技術、一種內在的精神技術,唯有這一
點才是劇場藝術的真正基礎(Stanislavsky 2006, 343)。史氏堅信演員訓練最終的
目的,就是要進入超意識,並提升人的靈魂(White 2006, 86-87)。9 在史氏的劇
場實驗最後階段(1933 年之後),致力於發展出一套「身體行動方法」(method of
physical actions, MPA)以幫助演員更有效地進入「創意狀態」,也就是:「不再依
賴『情感記憶』來進入角色的感情世界,而是演員只要仔細地建構角色在該情境
中的身體、聲音、走位的各個細節,然後很仔細地、合乎邏輯地執行這些行動即
可活出角色來」(鍾明德 2013,123)。換言之,透過有意識的訓練(即 MPA), 8 貝克將爪哇原文中的 “samadi” 譯為禪修 (“meditation”),布列可則翻譯成神秘的合一
(mystical union)即宗教上的禪定(religious concentration)。本文則就不同脈絡翻譯之。 9 根據懷特(R. Andrew White)的研究指出,史氏的劇場實驗和研究,早在 1906 年即運用許多瑜珈(Yoga)的練習來訓練演員的專注力(concentration),以及東方玄學的教義(Oriental metaphysics)引導演員在舞台上經驗(to live)精神生活,並且能夠瞭解精神生活諸多的奇妙面向。
-
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中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 9
演員就能進入活生生的、有機的、自發的、有創造力的最佳表演狀態(超意識,
superconsciousness)。
葛羅托斯基(以下簡稱葛氏)雖不曾親自師事史氏,卻不諱言他一生在劇場
內∕外的實驗深深受惠於這位大師的方法和精神。葛氏早在十三排劇坊時期即開
始進行精神性的探索。10 待宣布離開劇場之後,他更專注於「藝乘」(art as vehicle)
的研究與實踐,欲創造一種表演者的精神性修練方法。葛氏在藝乘時期(1986
~1999 年)11 將 MPA 比喻為「打造一架頂天立地的雅各天梯」,其主要的作法
是利用古老的震動歌曲發展成為行動(action,即 score 或 structure),經由精準
地執行,行者的能量就開始「垂直升降」(鍾明德 2007,81-83)。葛氏在這個時
期的目的是要發展「我─我」(I-I)的覺性(鍾明德 2013,122)。
芭芭的「劇場人類學研究」(theatre anthropology)是一連串對表演過程的考
察、質詢和探索。芭芭對於劇場前輩們的智慧與實踐如數家珍,總是大方承認他
與這些先進之間有著縱向的既傳承又挑戰的關係(Barba 1995, 150)。尤其葛氏
與芭芭亦師亦友,從歐丁劇團的演員訓練和《劇場人類學辭典》(A Dictionary of
Theatre Anthropology)一書中,都可清楚看出葛氏對他深厚的影響。芭芭與歐丁
劇團「族人」12 歷經超越半世紀的錘鍊,在世界的邊緣過著公社般的生活,至今
仍持續並肩走在劇場的大道上,打造屬於他們自己的「身體行動方法」。芭芭讓
劇場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梁燕麗 2005,51),劇場不是途徑,它是生命不斷更新、
創造的軌跡。藝術創作即是生命的課題,是個人如何安身立命的奮鬥過程。綜上
所述,歷史性地來說,MPA 指史氏、葛氏和芭芭致力找出讓表演者有系統地、
10 參見鍾明德(2007,105)的《OM 泛唱》;鍾明德(2012,9)於〈這是種出神的技術〉
一文亦點出「一直到 1977 年前後,葛氏才較公開地進行他個人的精神性探索」,詳見註腳 8。
11 鍾明德(2013,122)以表格陳列葛氏在四大時期的「精神探索目標」與「身體行動方法」,讓讀者對葛氏一生的實驗工作有一個清晰的輪廓。
12 芭芭經常以部族(tribe), 夥伴(companion)(Barba 1995, 147)、同胞(compatriot)(Barba 1995, 149)來稱呼歐丁劇團的演員們或劇場人類學學校的參與者。
-
10 林佑貞
重複地達到或回到身心合一的創意狀態的秘訣,雖各自成一家,但大同小異,可
視為同一宗派。
鍾明德於 2013 年甫出版的《藝乘三部曲:覺性如何圓滿?》一書中,詳盡
地分析歸納了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與葛羅托斯基的藝術創作方法,並根據他個人十
幾年來分別對於臺灣賽夏族矮靈祭、布農族的八部合音、白沙屯媽祖徒步進香與
泛唱,以及正念動中禪等的研究與實踐得出的成果,同時採用史氏晚期劇場實驗
的用語 MPA 整理出以下的定義:
狹義的 MPA 為:
表演者藉由一套學來的或自行建構的表演程式之適當的執行,而進入
最佳表演狀態的方法。
廣義的 MPA 指:
藉由一套身體行動程式之適當的執行而產生有機的身心狀態(如「出
神」、「動即靜」、「覺性」等)的方法。13
根據以上的定義,若經由適當地執行一個表演程式,就能進入到最佳表演狀
態,那麼在執行程式的過程裡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有機的身心狀態指的又是什
麼?史氏會說,那是一種進入創意的、超意識的狀態,葛氏說是回到「動即靜」
或是覺性圓滿( total awareness),芭芭認為是存有(presence)、前表現性
(pre-expressivity)、舞台活力(scenic bios)、能量(energy)等,爪哇表演者則
以出神(trance)、充滿“rasa”、半睡半醒的意識狀態、天人合一等來表達(暫待
下節分析),這些都可以看作是一連串將日常意識轉化為超日常意識的展現,也
就是經歷「意識的轉化」(transformation of consciousness)。簡言之,MPA 是一
13 此定義摘自鍾明德(2014)〈一個萬人參與演出的溯源劇場〉一文,然其詳盡的分析與推
論過程可參考《藝乘三部曲:覺性如何圓滿?》。
-
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中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 11
套幫助執行者達到意識轉化的技術。
那麼,達到意識的轉化為什麼重要?貝克在 Deep Listener: Music, Emotion
and Trancing 一書中重新看待「出神」(trance)。她指出,我們不應該再將非日
常的意識狀態歸類為病理學的範疇,應該正視一個事實:「在世界其他大多數的
文化中,出神是被接受,甚至被認為是個人與社會幸福安康的必要條件」(Gold
and Brinner 2007, 678-679)。因此,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從表演(狹義)與個
人∕表演者精神性探索(廣義),或說整個社會的幸福安康兩個層面著手。就表
演而言,只有演員進入活生生的、有機的、具創造力的表演狀態,演員才能展現
出「在場」(presence)的舞台魅力。這才是史氏一再強調的讓觀眾體驗真實的劇
場,亦如葛氏的演員奇斯拉克(Ryszard Cieslak)所展現的「圓滿行動」,或是芭
芭所稱的「跳舞的劇場」。就個人而言,廣義地來說,是透過一套具體可行的身
體技術,作為精神性探索的計畫,以達到內在的和諧與安寧。
而應該如何適當地執行?演員訓練一直是芭芭所關切的重點。芭芭指出,人
類運用相似的原則發展出不同的表演。他不以地域來區分東、西方的表演者,而
是將表演者劃分為北極和南極。北極表演者有芭蕾、亞洲古典戲劇、現代舞、歌
劇和啞劇(顯然,爪哇傳統藝術表演者屬於此類);南極表演者則不屬於這樣以
細節化風格代碼來界定的表演類型(Barba 1995, 13-14)。下一節,本文將探究
爪哇的表演藝術 MPA,以《貝多優》為例,佐以芭芭劇場人類學的研究,檢視
其作為演員訓練和自我靈性成長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在進入爪哇以前,以下簡要列表(如表 1)比較兩種 MPA。14
14 此為參考鍾明德(2014,6)〈一個萬人參與演出的「溯源劇場」〉一文中的表格格式,
再由本文作者完成內容。
-
12 林佑貞
表 1 兩種 MPA 比較 目 的 過 程 方 法 戒 律 原 理 發 現
芭芭與歐
丁劇團
會跳舞的劇
場、真實行
動、身心合
一
演員的準備
打磨程式
再 三 重
複,達到舞
台能量(轉
化)
真實行動,
即興,發展
程 式 (score)
與 潛 程 式
(subscore)
耐心、內在
脈動、孤獨
( 長 時 間
操練、工作
自己)
程式與潛程式
整合互動可以
使演員蛻變、
展現舞台活力
1979
爪哇宮廷
表演藝術
《 貝 多
優》
舞我合一的
圓滿實現、
與 神 共 舞
( 上 達 天
聽)、身心靈
和諧、覺性
精熟外顯動
作,同時進
行內在靈性
的訓練,反
覆練習以達
到意識轉化
精熟程式化
的 舞 蹈 動
作、舞譜、
音樂等,生
活修行:禪
修
齋戒、遵守
禁忌、祈禱
祭拜
重複、規律地
練習舞蹈,不
以 表 演 為 目
的 , 剝 除 慾
望,淨空自己
十七世紀
中葉
四、感知(Rasa):表演者的存在感或活生生的演出?
劇場人類學假設「前置表達(pre-expressivity)是各種表演技巧的根本」(Barba
2012, 218)。芭芭勉強地予以區分,認為前置表達屬於執行層面;如何「做」,在
這做的過程中能夠強化演員的舞台生命力,抓住觀眾的注意力。換言之,它的目
標就是能量、存在感、舞台生命力(Barba 2012, 218)。芭芭在《劇場人類學辭
典》與《紙獨木舟》(The Paper Canoe)中經常交互使用幾個不同的語詞和描述:
舞台活力(scenic bios)、存有(presence)、舞台存在感(scenic presence)、能量
(energy)、有機性(organicity),附身、轉化、狂喜等,細究這些看似相異的表
達,其實都在說明同一件事——演員的「存在感」(presence)。芭芭這樣描述「存
-
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中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 13
在感」:「從靈魂散發出來的極品,向四方擴散,波及一切。演員如果覺察到自己
的存在感,就敢表達他的感覺,因此做出合宜的行動,毋須努力就能讓觀眾傾聽
他」(Barba 2012, 210)。然而,即便有了這樣的定義,「存在感」依舊是那言語
無可觸及的「什麼」,唯一的途徑似乎只能經由演員和觀眾親身體驗來證明。
2013 年 9 月,筆者於印尼中爪哇梭羅的芒辜納嘎蘭偏宮(Mangkunegaran)
邂逅了一次特殊的練習經驗,它很快就成為驅使筆者探究當地表演者理解與詮釋
「存在感」的線索。每週三晚間,芒辜納嘎蘭偏宮都有例行的甘美朗和古典舞蹈
練習,免費開放給一般大眾參加,也歡迎外國人士的加入。整個演藝亭經常像個
聯合國,不同膚色、國籍的男、女,圍上凱茵裙,腰繫棉布長巾,共聚一堂,開
始二至三個小時音樂與舞蹈的學習。這裡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愈是資深、成熟
的舞者,自然就排在隊伍的最前方,其他學員們按照自己的程度往後方排去,如
此,後面的學員在不干擾前者的情況下,即可跟隨、模仿前者的舞步(如圖 2)。
甘美朗的樂師們約有十人,七點前即開始演奏。各國的舞者(學生)
們紛紛換裝,陸續約有二十多名加入練習。我走到中間偏後的位置,排在
一位大約 60 歲上下的女士後方。心想,她排這麼後面,我應該可以盡量跟
上。沒想到,音樂一下,她的身體隨即如一支活動的畫筆,一個蹲地
(jengkeng),一個起身(tanjak),一個手部挑甩長巾的動作(kebyok),溫
柔中帶著果敢的力道,渾然天成,就在空中舞出一幅抽象畫。我無法將視
線從她身上移開,自己則愈跳愈激動,待音樂一停止,我索性離開練習隊
伍,席地坐在樑柱旁觀看。第二支舞一開始,甘美朗的跳躍聲如水滴般落
在她的身上,濺起點點亮光,我的所有感官又被她的舞動深深吸引。演藝
亭裡好像只剩下我和她,更像是只有跳躍進我耳裡的聲響和她舞動的線
條。(田野筆記,2013 年 9 月 11 日)
-
14 林佑貞
圖 2 2013 年 9 月 11 日於芒辜納嘎蘭偏宮西面練習場地
當晚練習結束,筆者坐上三輪車迎著涼風回到住處,迫不及待地將剛剛發生
的點滴記錄下來。接著,有好幾天的時間,當晚的情形時時浮現,心中一直有個
疑問縈繞不去:我看到、感受到的是不是就是芭芭所謂的演員活生生的存在感?
之後,有一次與梭羅藝術大學古典舞蹈老師碧水(Bambang Besur)見面,筆者
窮盡所能地描述當晚的見聞,向他提出疑問,他只幽幽說道,那就是 “rasa”,還
順便給了筆者那位舞者的姓名。15
那次的經驗,以當地人的用語,就是感受到 “rasa”,16 或說從表演者身上看
15 即便他當晚並不在場,僅靠筆者的描述,就正確地猜到是任教於梭羅藝術大學舞蹈系的
魯西尼老師(Ibu Rusini)。 16 “rasa”在印度的宗教、文化脈絡下,是個相當複雜的語詞、概念、甚至是體驗,因此在翻
譯上,很難找到一個固定、確切的語詞來代表它。蘇子中於〈Rasa:表演藝術的情感滋味〉一文中,也坦承其翻譯上的難題,然其對“rasa”在梵語表演藝術經典論著《舞論》裡的建構和定義有詳盡的爬梳,相當值得參閱。但本文仍暫時讓中文翻譯從缺,並著重在
爪哇的表演藝術文化脈絡下來討論“rasa”。
-
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中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 15
到“rasa”?是舞者身心合一的清明境界?表演者展現出舞台的活力正是吸引我這
個觀眾目不轉睛的原因嗎?為了解答這些問題,我得先探究爪哇人所認為的
“rasa”在不同脈絡下的意義。
爪哇菁英階層(prijaji)的宗教生活主要關注三個焦點:生活禮節(etiquette)、
藝術(art)以及實踐神祕主義(mystical practice)(Geertz 1965, 238)。這三者可
以由從印度借來的概念 “rasa”,連結起來理解。在爪哇的運用裡,“rasa” 字面上
的意思有兩層:感覺(feeling)和意義(meaning)。根據紀爾茲的解釋,就第一
層意思而言,“rasa” 指從外在感官與內在情感產生的感覺。第二層「意義」的解
釋,又分為:(一) “rasa” 指外顯行為(lair)事件的意義(聲響、形狀、姿態的外
顯行為世界);(二)從較神秘的「靈性成長」(batin)來說,“rasa” 指的是流變的
內在生活世界(Geertz 1965, 238-239)。
除了紀爾茲奮力地想要說清楚“rasa”外,貝克以她最熟悉的表演藝術為例來
定義“rasa”。她指出爪哇音樂家用“rasa”這個名詞(情感、味道、本質等)去包含
許多藉由一首曲子、一支舞蹈、一首歌或一首詩傳達出來的意義、感覺、意圖和
想法,“rasa”還具備一個強烈的宗教意涵,亦即指由一個藝術事件所激發出的超
凡經驗,超出個人自我世界的合一境界(Becker 1993, 5)。因此,文前提及的魯
希尼女士充滿“rasa”的狀態,按照爪哇的美學標準:她藉由舞蹈,不但傳達了內
在情感和意圖、舞蹈蘊含的意義,或可以說她「出神」了。
“rasa”猶如「存有」、「能量」、「前置表達」般,捉摸不定,有時又像突然浮
現的一股動能。懷思(Sarah Weiss)試圖說明爪哇人認定一個有效的、使得表演
成立(以甘美朗演出為例)的判別標準:
一個成功的表演能以至少兩個不同的方式予以描述及達成:表演者能
夠將作品活生生地展現(bring the piece to life),他們能夠發掘、掌握並實
現作品的內在生命,或者他們能夠為作品所填滿(filled-up),體現這個作
品(embody the piece)。無論是主動地掌握作品的內在生命,或是被動地為
-
16 林佑貞
作品所充盈,表演者都被描述為彷彿他或她如同一只器皿,只有進入或透
過這只器皿,能量和力量才因而湧現。這種具現作品或作品的體現,歷經
嚴酷地操練,透過極度地專注力(concentration),讓表演的 “rasa”進入且
從表演者流瀉而出。(Weiss 2003, 42-43)
不論是表演者將作品活生生地展現出來,或是為作品所填滿,都在展現表演
者與作品合而為一的境界,並使彼此充滿生氣與活力。爪哇的表演美學觀點中,
經常出現以下超越二元對立的幾組象徵:心靈與身體、神與人、偶與操偶師、匕
首與刀鞘、面具與舞者,以及舞蹈與舞者等,以兩者無從區分彼此的合一狀態(如
出現在觀眾眼前的到底是戴上面具的角色還是表演者?是流動的線條還是舞
者?那入鞘的短劍是鞘還是劍?),詮釋它們彼此依存,互相充滿能量、彼此完
成的關係。已故日惹宮廷的表演者∕教師蘇哈托(Ben Suharto)指出,若以舞蹈
和舞者而言,表演者必須在過程中完全付出自己。先淨空自己(empty yourself),
剝除所有的慾望,然後才能讓舞蹈充滿自己,同時讓舞蹈自然流露出來,當然也
才有機會讓意識轉化發生(Suharto 1990, 25)。一場演出最高、最完美的展現莫
過於此。然而,這裡需要注意的是一個看似矛盾的修辭,當舞者與舞蹈合一時,
表面上舞者的個人特質消失了。其實正好相反,也就是在合一的瞬間,舞蹈成為
表演者內在精神的表達,即從他的舞蹈可以感受到其內在精神修練的程度與質
地。個人最內在的光輝的「表達」,並不能受自我意識的控制而達到,而是在舞
蹈的過程,也就是合一的過程中,自然展現。
另一方面,由於表演者(器皿)具備精湛的肢體技巧,並掌握這門藝術及其
信仰相關的知識,灌以全然的專注力,“rasa”會進入並且從表演者流瀉而出,因
此可以得出這樣的解釋:“rasa”也代表一股力量或能量,經由表演者的身心磨練
與努力,像電流般能夠貫穿表演者。
-
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中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 17
五、最佳表演狀態:充滿“rasa"、出神、狂喜
每種劇場傳統都有自己的特殊詞彙來描述演員的表演在觀眾眼中是
否成立。「成立」有很多不同的名字:西方最常用的辭彙是「能量∕生命
或更簡單的「演員的存在感」。亞洲劇場傳統則用到其他概念,例如:印
度的呼吸能量或力量,日本的腰力、氣合和幽玄,巴里島的查克拉或脈
輪、塔蘇和巴幽,以及中國的功夫。(Barba 2010, 72)
經由在中爪哇日惹和梭羅兩地的田野調查訪談,筆者發現表演者經常運用
「出神」(trance)、「狂喜」(ecstasy)等字眼來描述或強調舞蹈過程中所體驗到
那不可言喻的經驗。17 過去曾經連續三年(1986~1988 年)在梭羅皇宮擔任《貝
多優卡達望》舞者的藝術大學舞蹈老師瑟蒂優希(Sri Setyoasih)談到,她從擔
任舞者至目前(2013 年 9 月)唯二進入到出神狀態的經驗:
那支舞蹈(指《貝多優卡達望》)歷時一小時又四十五分鐘,通常舞者
會進入出神狀態(trance)。我曾有一次這樣的經驗。舞蹈的過程感覺很輕
盈、舒服。我還是知道自己在哪裡。動作非常令人愉悅。我曾經經歷過出
神兩次,一次是跳《貝多優卡達望》,一次是在 Loji 跳斯林碧桑歐巴蒂(Srimpi
Sangopati)。那裡焚燒著線香,而且整個空間、環境也有幫助,所以我就出
神了。感覺就像時空錯置,我自己獨自一人,但又不是。18(瑟蒂優希,個
人訪談,2013 年 9 月 25 日) 17 從印尼受西方勢力(尤受荷蘭達 350 年的殖民)長期影響的歷史事實,加上有許多表演者
和研究者也曾經至外國,尤其美國,以文化交流的方式於當地攻讀碩、博士學位,並同
時任教於大學或相關教育機構,因此權宜上,為了避免溝通上的歧異,面對外國人或是
不同文化的研究者,當地人有極大的可能傾向運用英語的詞彙和意涵,去解釋那難懂的
自我感知的經驗世界。 18 文中引用的田野訪談原以印尼文進行、記錄,再由本文作者翻譯成中文。粗體為作者強調。
-
18 林佑貞
瑟蒂優希女士所謂的出神:感覺輕盈、舒服、愉悅,覺知自己的一舉一動。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經驗出神,就像瑟蒂優希女士說的,和她一起舞蹈的朋
友們就沒有這樣的經驗(瑟蒂優希,個人訪談,2013 年 9 月 25 日)。
再對照另一位舞蹈大師對於進入「最佳表演狀態」的說法可以發現,無論是
“rasa”、出神、狂喜,或是半失意識的轉化現象,都在盡可能地闡明表演者呈現
活生生的舞台魅力的關鍵。已故印尼古典舞蹈大師蘇立優布朗托(G.B.P.H.
Suryobrongto)(1914~1985 年)是日惹蘇丹王哈孟庫布瓦納八世(1880-1939)
的兒子,同時也是優秀的傳統宮廷舞劇表演者。他於 1970 年代為了能在歐洲巡
迴演出時,向西方觀眾解釋爪哇古典表演藝術的精髓,提出了「日惹表演理論」
(Jogèd Mataram)。19 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明言,表演過程中,表演者是處於半覺
知(sadar)半失意識(tak sadar)的狀態,並非進入出神(trance)而完全失去
自我控制(Suharto 1990, 24; Suryobrongto 1981, 93)。表演者進入到一個非日常
的意識層次,在不完全失去意識的情況下,仍然可以覺察自己的動作與其他舞者
的互動關係。20 蘇立優布朗托曾寫道:當扮演一個特定角色時,訓練有素的舞者
應該摒除日常個人的覺知(awareness),並且進入一種「全神貫注」( total
concentration)的狀態來表演,「事實上,是處於一種狂喜狀態(ecastasy),因此
他整個心志只集中在舞台上所發生的一切,別無他物」(轉引自 Brakel-
Papenhuijzen 1995, 18)。可見,瑟蒂優希所說的出神經驗看來較為接近以上的說
法,只是蘇立優布朗托使用狂喜與中間狀態:半覺知半失意識的描述方式。總之,
19 Jogèd Mataram 這個詞直譯為馬塔蘭(王朝)的舞蹈,已經被拿來特別指「日惹舞蹈哲
學」(Yogyakarta dance philosophies),而不代表舞蹈的活動本身(Brakel-Papenhuijzen 1995, 3)。西方著名的印尼表演藝術研究者 Hughes-Freeland(2008,184)更直接將 Jogèd Mataram 稱為「爪哇的表演理論」。詳盡的分析請參閱林佑貞(2012)〈貝多優大師們的舞蹈生活哲學:印尼傳統表演理論初探〉。
20 這裡的「出神」,可以簡略地分為兩種:一是出神者完全失去意識,渾然不知自己身在何處,所為何事,回復意識時對於之前發生的事完全沒印象,例如:附身等(Becker 2004, 43)。另一種則是達到意識轉化,但仍然有一個旁觀的我清楚地覺察自我和周遭的一舉一動。文中爪哇舞者所描述的出神,明顯屬於後者。
-
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中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 19
當表演者專注於當下,覺知每一個動作,意識的轉化過程就發生了,表演者即進
入了最佳的表演狀態。
六、《貝多優》作為身體行動方法的實踐
純熟的技術是進入最佳表演狀態最根本的條件。芭芭曾在一封給謝喜納
(Richard Schechner)的信寫道:「我對於技巧並沒有興趣,但為了達到那最讓
我感興趣的,我必須將注意力放在關於技術的那些本質的問題上。我所追尋的,
在河的彼岸。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全神貫注於獨木舟的原因。」芭芭將技術比喻為
獨木舟,是搭載他和表演者前往彼岸的工具(Barba 1995, 142)。「存在感」既然
無法企及、無法描述,也無法度量,只能「準備」好讓它自己進入表演者。因此,
各種傳統劇場的大師們就設計出固定的程序,以摧毀演員體內習以為常的既定模
式,改變自然的平衡,刪除日常生活動作的動力(Barba 2012, 72)。在芭芭和歐
丁劇團的 MPA 小傳統裡,強調他的演員—舞者(actor-dancer)經過長時間的淬
鍊自己,透過超日常的技巧:平衡轉換、對立原則、等值的原則、潛程式(subscore)
等,發展出一套套固定下來的行動,即表演程式(score)。表演者藉由表演程式
與潛程式互動、整合,可以進入到另一種意識狀態,展現活生生的生命力。
爪哇的傳統表演者的養成過程經常從兩個方向進行:精熟外在技巧與內在靈
性的培養(如表 2)。實踐舞蹈即個人靈性修養、成長的過程,也就是自我情感
控制的訓練。情感管控同時就在型塑個人外在行為舉止,雕塑出優美、柔順、精
煉的身體動作。相對地,生活中合宜、優雅的行為舉止也會影響個人在表演藝術
上的創作。一般而言,東方的傳統或主要的亞洲哲學並不區分身體和心靈的訓練
方式,因為兩者密不可分。因此,表 2 中左、右兩邊的實踐可視為互為增長的正
向關係;換言之,表演者性靈的成長程度同時展現在外顯的舞蹈動作;而精熟技
巧也是個人精神淬練的過程。
-
20 林佑貞
表 2 爪哇舞蹈表演者(dance doer/performer)的訓練
外顯動作、技巧(outer transformation) 內在靈性成長(inner transformation)
1.精熟程序化舞蹈動作、舞譜、舞蹈類
型
2.通曉甘美朗音樂知識、節奏
透過苦行、夜間冥思(南海邊)、日惹
表演理論、齋戒、登火山等,培養耐心
(sabar),受、接受、承受(terima),
不受物質束縛、甘心(iklas)等特質
《貝多優》的 MPA 基本上是透過一套學習得來的抽象程式化動作,配合甘
美朗音樂,遵循既定的禁忌和規範,達到完滿感知(rasa full)的活生生的演出。
一般認為,只有成熟的舞者能學習、演譯最困難,也最神秘的《貝多優》,也就
是表演者對於舞蹈動作、舞譜、類型已經瞭若指掌,能充分掌握音樂的節奏,並
具備了關於甘美朗作品的知識。21 爪哇的舞蹈老師(guru)稱成熟的表演者為
“wiragadadi”,“wiraga”指的是舞蹈的身體技巧方面,“dadi”字面上的意思是準備
就緒、完成或成功地達成。日惹的 Krida Beksa Wirama 專業舞蹈學校裡,初級階
段的學生需要先從基本舞蹈動作語彙開始練習,稱為“teori”,不搭配甘美朗,著
重在記住動作的順序(Suharto 1990, 64-65)。這些單一個或一組的基本動作,顯
示了張力和鬆弛不斷變化的過程。例如:站立的基本動作“mandhak”:雙腳站立
的位置似古典芭蕾的基礎動作「蹲」(plié),膝蓋微彎,兩腳尖翹起、朝外張開
45 度。在舞蹈過程中,表演者必須以腳跟向左、向右扭轉,持續、穩定地橫向
改變身體重心。看似輕鬆隨意的搖擺站立,實際上需要身體各部位肌肉的運作支
持,才能平衡。芭芭認為,程式化劇場傳統的演員根據某種特定的張力和形式來
塑造身體,也就是這些張力和形式變成了閃電,感動了觀眾。因此,即使一動也
21 經由訪談得知,老一輩的舞者老師如蘇哈蒂(Theresia Suharti)女士和蘇蒂雅女士,對於
甘美朗音樂亦有深入的理解。但新生代的舞者,通常因為學校將舞蹈和音樂分科的關
係,比較傾向精熟單一領域。這兩位舞者老師的介紹、訪談內容與分析,可參見林佑貞
(2012)〈貝多優大師們的舞蹈生活哲學:印尼傳統表演理論初探〉。
-
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中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 21
不動的演員也可以感動觀眾(Barba 2012, 216)。碧水老師在向筆者解釋什麼是
“rasa”時邊示範邊說,「就像我看到一位舞者的站姿(tanjak,程序化的姿勢),就
能感受到他是不是充滿“rasa”」(碧水,個人訪談, 2013 年 9 月 12 日)。
這次與碧水老師的訪談,就在偏宮蒙辜那嘎蘭的演藝亭進行,我們脫下鞋
子,隨意坐在大理石階梯上。他時時起身示範,講解他對爪哇古典舞蹈的體悟。
早從孩提時期即深受祖父母的教誨與影響,碧水老師認為,舞蹈同時是「內在精
神」與「外顯身體」的朝聖過程(pilgrimage),舞者可能經歷狂喜(ecstasy)而
非出神。他認為,舞蹈《貝多優》必須注意三個重要的特質:「柔軟」(softness)、
「緩慢」(slowness)與「流動」(flowing)。為了訓練學生達到這些質地,他要
求學生須透過禁食活動,從傍晚 5 點至隔日清晨 5 點,在這 12 個小時內,無論
做任何一個動作、任一件事,都以比它原來日常生活節奏要緩慢許多的速度進
行,慢慢品嘗每個動作細微的變化,一個一個地完成。這個方法能實際讓學生體
驗到因為禁食的關係,物質身體逐漸虛弱無力、呼吸變緩、身體鬆弛,也因此能
在舞蹈時,自然而然展現柔軟、緩緩流動的感覺(碧水,個人訪談,2013 年 9
月 12 日)。22
西元十六世紀信仰伊斯蘭的馬塔蘭王朝取代了印度教王朝滿者伯夷
(Majapahit),伊斯蘭信仰和文化逐漸成為印尼大熔爐的要角。因為傳入爪哇的
伊斯蘭是具有長遠靈修傳統的蘇菲密契主義,「不以為『真一』乃是真主超越性
的絕對化,反而是指向真主、宇宙與人在本質上的合一,故開啟了內在性之路,
從人類心靈的內在尋找近神之道」(蔡源林 2011,153)。學者們一般認為,著重
靈修實踐的伊斯蘭蘇菲主義,與在爪哇本土盛行已久遠的印度教∕佛教的修行法
門類似,再加上蘇菲主義常將傳統表演藝術作為信仰傳播的媒介,因而很快地就
在上層社會傳播開來,風行草偃,於爪哇落地生根。
22 由於年輕一代的學生不習慣像老一輩的舞者會在演出前幾天或幾星期即開始齋戒禁食,
也因此碧水老師將禁食活動作為舞蹈教育的課程活動之一,使學生獲得實際的體驗。
-
22 林佑貞
從以上的歷史脈絡能夠解釋為何許多爪哇傳統表演藝術的大師依舊秉持
著,舞蹈和音樂的操練本身就是種苦行(Weiss 2003, 26)。為了確保一個好的、
有效的表演,大部分的爪哇藝術家都會定期進行超越學習角色的一些活動。蘇哈
托(1944-1997)23 曾就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的舞蹈系,作為日惹宮廷表演者的「局內人」(insider)的觀點,
寫就碩士論文:〈舞蹈的力量〉(Dance Power: The Concept of Mataya in Yogyakarta
Dance)。24 他在文中特別提到,一般認為建立日惹宮廷的哈孟辜布沃諾蘇丹一世
(Sri Sultan Hamengkubuwana I,治理期間:1755~1792),同時也是日惹風格舞
蹈的創造者。蘇丹本人即這門精神藝術的實踐者;日惹舞蹈的內在精神就是根據
蘇丹自我操練,而發展出來的內在能力與力量。他修行的方式包括「克服艱難登
上梅拉比火山(Mount Merapi)、齋戒以磨亮個人的內在情感、整個人淺浸於水
中來培養耐性與毅力,並且在夜間靜心修行」(Suharto 1990, 3)。蘇哈托的得意
門生戚湯尼(Bhaghwan Ciptoning)於文中也列舉了許多蘇哈托過去教導學生的
方法和例子,比如:蘇哈托經常會在深夜時,帶著學生前往日惹南方印度洋的海
邊,在那裡徹夜冥思、舞蹈,以體驗大自然隨時間更迭的變化下,個人和舞蹈的
互動(Ciptoning 2005, 45-54)。
日惹宮廷表演藝術有許多的舞蹈類型(形式),它們都是在描寫人的內在性
格,表達人的內在情感,可以說是靈魂的化妝師。這些舞蹈型態就是上了不同妝
容後的靈魂(Sas 1979, 1)。《貝多優》的形式亦顯示其追求靈性成長的特色。以
《貝多優卡達望》(如圖 3)為例,整支舞蹈歷時 90 分鐘,由三大部分組成,每
一個部分均以一連串的舞蹈隊型按照一定的順序變換,由九位舞者組成,每一位
代表著身體的九個部位(孔穴與四肢),列表如下:25
23 蘇哈托從 12 歲開始習舞,出身日惹宮廷的樂師與舞者世家(他是蘇哈蒂老師的胞弟),
曾是宮廷優秀的表演者,以演譯阿周那(Ajuna)聞名,生前擔任日惹藝術大學舞蹈老師。 24 1998 年於印尼出版。 25 《貝多優》的舞者名稱和排列順序依不同的作者有些微的差異,但隊型變化和舞者的位置
-
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中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 23
1. endhel:慾望,愛戀的情感。
2. batak:頭部、心靈。
3. gulu:頸部。
4. dhadha:胸部。
5. buncit:尾巴、生殖器、尾椎。
6. apit ngajeng:右臂、右翼、前翼。
7. apit wingking:左臂、左翼、後翼。
8. endhel wenton:右腿、突發的、原初的慾望、外顯慾望。
9. apit meneng:左腿、隱藏側翼、後發的慾望(Becker 1993, 131; Brakel-
Papenhuijzen 1992, 188)。26
基本上是一致的。不過,不同《貝多優》舞蹈隊形有時也代表不同的意涵。
26 布列可的舞者順序為:1. batak;2. endhel;3. endhel weton;4. apit meneng;5. apit ngajen;6. apit mburi;7. gulu;8. dhadha;9. buncit。但其舞蹈隊型的位置與貝克的資料一致。
圖 3 《貝多優卡達望》的隊形變化
註:圖的左方為王位所在。
-
24 林佑貞
舞者 endhel 代表慾望,也可以說是對任何事物的依戀與執著,是修行中最
需要克服的障礙。2、3、4 和 5 分別指佛教經典裡四個標準的脈輪(cakras),
加上 6、7、8、9 就形成了整個人類的形體(Becker 1993, 138):
X (王位) ↑ ↑ 6 8 右臂 右腳 ↑ ↑ ↑ ↑ ↑ 慾望 頭 頸 胸 生殖器
↑ ↑ 左臂 左腳
《貝多優》的隊形基本上有四或五種,分別代表陰陽調和、星辰運行和軍隊
陣式(Becker 1993, 131-140; Brakel-Papenhuijzen 1992, 188-196; Sas 1979, 2)。其
隊形變化通常展示著心靈與慾望不斷地相互拉扯,互相影響、抗衡,最後達到平
衡的過程。例如:《貝多優瑟曼》(如圖 4)的隊行變換從慾望試圖支配心靈,時
而衝突時而互相吸納,最後形成 3 × 3 的圓滿狀態,如下所示(Becker 1993, 140;
Suharti 2012, 156, 232):
X(王位)
↑ ↑ ↑ 1 2 8 頭
↑ ↑ ↑ 6 3 5 頸
↑ ↑ ↑ 7 4 9 胸
-
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中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 25
圖 4 《貝多優瑟曼》結束時的隊形
註:舞者面向蘇丹王。
《貝多優》的形式與內蘊的意義即說明了,表演者舞蹈的過程就在經歷一段
內在旅程,猶如禪修。一連串不斷反覆的程式化動作(系列),舞者需要時時變
化隊形,同時 360 度地轉換方位,加上長時間、緩慢地、沒有停頓的動作著,就
像氣流在身體裡互動環繞,形成美麗的線條。唯有在極度專注、身心合一的狀態
下,才可能無瑕地將舞蹈展現、完成。舞蹈就在舞者成為行動中的人(man in
action)27 隱沒消失的那一刻,浮現。
瑟蒂優希講述舞蹈《貝多優卡達望》的經驗時提到:
當時一跳就是兩個小時,28 舞者並不覺得累,因為必須全神貫注才能記
住每一個動作。就好像有人在靜心修行(meditasi)一樣,一定要全然地「進 27 蘇哈托以舞蹈表演者成為「行動中之人」來比喻舞蹈,就是「與神合一」(Suharto 1990, 26)。 28 《貝多優卡達望》全長 90 分鐘,若從入場前在內室的祈禱與待命,就將近兩小時。
-
26 林佑貞
入」(masuk),不只是跟著做。這些動作好像很簡單,但要不斷地重複。那
麼,必須能有[幫助]持續穩定狀態的[環境]:比如焚香以及富節奏的音
樂。如果舞者已經進入,就很好、舒服(enak),就像出神(trance)。(瑟蒂
優希,個人訪談,2013 年 9 月 25 日)
外在環境、戒律和禁忌等也是幫助進入最佳表演狀態的重要因子。《貝多優
卡達望》一定有火盆和焚香瀰漫整個演藝亭,而甘美朗敲擊出的特定節奏具有穩
定心緒的功能,以使表演者專注與持續。
舞蹈《貝多優卡達望》也須遵守宮廷的戒律和禁忌。例如:必須準備食物供
品向四方禮拜祈禱,以尋求不可見的神靈的允許和庇佑。29 即使只是練習而已,
也要預備供品祭拜。舞者若遇生理期必須上報宮廷特定人員並準備祭品以向琪督
皇后稟報。瑟蒂優希表示,齋戒在當時已經不是強制規定的活動,但她本人會盡
可能在表演前三天進行齋戒,幫助自己專注。(瑟蒂優希,個人訪談,2013 年 9
月 16 日)
七、轉化更新自我:實踐即革命
在爪哇的表演傳統中,舞者應該避免炫耀、展現個人自我。表演者要謹記觀
眾並不是要來看舞者跳得如何的好,而是看舞蹈本身。有句格言說:「別看我怎
麼跳,而是欣賞我的舞」(Suharto 1990, 20)。舞蹈是一種對上天(全能之神或是
南海女神)的「敬獻」(碧水,個人訪談,2013 年 9 月 12 日),你需要先淨空自
己,才可能充盈滿溢(empty yet full)。如同芭芭所強調的,訓練是種測試,看
一個人能夠為自己所宣稱的付出多少,是對於意圖的測試。這是演員作為一個人
29 瑟蒂優希示範默禱詞:「請允許演出《貝多優卡達望》,希望能獲得力量,平安順利直到
演出結束」(瑟蒂優希,個人訪談,2013 年 9 月 16 日)。
-
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中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 27
與群體的一部分,可以達到蛻變的具體因子(Barba 1972, 47-48)。據年長的古典
舞蹈大師們回憶,他們平時就不斷地練習舞蹈,從來沒把表演當作目標(Sas 1979,
1)。蘇哈蒂老師談起她小時候接觸舞蹈,只單純地將它當作日常的活動,沒想過
有一天會演出(蘇哈蒂,個人訪談,2013 年 9 月 24 日)。對他們而言,舞蹈是
在日復一日、甚至日以繼夜的沉默活動中,使個人經歷蛻變,改變自己看世界、
看彼此的觀點,讓個人(小宇宙)與所處的社會、世界(大宇宙)和諧共存,堅
定地朝著良善與真理邁進。
歐洲二次大戰後的混亂、失序、令人失望的現實環境,促使劇場開始往儀式
救贖的方向走。時序推移至今,已經二十一世紀了,儀式、宗教或個人靈修這樣
老掉牙的題材,還有討論、存在的價值嗎?在芭芭和歐丁劇團創造的小傳統裡,
這不是譁眾取寵的話題,也非意象和隱喻的城堡,而是關乎你是誰、生命是什麼
的真實行動(Barba 1995, 137)。芭芭的劇場人類學邀請世界各地不同傳統的表
演者齊聚在一堂,以二至四個星期不等的時間,進行交流、演練、討論與演出。
目的是從彼此的差異裡找出使表演者能展現活生生演出的秘密。對芭芭而言,這
些秘密具備著普世皆然的特性,是人類共有、共享的身體技藝。30 然而,劇場人
類學「去脈絡」的比較是不是就喪失它想要從技術層面,以理性、科學的分析角
度,探討演員訓練與表演的核心問題所給出的洞見和貢獻?本文認為,這是更具
企圖心的嘗試:找到超越意識型態的 MPA,使演員在不分種族、文化、宗教、
政治立場的情形下,都能透過嚴密的訓練,進而在演出時展現「存有」。芭芭和
他的生命夥伴——歐丁劇團成員,秉持這樣的信念,走過半個世紀的「實踐」,
30 這樣的主張自然招徠許多的批評,尤其當一個歷史久遠的傳統表演藝術脫離它原來的政
治、經濟、文化脈絡而被獨立出來研究、討論時,就容易只流於對它的技術層面的探
討,而忽略了這門藝術更深層的價值及它所乘載的文化精神,無視差異的存在而化約出
粗淺的結論。癥結在於芭芭用了人類學(學門)這個字,因為人類學的傳統是研究一特
定族群的社會組織與文化現象。舞蹈人類學雖然旨在凸顯舞蹈本身與其演變的過程,但
也不脫離孕育出人類動作系統成長發展的社會脈絡,儘管這些背景的探討還是為了解釋
舞蹈。芭芭的劇場人類學辭典,詞條式的呈顯方式顯然置外於這兩者。
-
28 林佑貞
為世界的劇場歷史接續演員訓練的追尋,以客觀的分析和主觀的操演讓各地的演
員們有不同於自己文化以外的訓練選擇和啟發。
著名的美國人類學者 Adrienne L. Kaeppler 在回顧與展望舞蹈研究的篇章裡
提到,新世紀裡的舞蹈研究應該著重在人類動作系統的研究;以發生這些動作的
社會的觀點為基礎,研究他們所發展的動作理論與哲學。她進一步說明,「研究
者運用西方舞蹈理論來分析非西方的舞蹈是不恰當的,而一位研究者應當企圖去
發現本地人關於動作的理論。」(Kaeppler 2000, 121)基於這樣的觀點,本文就
芭芭(以及他的生命共同體,歐丁劇團)發展出的 MPA 為切入點,闡明劇場演
出的有效性和個人在劇場經歷蛻變的兩個面向,透過解析並凸顯爪哇傳統的哲思
與表演者的詮釋,彰顯彼此相同呼應之處,更重要的是,探究印尼傳統表演藝術
的身體行動方法及其實踐。《貝多優》的 MPA 不僅只停留於建構國家、民族認
同與團結的功能上,反而繼續扮演使個人與社會幸福安康的角色。
這兩個活生生的身體行動方法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個人可以經由具體
適當的身體實踐,達到有機身心的轉化。超越劇場、表演的面向,讓身體行動回
歸生活;行動即生活。芭芭始終相信,劇場具備創造、反轉與自由的力量。爪哇
的表演藝術秉持著,透過舞蹈培養覺性,不斷地經歷自我轉化更新的過程,算不
算創造、反轉更基進的表現?如果說,一個時代造就劇場藝術的風格或走向,那
麼芭芭的 MPA 小傳統、印尼《貝多優》MPA 小傳統,是否也提供了一條能夠面
對存在、跳脫生命困境,充滿希望的路徑?
答案肯定不在文字迷障裡。當筆者即將再度離開爪哇時,蘇哈蒂老師 31 輕
聲道別說:「你何時再來?等你一起來跳舞!」
31 當天蘇哈蒂老師即在家中撥放《貝多優芭芭拉雅》,讓我一邊觀看,一邊為我解說。
-
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中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 29
圖 5
註:左一舞者為蘇哈蒂老師,於 2007 年 8 月 5 演出《貝多優芭芭拉雅》
(Bedhaya Babar Layar)。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尤金諾‧芭芭(Eugenio Barba)著,丁凡譯。2012。《劇場人類學辭典:表演者
的秘藝》。臺北市: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y)著,瞿白音譯。2006。《我的藝術
生活》。臺北市:書林。
林佑貞。2012。〈貝多優大師們的舞蹈生活哲學:印尼傳統表演理論初探〉。《戲
劇學刊》16:153-176。
梁燕麗。2005。〈巴爾巴與他的戲劇人類學〉。《戲劇》2:46-56。
理查․謝克納(Richard Schechner)著,周憲譯 。1998。〈東西方與巴爾巴的
戲劇人類學〉。《戲劇藝術》5:14-21。
-
30 林佑貞
曾薇霖。2010。《傳承、重建與接軌:印尼中爪哇日惹宮廷貝多優舞蹈音樂文化
發展與演變》。臺南市: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蔡源林。2011。《伊斯蘭、現代性與後殖民》。臺北市:臺大出版社。
鍾明德。2007。《OM 泛唱作為藝乘》。臺北市: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鍾明德。2012。〈這是種出神的技術︰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葛羅托斯基的演員訓
練之被遺忘的核心〉。《戲劇藝術》16:119-152。
鍾明德。2013。《藝乘三部曲:覺性如何圓滿?》。臺北市: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鍾明德。2014。〈一個萬人參與演出的「溯源劇場」:目瑙綜歌的身體行動方法
(MPA)研究〉,臺灣戲劇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國
立台北藝術大學,臺北市,2014年5月9日。
蘇子中。2013。〈Rasa:表演藝術的情感滋味〉。《中外文學》42(3):157-197。
西文部分
Kaeppler, Adrienne L. 2000. Dance Ethnology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Dance.
Dance Research Journal 32, no. 1: 116-125.
Barba, Eugenio. 1972. Words of Presence. TDR 16, no. 1: 47-54.
Barba, Eugenio. 1995. The Paper Canoe: A Guide to Theatre Anthropology. London,
UK: Routledge.
Becker, Judith. 1993. Gamelan Stories: Tantrism, Islam and Aesthetics in Central
Java. Mongraphs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Tempe: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Becker, Judith. 2004. Deep listener: Music, Emotion and Trancing.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rakel-Papenhuijzen, Clara. 1992. The Bedhaya Court Dances of Central Java.
Leiden: E. J. Brill.
Brakel-Papenhuijzen, Clara. 1995. Classical Javanese Dance: The Surakarta
-
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中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 31
Tradition and Its Terminology. Leiden: KITLV Press.
Ciptoning, Bhaghwan. 2005. Taking a Stroll in the World of Dance Together with Ben
Suharto. Contemporary Theater Review 11, no. 1: 45-54.
Geertz, Clifford. 1965. The Religion of Java.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Gold , Lisa and Benjamin Brinner. 2007. Review.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 60, no. 3: 677-688.
Hostetler, Jan. 1982. Bedhaya Semang: The Sacred Dance of Yogyakarta. Archipel 24:
127-142.
Hughes-Freeland, Felicia. 2008. Embodied Communities: Dance Traditions and
Changes in Java. Oxford, UK: Berghahn Books.
Parto, F. X. Suhardjo. 2001. Recent History of Javanese Classical Dance: A
Reassessment. Contemporary Theater Review 11, no. 1: 9-17.
Ranggawarsita, Raden Nagabehi. 1906. Pustaka Raja. Poerwa, 9 vol. Ngayogyakarta.
Sas, Rama. 1979. The Physical and Spiritual Education Found in Yogyanese Classical
Dance. Manuscript.
Suharti, Theresia. 2012. Bedhaya Semang: Kraton Ngayogyakarta Hadiningrat
Reatualisasi sebuah Tari Pusaka. Universitas Gadjah Mada. PhD.
Dissertation.
Suharto, Ben. 1990. Dancer Power: The Concept of Mataya in Yogyakarta Da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Master Thesis.
Sumarsam. 1995. Gamelan: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Musical Development in
Central Java.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uryobrongto, G.B.P.H. 1981. Penjiwaan dalam Tari Klasik Gaya Yogyakarta.
Mengenal Tari Klasik Gaya Yogyakarta, ed. F. Wibowo. Yogyakarta: Dewan
Kesenian Propinsi DIY. 88-93
Sutton, R. Anderson. 1993. Semang and Seblang: Thoughts on Music, Dance, and the
-
32 林佑貞
Sacred in Central and East Java. Performance in Java and Bali, ed. Bernard
Arp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Tirtaamidjaja, Nurjirwan. 1967. A Be�aja Ketawang Dance Performance at the Court
of Surakarta. Indonesia 3: 30-61.
Warsodininggrat, R.T. 1972. Weda Pradannga. Surakarta: SMKI Surakarta.
Weiss, Sarah. 2003. “Kothong Nanging Kebak”, Empty Yet Full: Some Thoughts on
Embodiment and Aesthetics in Javanese Performance. Asian Music 34, no. 2:
21-49.
White, R. Andrew. 2006. Stanislavsky and Ramacharaka: The Influence of Yoga and
Turn-of-the-Century Occultism on the System. Theatre Survey 47: 73-92.
訪談
碧水(Bambang Besur)。2013 年 9 月 12 日。梭羅。訪談人:林佑貞。
瑟蒂優希(Sri Setyoasih)。2013 年 9 月 16 日。梭羅。訪談人:林佑貞。
瑟蒂優希(Sri Setyoasih)。2013 年 9 月 25 日。梭羅。訪談人:林佑貞。
蘇蒂雅(Siti Sutyiah)。2013 年 9 月 19 日。日惹。訪談人:林佑貞。
蘇蒂雅(Siti Sutyiah)。2013 年 9 月 26 日。日惹。訪談人:林佑貞。
蘇哈蒂(Theresia Suharti)。2013 年 9 月 23 日。日惹。訪談人:林佑貞。
蘇哈蒂(Theresia Suharti)。2013 年 9 月 24 日。日惹。訪談人:林佑貞。
蘇哈蒂(Theresia Suharti)。2013 年 9 月 27 日。日惹。訪談人:林佑貞。
錄影、影片資料
Bedhaya Semang. Ed. Alex Dea. 2002. Yogyakarta: Kraton Ngayogyakarta. DVD.
Bedhaya Babar Laya. 2007/8/05. Yogyakarta: Dalem Yudhaningratan. Personal
Documentary.
-
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中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 33
On the Method of Physical Actions in Bedhaya, Javanese Court Dance
Lin, Yu-Chen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Theatre Art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bstract
Eugenio Barba found that successful performers in different cultures all possess
the secret art of presenting scenic bios; that is, the performer can become a
“presence” on stage. This is also the origin of all techniques that are based on Barba’s
“theatre anthropology” and its “Method of Physical Actions” (MPA) as developed by
both Barba and the Odin Theatr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secret art of
Javanese court dance, showing how they train performers/individuals through
Bedhaya (MPA), so as to experie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sciousnes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is not only the key to an effective performance but can also be a
proper course for personal spiritual growth.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start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Bedhaya history, and
then gives a definition of MPA. The second part focuses on how Javanese defi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sciousness. The third part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the training
-
34 林佑貞
and practices of Bedhaya as a kind of MPA, aiming to provide performers/individuals
with a workable, as well as effective, way of self-training.
Key words:Bedhaya, Method of Physical Actions, presence, transformation of
consciousness, theatre anthropology
![Stripe blue [轉換]拷貝](https://static.fdocument.pub/doc/165x107/55c51cffbb61eba1488b469e/stripe-blue-.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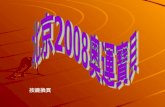








![Stripe stellblue [轉換]拷貝](https://static.fdocument.pub/doc/165x107/55b9321ebb61eb216a8b4591/stripe-stellblu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