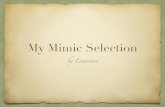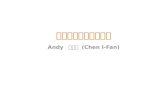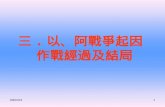日本戰後小劇場運動當中的「身體」與「空間」
-
Upload
tnua-ebook -
Category
Documents
-
view
240 -
download
14
description
Transcript of 日本戰後小劇場運動當中的「身體」與「空間」

日本戰後小劇場運動當中的「身體」與「空間」
林 于 竝 著


前 言
1986 年的某天,王墨林以及卓明老師突然宣布,說有個日本「前衛得不得了」
的表演團體要來台灣,正在徵求幾名地陪人員。我基於強烈的好奇心報名參加。現
在已經忘記最初約定的地點,只記得眼前出現十幾位長相怪異的日本人,他們穿著
鮮豔服裝,但卻顯得有點過於沉默與壓抑。不知道為什麼對於這群人的第一印象是
「髒」。地陪的工作是帶他們尋找表演用的道具。我們來到後火車站的市集。本來
想介紹代表台灣味道的傳統竹編製品,但是他們卻對那些便宜顏色俗艷的塑膠製品
顯現出強烈的興趣。他們挑了大量的桃紅色的臉盆、綠色的鬃刷、拜拜用的紅色塑
膠酒杯、蛙鏡等。我很納悶這些「道具」將如何被使用。兩天後,他們帶著這些塑
膠製品來到中影文化城拍照。到了充當化妝間的側房,他們不分男女迅速地脫去全
身的衣物,我身處他們中間一時不知所措。他們在身上塗上一種奇特的白色顏料,
最後轉身相互補上背後塗不到的那部分,一切是這麼安靜而有效率。一名男舞者將
蛙鏡罩在自己的下體上,另一名女舞者將拜拜用紅酒杯套上自己的兩隻乳房,空氣
當中瀰漫著白色顏料刺鼻的味道。舞者們爬上中影文化城中式古典廳堂的大桌上,
擺出充滿色情暗示的姿勢。雞鴨魚肉的中式菜餚,以及十幾名近乎裸體的舞者擠在
桌面上,蓄著大鬍子的團長用擴音器大聲斥責團員們,觀光客們議論紛紛,就在場
面接近失控時,強烈的閃光燈突然亮起,十幾副詭異猙獰的臉孔烙印在我的視網膜
上。
「白虎社」的《雲雀與臥佛》是我青春不能抹滅的記憶。之後,王墨林關於日
I

本前衛劇場的文章成了我重要的養分來源。土方巽、唐十郎、鈴木忠志這幾個名字
組織起我的日本前衛劇場想像。為了想知道鈴木忠志所寫的一本小書《演劇とは何
か》的內容,於是我開始學日文。
「陰暗」、「潮濕」、「詭異」、「死亡」、「怨念」等,是當時對於日本前
衛劇場的印象。不管這個印象是否出自於某種對於日本的先入為主觀,但至少對我
而言,這是年少時期的真實感覺。這個日本印象成了我後來想要對於日本戰後劇場
作第一手研究的強烈慾望。
在日本進入博士班之後,我必須決定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原本想選擇一個更能
全面性地觀察日本戰後劇場的題目,但是,基於必須以日文書寫幾十萬字的論文,
以及前後兩次在幾位教授面前進行答辯,我最後選擇鈴木忠志做為我的研究對象。
因為鈴木忠志是個很「知性」、很「哲學」的導演,我當時認為選擇這樣的研究對
象對於論文而言是比較好寫的。但是在事後,我發現鈴木忠志的確是非常正確的選
擇。原因不是因為鈴木忠志比較好寫,而是因為鈴木忠志對於表演導演理論的高度
自覺,他不只是在作品的層面上,而是在日本戰後的文化情境整體上來思考戲劇的
問題,而這點對我思索日本的戰後戲劇而言是個絕佳的切入點。耙梳鈴木忠志的戲
劇思想,以第一手資料來復原日本戰後小劇場作品,並將作品置於當時的社會、經
濟、政治以及文化脈絡上來思考鈴木忠志,這是我的博士論文的主要工作。再度回
頭觀看自己的博士論文,有幾分滿意,也有幾分缺憾。對於自己的博士論文的缺憾
有以下幾點,首先是這篇論文主要處理鈴木忠志的戲劇,對於唐十郎、鈴木忠志等
同時代的其他戲劇作品較少著墨。另外,這篇論文對於日本戰後的精神史、日本面
臨敗戰,以及加入戰後世界新局勢的過程較少涉及。最後對於「身體」與「空間」
這兩個日本戰後小劇場運動很重要的問題的探討不足。因此,在本人回國之後,以
國科會研究案的形式對於這幾個問題繼續做較深入的探討。從 2003 年起,本人分別
進行以下的研究計畫案:
1.2003 年國科會研究案 :「存在論的舞蹈--『舞踏』的美學研究」
(NSC92-2411-H-119-002 )
2.2004 年國科會研究案:「日本戰後前衛劇場帳篷劇研究」
(NSC93-2411-H-119-002)
3.2005 年國科會研究案:「身體、空間與文體;唐十郎帳篷劇場之
II

研究」
(NSC94-2411-H-119-003)
4.2006 年國科會研究案:「『表演的身體』與『文化認同』--日
本戰後前衛導演鈴木忠志研究」
(NSC95-2411-H-119-004)
5.2007 年國科會研究案:「世阿彌表演美學研究」
(NSC96-2411-H-119-003-MY2)
6.2008 年國科會研究案:「世阿彌表演美學研究」
(NSC96-2411-H-119-003-MY2)
7.2009年國科會研究案:「疆界、移動與跨文化主義:日本藝術節慶之研究」
(98-2420-H-119-010-MY3)
這幾個研究計畫都是延續本人對於日本戰後劇場問題的追尋,本書同時也是這
幾年國科會研究計畫的成果報告。本書的主要任務,是從作者本人的觀點對於日本
戰後的小劇場運動,以第一手的資料,進行貼近的觀察。本書作為分析研究對象所
使用的資料,包括作品資料、演出記錄、戲劇評論、訪問記錄,以及研究對象的著
作文章、訪談、對談紀錄等,都是本人在日本所收集的第一手資料。因此,本書首
先要感謝國家科學委員會所提供的經費補助,讓本人可以在國內資料取得不易的情
況之下遠赴日本,讓本研究可以順利進行。並由衷感謝日本早稻田演劇博物館、日
本慶應義塾大學藝術中心(慶應義塾大學アートセンター)的土方巽資料中心、日
本國會圖書館、日本大阪大學演劇研究室、日本演劇學會近現代演劇研究分會等單
位所提供的資料以及一切的協助,讓本研究得以完成。
我要特別感謝吳靜吉博士的帶領,我是多麼的幸運可以跟著吳博士這麼長的時
間,這麼豐富的課程,這麼多的啟發。以及蘭陵劇坊的師長金士傑、李國修、卓明、
劉靜敏、陳偉誠,在成長期間有機會可以跟隨在他們的身邊,很喜歡上他們的課,
很喜歡圍繞在他們的身邊,聽著他們關於藝術,對於生命許許多多的想法,這些都
深深影響著我,成為我現在的一部分。我再也想不出還有誰能有這樣的幸運,可以
同時擁有這些人這麼直接的影響。當然還要感謝王墨林,是他引領著我們進入日本
前衛劇場的魔幻世界,以及永遠不願與這個世界達成共識的批判精神。以及要感謝
櫻井大造、秦 Kanoko、鍾喬以及海筆子的夥伴們。他們開啟了我對於藝術的另外一
種看法,讓我可以將最無償的愛、最冷酷的社會現實以及最自由的藝術想像力,這
III

三種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思考。最後要感謝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所提供的環境,
當初很遺憾無法成為邱坤良、鍾明德、陳芳英以及馬汀尼等老師的學生,來到這裡
終於讓我有機會可以跟著他們學習。無論是在創作上或者是在研究上,這裡永遠充
滿刺激,激發我邁向下一個目標。我覺得來到這裡的這段期間我成長了很多很多。
我還要感謝我的學生們,沈亮慧以及我的助理周曼農,謝謝他們的幫助和照顧。如
果這本書所代表的,是我的學習與研究的成果的話,我要謝謝我的父母,我的摯友
王耿瑜以及日本國立廣島大學的指導教授原正幸教授與青木孝夫教授,雖然這本書
的成績尚不足以回應他們對我的教導與期待,但是,我想把這本書獻給他們,而且,
今後我將會更加努力。
IV

目 錄
前言
第一章 日本的「戰後」與小劇場運動
第二章「否定性的身體」:土方巽與日本人
第三章「表演」與「瘋狂」:鈴木忠志戲劇理論中的沙特與梅洛龐蒂
第四章 以「亞洲」做為方法的舞踏:秦 Kanoko 與台灣
第五章「負性空間」的劇場:試論鈴木忠志的空間思想
第六章 亡靈凝視的空間:櫻井大造與台灣帳篷戲劇


1
第一章
日本的「戰後」與小劇場運動
第一章 日本的「戰後」與小劇場運動
一、戰後的「小劇場運動」
1965 年 3 月一個酷寒的日子,東京西銀座數寄屋橋公園當中突然出現了一群
穿著白色衣服發出奇怪的聲音的團體,他們煞有介事地走到水池旁邊,有人拿著保
健室的人體模型當做道具,有人坐在地上類似參禪冥思,另外還有一名演員跳進酷
寒的公園水池當中來回游泳一個鐘頭幾乎凍死,最後警察以警力制止了這場演出。
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導演唐十郎以及數名演員被帶到警察局拘留一個晚上。這群宣稱
為「狀況劇場」的團體將這個「作品」取名為《縫紉機與黑雨傘的別離》。從名稱
上可以很明顯看出,年輕導演唐十郎似乎有意讓他的「街頭劇」與超現實主義藝術
家羅多雷蒙(Lautreamont)的《在解剖台上縫紉機與黑雨傘的相遇》之間相互呼
應 1。
1966 年 10 月,唐十郎接著又於新宿區的戶山社區裡演出戶外劇《腰卷阿仙忘
卻篇》。他們以簡單的手提卡式錄音機作為音效,負責「燈光」的工作人員死命踏
著腳踏車的踏板,旋轉車輪來發動車燈作為演出的照明。一樣的,這個戶外演出還
是並沒有經過事前的許可申請,還出現全裸的演員,因此警方出動四台警車包圍舞
台區與觀眾,並不斷以擴音器干擾演員的表演。就這樣,這個「街頭劇」的演出就
在噪音與混亂當中結束 2。在《腰卷阿仙》之後,唐十郎開始在他的戶外劇的表演四
周圍上帆布,並且逐漸加上屋頂,帳篷劇場的表演方式因此誕生。1967 年,唐十郎
1 見扇田昭彦:《日本の現代演劇》,東京:岩波新書,1995 年,頁 27。
2 同前註,頁 28-29。

2 第一章 日本的「戰後」和小劇場運動
首次以紅色的帳篷劇場演出他的戲劇作品《月笛小仙 ---義理人性篇》。從此以後,
帳篷劇場成為唐十郎的戲劇作品最主要的演出形式,而彷彿「毒香菇」般在都市角
落突然出現的「紅帳篷」也成為「狀況劇場」的標誌。
1966 年,一群從早稻田大學畢業或者退學好幾年的學生們聚集在一起,他們
並沒有展開任何就職活動,四處打工,半年後,他們將打工累積的錢掏了出來,在
東京新宿區的一家喫茶店的二樓搭建起專屬的排練兼用劇場「早稻田小劇場」。從
1966 年到 1976 年為止,這個劇場總共維持了十年。這個群體以導演鈴木忠志、演員
小野碩以及新興劇作家別役實為中心,稱為「新劇團自由舞台」。這個成立於 1961
年的劇團當初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想把別役實的作品推出去。別役實的作品風格
與當時以社會寫實主義為主流的新劇作品大異其趣,劇中沒有顯著的情節以及角色
衝突,整個劇本充斥著看似平凡近乎無聊的對話,可是在極為日常的風景背後卻隱
藏著某種巨大的犯罪。「新劇團自由舞台」的團員們都知道,在當時新劇主流的劇
場體制底下,像別役實這樣的劇本是不可能得到任何上演的機會的。當時日本的新
劇主要以「文學座」、「俳優座」以及「民藝」為中心。這三個大劇團幾乎掌握了
當時戲劇所有製作、演出場地以及演員訓練的資源。因此,一般非此系統出身的劇
團幾乎沒有演出的可能。在「新劇團自由舞台」成立之後,鈴木忠志執導了別役實
的《象》、《門》等作品,在報章雜誌的劇評上獲得了很大的好評。但是在「早稻
田小劇場」落成後不久,鈴木忠志與別役實因方向不同而各自發展。失去駐團作家
的鈴木忠志開始以「蒙太奇」的手法創作舞台,試著將荒謬劇《等待果陀》、新派
劇《婦系圖》、鶴屋南北的歌舞伎《櫻姬東文章》、《隅田川花御所》等幾個風格
迥異的劇本的片段「拼貼」在一起,創造出一個新的戲劇來。自1969年起至1971年,
鈴木忠志用這樣的手法在「早稻田小劇場」當中發表了《關於戲劇性的東西》三連作,
獲得了極大的迴響。尤其是未曾受過正統戲劇訓練的新進演員白石加代子所飾演發
瘋的老太婆,她的表演一鳴驚人,徘徊在控制與失控邊緣的瘋狂表演,讓日本被看
慣於史坦尼斯拉夫斯基(Constantin Stanislavsky)體系所型鑄出來的表演的劇評
家瞠目結舌。劇評界形容白石加代子的表演為:「充滿濃密的身體感覺,極具侵犯
力與激情讓我們不敢直視。」3,此後被稱為「瘋狂女優」。
3 同前註,頁 51。

3
第一章
日本的「戰後」與小劇場運動
1967 年初,在報紙不起眼的角落出現一則小廣告:「奇優怪優侏儒巨人美少
女等募集」。幾天後果然有許多「畸形人」出現在約定地點,在簡單的談話之後這
些人成為劇團「天井棧敷」的演員。雖然說是「演員」,但是以詩與短歌在當時文
學界已經是知名人士的團長寺山修司並不打算訓練這群毫無表演經驗的演員,他讓
這群具有驚人肉體的「演員」直接登上舞台,暴露在觀眾的視線之下演出《青森縣
的駝背男》。幾個月後寺山修司又找來一群體重驚人的女人排列在舞台上演出《大
山肥胖女的犯罪》。他稱他這樣的舞台為「見世物的復權」。在日本所謂的「見世
物小屋」是指早期巡迴各鄉鎮,混合魔術表演、畸形人或動物展示甚至色情表演的
低級馬戲小屋。寺山修司的作法對於盡畢生之力好不容易讓戲劇成為正統藝術,甚
至為了貫徹戲劇裡念而犧牲生命的那些新劇前輩們是個嚴重的冒瀆。1970 年 5 月,
在「天井棧敷」地下劇場裡頭,正在進行的舞台演出突然中止,觀眾被請出劇場,
搭上一部窗戶全以窗簾遮蔽的巴士當中,在迂迴的環繞之後巴士停在一棟公寓的門
口,在「導遊」的引導之下觀眾們登上階梯,來到一戶住家的門口。在一陣敲門之後,
一對正在吃飯的夫妻打開房門,正當驚訝於這群不速之客時,這位「導遊」竟然在
未經主人的允許之下,帶領著所有觀眾強行進入這戶人家之中。面對不知所措的這
對夫妻,「導遊」彷彿電視秀主持人般不斷提出許多關於「現實生活」的問題質問
他們。就這樣,觀眾在「導遊」的引導之下「觀看」了這對夫妻的「最真實的生活」。
最後觀眾才發現這對夫婦原來是特別安排的「演員」4,而所發生這一切其實是劇團
「天井棧敷」所進行的一齣叫做《イエス》的「市街劇」。
1966年,一群自新劇名門「俳優座」所附設的「俳優養成所」(演員訓練學校)
出身的年輕演員組成新的劇團「自由劇場」。在 60 年代當時,「俳優座」的俳優養
成所是培養「正統」新劇演員的大本營,從這裡訓練出來的演員被允諾一個登上正
規新舞台的康莊大道,但是,這群新劇界的菁英卻捨棄這條路徑,投身到「小劇場」
的行列。不同於「早稻田小劇場」花了半年的時間,他們以很快的速度募集到了足
夠的資金,將位於西麻布一棟大樓地下室改建成一個可以容納八十人的小劇場「ア
ンダーグラン自由劇場」(underground 自由劇場)。1968 年,「自由劇場」與東
京大學學生戲劇社團出身的「六月劇場」,以及「發現之會」串聯,共同成立「演
劇センター 68」(演劇 center 68)的組織,企圖發動一個跨劇團的小劇場運動。
1969 年 6 月,這個串聯組織(後來稱為「演劇センター 68/69」)發表「コミュニ
4 同前註,頁 148。

4 第一章 日本的「戰後」和小劇場運動
ケーション計画 ‧ 第一番」(communication 計畫 ‧ 第一號),公開宣示即將進行
「據點劇場」、「移動劇場」、「壁面劇場」、「教育」以及「出版」五個部門的
活動。所謂「據點劇場」指的是室內劇場的戲劇演出活動,除了原有的「underground
自由劇場」之外,還計畫興建一個容納二、三百人的劇場。在「移動劇場」計畫當中,
他們展開「黑帳篷」劇場的全國巡演活動。「壁面劇場」則是延伸發展中國文化大
革命「大字報」,或者學生校園抗爭運動當中作為宣傳思想的海報的形式,企圖創
造出具有社會運動性質的「反抗藝術」。在「出版」方面,他們發行了季刊雜誌《同
時代演劇》。整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計画 ‧ 第一番」的規模非常的龐大,他們
不滿足於局部性的小劇場演出活動,而企圖將小劇場的運動擴展成為全面性的「文
化社會運動」,甚至某種「文化革命」。雖然在「劇場興建」、「壁面劇場」等方
面的活動最後遭受挫敗,但是「黑帳篷」的帳篷劇場活動到最後仍然持續下來。
從 50 年代後期到 60 年代中期,以東京為首的大都市開始出現許多「小劇場
劇團」。除了以上所提及的「新劇團自由舞台」(1961 年)、「狀況劇場」(1962
年)、「發現之會」(1964 年)、「六月劇場」(1966 年)、「自由劇場」(1966
年)、演劇實驗室「天井棧敷」(1967 年)之外,還有蜷川幸雄的「現代人劇場」
(1968 年)、程島武夫以及太田省吾的「轉形劇場」(1968 年)、東由多加的「東
京 kidbrothers」(1968 年)等。這些小劇團大多來自兩個源頭,一個是學生劇團,
另一個是新劇劇團所附設的演員訓練學校。無論是來自哪一個源頭,相對於當時的
戲劇主流的「新劇」而言,這些「小劇場劇團」都是「業餘的」戲劇團體。他們大
多標榜著激進的「前衛」藝術理念,甚至受到「偶發藝術」的影響,進行一些戶外
的即興表演。就劇團組織而言,導演通常兼任團長甚至劇作家,對於演出工作並非
由分工的專業人員所擔任,而是由演員共同負擔所有製作和演出的工作。這類的劇
團當然不可能負擔一般大劇場的演出使用租金,更別說擁有自己的專屬排練場,因
此,為了確保演出的機會,他們改造一般民宅或者咖啡廳成為劇場,利用非劇場空
間作為表演場地。在 60 年代的戰後日本,伴隨著這些「前衛」劇團的興盛,東京大
都會當中出現了許多「小的」劇場空間,形成所謂「小劇場現象」。
二、「小的劇場」
談到日本戰後小劇場運動的發展首先必須被提起的是「Art Theater 新宿文
化」。「Art Theater 新宿文化」原本是家位於新宿的電影院。自 1963 年起,在每

5
第一章
日本的「戰後」與小劇場運動
天晚上九時最後一場電影放映完畢之後,開始變身成為劇場,上演各小劇場的舞台
作品。對於當時欠缺演出場地的小劇場運動者而言,「Art Theater 新宿文化」不只
提供寶貴的演出場所,它更帶動了當時的「小劇場文化」。之後,小劇團紛紛開始
尋求自己專屬的排練場兼演出場地。1965 年,劇團「變身」將位於明治神宮森林附
近的一戶住宅改建成「代代木小劇場」,這個場地可以容納觀眾70名。1966年10月,
鈴木忠志所領導的「早稻田小劇場」將位於東京早稻田咖啡廳二樓的場地改建成為
60 名觀眾的小劇場。同年 11 月,由佐藤信所領導的劇團「自由劇場」利用位於東京
六本木商店街地下室成為60名觀眾席的小劇場「underground自由劇場」。1969年,
寺山修司所成立的劇團「天井栈敷」在澁谷的地下室裏興建地下劇場。綜觀這些劇
團專屬的小劇場,在空間性格上具有下列幾個共通性:(1)大多坐落於一般民宅內、
咖啡廳、商店街地下室等日常生活空間內部。(2)建築本身原來非爲劇場設計,而
是替代空間的劇場。(3)整體空間極小,平時做為劇團排練之用,演出時化身為劇
場空間。(4)非鏡框舞台,欠缺舞台縱深,無固定的觀眾席區或舞台區,由於空間
侷促,演員以及道具等待進場的區域幾乎不存在,所以無法經常變換場景。(5)觀
眾數量在 80 人以內。
在一開始,一般大眾以及新聞媒體對於這股業餘性質的「小劇場運動」並不予
以正視。或者相反的,他們反而經常以醜聞或者社會事件登上新聞雜誌。例如舞踏
的創始者土方巽以及他的舞者們的照片經常因為裸體或者大膽的身體姿態而登上《演
藝畫報》等這類八卦雜誌的版面。在早期唐十郎的「街頭劇」以及寺山修司的「市
街劇」,與其說是因為藝術上的成就,倒不如說是因為擾亂交通或者與警察的衝突
而成為新聞的話題。新聞媒體習慣以「アングラ」這個字眼來稱呼這群人的表演。「ア
ングラ」(發音「angura」)是日本新聞媒體取自「地下(underground)」所創造
出來的字彙。原本這是對於這個小劇場運動的蔑稱,但是到後來這群年輕人卻將此
來自社會的蔑稱視為光榮的勳章而加以使用。像唐十郎、寺山修司以及土方巽更把
不斷的創造出社會新聞事件當作「顛覆既存的社會體制」的戰略,直接將「醜聞性」
作為他們「激進劇場美學」之一。
三、「安保鬥爭」與「高度經濟成長」
一般的日本戰後小劇場研究必定會觸及到「安保鬥爭」這個時代背景,除了因
為鈴木忠志、唐十郎、別役實、蜷川幸雄等這群所謂的「第一代」的小劇場運動者

6 第一章 日本的「戰後」和小劇場運動
大都曾經親身經驗過「安保鬥爭」這個因素之外,「小劇場運動」對於既存的戲劇
表現形式所作展現的批判與反叛,其實與日本當時從「安保鬥爭」這股彌漫在整個
60、70 年代的「造反」、「顛覆」社會氣氛息息相關。關於這點,我們有必要進一
步地從「空間」與「身體」這兩個層面,探討日本戰後小劇場美學與「安保鬥爭」
之間的關係。
所謂「安保鬥爭」(或者「反安保鬥爭」),就是「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反
對鬥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以與昔日大敵美國的共同防禦聯盟關係,重新
加入了國際社會,並且在美國的軍事傘的保護之下,日本在經濟上以驚人的高度成
長,迅速地從戰爭的瓦礫中重新站了起來。而這個形成美國軍事保護傘的日美共同
防禦聯盟關係,就是奠基於「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之上。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
投降,自此日本的「戰後史」正式開始。受降之後的日本政府由「聯合國軍總司令
部(簡稱 GHQ)」所接管,進入所謂的「佔領」時期。到了 1951 年,日本與聯合國
於美國舊金山簽訂和平條約,正式終止與世界各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戰爭
狀態」。原本在和平條約生效之後,由麥克阿瑟所領導的 GHQ 必須撤出日本,讓日
本回歸主權獨立國家,但是在1950年當時正值韓戰爆發,蘇俄的共產勢力不斷擴張,
以及鄰近的中國成為共產國家。在冷戰的世界局勢之下,日本的戰略地位對美國而
言日趨重要。而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也盤算著,在當時的局勢之下,與其爭取發
展國家軍隊,倒不如藉由將國家防衛託付給美國,以便於全力發展經濟。因此,就
在舊金山簽訂和平條約的同時,日美簽訂了「安全保障條約」。根據這個條約,戰
後占領日本的美軍成為駐日美軍,繼續駐留日本。
但是,「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同時也意味著日本對美國的從屬關係,許多人擔
心這個條約將為日本帶來戰爭的危險。加上美國駐軍在日本所犯下的許多刑事案件,
以及圍繞在美軍基地的衝突事件不斷發生,在學生和知識份子之間逐漸凝聚了一股
反美的情緒。這股情緒以大學校園為中心漸漸在日本各地蔓延開來。在 1950 年的協
定當中,這個條約於十年後,也就是 1960 年將會進行換約。而當時擔任日本首相的
岸信介有意讓這個條約成為永久化,也就是在雙方無異議的情況之下,「安全保障
條約」將於每十年,也就是於 1970、80 年等自動換約。「安保鬥爭」運動就是以阻
止「安全保障條約」的換約為抗爭焦點,在 1959、69 年的兩次條約時效前夕達到最
高峰。「60年安保」以及「70年安保」的兩次鬥爭雖然在組織以及形態上有所不同,
但是「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連合」(簡稱「全學連」)扮演著主導的地位。「全學連」

7
第一章
日本的「戰後」與小劇場運動
是由不滿日本共產黨在 1955 年之後放棄武裝鬥爭路線而退黨的學生所組成的團體。
在「全學連」的主導之下,1960 年的「安保鬥爭」在「羽田空港包圍事件」、「國
會議事堂闖入事件」等激烈的衝突事件當中展開。東京大學學生樺美智子的死亡事
件,加上清水幾太郎、吉本隆明等思想家的在思想論述方面對於學生運動的支持,
讓原本以學生為主的「安保鬥爭」得到上班族、家庭主婦等的共鳴,原來與政治無
緣的一般民眾也參與投入支持,「全學連」成為當時全日本反美情緒的代言者。
到了 1970 年的「安保鬥爭」以「全共鬥」以及「新左翼」的學生組織為先鋒,
在各大學校園展開一連串的所謂「校園紛爭」。大學生進行罷課運動,他們用各桌椅
搭建拒馬霸佔校園,並在裡面遊行演說,鼓吹校園內的民主與自由。學生運動與鎮
暴警察的流血衝突事件充斥著每天的新聞電視。自1968年起,「沖繩日衝突事件」、
「新宿騷亂事件」等等衝突事件連日發生,比起1960年的「安保鬥爭」,1970年「安
保鬥爭」的激烈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在 1960 年的「安保鬥爭」當中,在鎮暴警察
的強勢武力鎮壓之下手無寸鐵的學生只能以肉身抵擋棍棒,但是1970年「安保鬥爭」
的學生運動的方式卻起了極大的變化。學生運動的抵抗變得更有組織而且顯得訓練
有素,他們頭戴膠盔身穿工作衣,手持棍棒,並且使用汽油彈。但是,過度的暴力
以及長時間的社會失序已經讓民眾產生反感,加上學生組織之間相互的衝突矛盾,
不像是60年代的安保鬥爭獲得廣大民眾的同情,一般民眾開始遠離學生運動。另外,
日本政府從 1960 年的安保當中獲取經驗,開始對於 70 年代的「安保鬥爭」採用兩
面策略。在一方面對於學生運動實施強力的武力鎮壓,另外一方面對於一般民眾以
經濟成長作為利誘,從側面瓦解安保鬥爭的氣勢。從 1960 年開始,日本開始以「國
民所得倍增計畫」作為施政的目標,池田內閣公開宣誓以十年的時間達到國民所得
的倍增,原本只有在經濟學者間所使用的「國民所得」、「GNP」等經濟用語開始成
為政治用語。其實在這之前日本的國民所得早就呈現高度成長狀態。從 1954 年到 59
年的五年之間的國民所得從六兆五九一七億日圓增加到十一兆二三三億日圓,總共
上昇了 67.2%,平均每年成長 10.83%。從 1955 年到 1972 年,每年日本實質經濟
成長率平均達到 9.3%,在這幾年當中,日本的經濟呈現高度成長的趨勢。而這點當
然也反映在日本人的一般生活當中。1964 年日本加入了有所謂先進國家俱樂部之稱
的「OECD(經濟協力開發機構)」,加上同一年舉辦東京奧運會,日本一般國民開
始自覺到自己已經進入了已開發國家。同時,在政治上,日本池田內閣有意將這樣
的高度經濟成長與安保條約作連接,提出「安保效用論」。宮澤喜一於1965年提出:
「就結果而言,(「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使得日本可以將非生產性的軍事支出保

8 第一章 日本的「戰後」和小劇場運動
持在最小範圍,傾全力於經濟發展上面。」5。
高度的經濟成長為背景,使得日本一般民眾將關心的焦點自安保鬥爭以及日美
關係當中轉移到經濟生活上。因此,儘管安保鬥爭運動學生們的激烈抵抗,「日美
安全保障條約」仍然自動生效。就結果而言,70 年代的「安保鬥爭」最終面臨了嚴
重的挫敗。這股在革命的激情過後所產生的挫敗感同時也投影在戰後小劇場運動當
中,形成某種時代的共同氛圍。劇評家扇田昭彥觀察1971年到72年之間的舞台作品,
對於當時作品內容當中所充斥的「黑暗」作如下的陳述:
「首先這的確是外面局勢的『黑暗』在舞台上的投射。以全共鬥為中心
的全國性的校園鬥爭在國家權利的『緊勒』當中被壓制。70 年的安保鬥
爭、三里塚鬥爭、沖繩鬥爭等等,幾乎所有的抗爭全被消滅。看起來像
是這種危機所產生的陰鬱反映在舞台上。但是,在那些舞台上我們所看
見的,我覺得除了政治鬥爭的『黑暗』之外,還有看到自己親手所創造
出來的舞台即將完蛋的這種危機感。客觀地說的話,1960 年代後半以
來,以否定新劇所開創出來的,充滿新鮮活力的戲劇,在那個時點當中,
已經面臨到了一個巨大障礙,我們所看到的,就是自己意識到這點所帶
來的一種黑暗。」6
扇田昭彥所觀察到的 70 年代小劇場當中的「黑暗」,就戲劇內容而言,也許
是「安保鬥爭」挫敗的投射,就戲劇表現形式而言,應當歸因於「形式耗盡」所帶
來的困境。無論如何,扇田昭彥所感受到的「黑暗」,無疑地是日本戰後小劇場的
重要特徵之一。
「安保鬥爭」表面上是「反美」的鬥爭,但其實是反映了戰後日本與美國之間
更為複雜的情感糾結。GHQ 在占領不久立即撤廢在長久以來禁錮日本人民的「治安維
持法」,並且釋放政治犯。為了徹底改造日本軍國主義體制,消除日本人的封建思
想,在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主導下,頒布日本新的民主憲法,實施美
國式的民主教育,並且策動日本天皇向全國人民發佈「人間宣言」,自行撤銷在神
道思想當中天皇的神性位置。日本的「敗戰」以及「投降」對於一般日本人民而言,
5 轉引自石川真澄:《戦後政治史》,東京:岩波文庫,1995 年,頁 98。
6 見扇田昭彦:《開かれた劇場》,東京:晶文社,1976 年,頁 110。

9
第一章
日本的「戰後」與小劇場運動
除了意味著挫折與屈辱之外,同時也帶來了解放與自由。而這種日美之間複雜而扭
曲的情感關係更延續到後來「占領」時期結束之後。就現實的層面而言,「安保鬥爭」
在表面上的「反美」,企圖藉由對於美國的「否定」來「肯定自我」。但是,這種「反」
的構造,正如同大澤真幸所指出,在本質上卻只是反映出日本的戰後,無論是在政
治經濟或者是文化上,已經與美國「同盟」這個無法改變的事實 7。60 年代日本的年
輕人想藉由「反美」來追求自我,而這個追尋自我的行為本身卻透露出「日本=自
我」以及「美國=他者」之間關係的前提。換句話說,日本戰後的自我是成立於「日
美關係」當中美國這個「他者的視線」之上。
在戰後的日本,尤其是在 1955 年的所謂「五五體制」成立之後,「美國化」
成為日本生活上的現實。如同吉見俊哉所指出的:「在日本本土,從 50 年以降,幾
乎是一面倒地將戰後的空間完全面對美國敞開,促進了美國化的消費,這種熱心程
度是在世界其他各地所罕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面對過去的準帝國日
本,發現具備從屬於自己的鏡子的條件,而日本方面,整個社會將美國視為一面優
越的鏡子,同時從面鏡子當中發現重新建構自我認同的可能性。」8。戰後日本,乘
著高度經濟成長的浪潮在生活上急遽地「美國化」,並且透過大眾流行文化滲透到
日本人生活的每一個日常角落。如同戰後日本的流行音樂或者電視節目等文化商品,
「美國」本身已經成為「消費慾望」的對象。吉見俊哉尖銳地指出戰後美國的「占領」
與戰前軍國主義在體制上的「延續性」,「占領」時期在日本廢除「特高(秘密警
察)」,大力推行「民主制度」的 GHQ,在結構上其實延續了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統
治。戰前日本帝國主義的體制,在冷戰這個新的世界局勢之下被換了個姿態溫存延
續下來。日本戰後社會的「資本主義消費文化」過程其實等同於「美國化」的過程,
在消費主義的「鏡像作用」當中,日本以美國為媒介重新再次地進行自我構築。
因此,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視點,在前衛劇場當中觀察到日本戰後「自我認同」
的問題。對於戰後「美國化」的日本而言,「反美」無可避免地必須「內化」,發
展成為「對於自我的否定」。「對於所有現存的體制以及事物加以否定」是前衛劇
場美學所標榜的價值觀,但是這個「否定的美學」在日本戰後前衛劇場當中卻以極
端的「自我否定」現象作為展現。最初,在 60年的「安保鬥爭」當中,這種的「反」
7 見大澤真幸:《戦後の思想空間》,東京:筑摩新書,1978 年,頁 60-63。
8 見吉見俊哉:〈冷戦体制と『アメリカ』の消費〉,《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の文化史9 冷戦体と資本 の文化》,東京:岩波書店,2002 年,頁 58。

10 第一章 日本的「戰後」和小劇場運動
的構造,同時受到「偶發藝術(Happening)」影響,表現在日本戰後的戲劇領域上,
如本章開頭所描述的,首先當然是對於先前既存的戲劇表現形式,以及其背後的體
制所做出的全面性的破壞。到了 60 年代後半所出現的前衛劇場運動,則以開始「新
劇」作為否定對象,以「反新劇」或者「新劇批判」作為他們劇場創作的出發點。
但是,如同扇田昭彥所觀察到的,70年代之後日本前衛劇場的「黑暗」,對於這個「黑
暗」,我們也許可以從 70 年代日本的自我的狀況來解釋。60 年代前衛劇場運動是以
「新劇」作為否定的對象,但是,進入了 70 年代,尤其是在歷經「安保鬥爭」的挫
敗之後,否定的對象從外在的對象回映到自我本身之上,以一種「自我否定」的方
式呈現出來。換句話說,「黑暗」是「敗戰」乃至「安保鬥爭」這一連串日本戰後
情境當中,日本人「自我認同」的過程所呈現出來的結果。
觀察 70 年代日本前衛劇場,扇田昭彥所使用的「黑暗」這個字彙也許只是個
感覺性的形容詞。但本書企圖更進一步地分析戰後前衛劇場的表現形式,從這當中
更具體地描述這個「黑暗性」。並且,本書將從「表演的身體」以及「劇場空間」
這兩個觀點具體的來論述這個「黑暗性」。「暗黑的身體性」以及「陰暗的劇場空間」
是戰後日本前衛劇場的美學之一。藉由對於「身體」與「空間」的分析,我們將更
可以進一步地理解日本戰後小劇場運動當中自我認同的複雜樣態。而這點也是本書
最感興趣的對象之一。
四、以「反新劇」為出發
如同小山內薰「不是歌舞伎,也不是新派劇」這句話所強調的,日本的近代戲
劇「新劇」是以對於它的先前劇種的否定作為出發。與它的前輩劇種「新劇」一樣,
日本戰後小劇場運動也是以「反新劇」或者「新劇批判」作為開始。1969年9月,「演
劇センター 68/69」發表他們雄心壯志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計画 ‧ 第一番」計
畫時,在記者會上,他們向外界公開宣稱「新的戲劇運動」的開始:
「所謂『新』這句話,對我們而言,不只是一句心情的形容詞。換句
話說,我們最終目的在於將作為藝術的新劇,以及作為制度的新劇破
壞殆盡,以此讓非新劇,別種的現代戲劇很具體地呈現出來。」9
9 同註 6。

11
第一章
日本的「戰後」與小劇場運動
「演劇センター 68/69」所批判的「作為制度的新劇」,首先是藉著與「松竹」
等資本體系合作,以及跨足電視劇演出而逐漸走向「大眾化」以及「職業化」的戰
後新劇,在 60 年代所形成的一個在組織營運、演員訓練機構以及劇場使用權上幾乎
形成獨佔的日本戰後「新劇體制」。
1945 年的「終戰」對於新劇人而言,意味著從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壓抑當中
的解放,以及繼續日本近代戲劇發展未完成的使命。1945 年 12 月 14 日,「東京藝
術劇場」在東寶的出資當中創團,以久保榮、瀧澤修、薄田研二為創立者,土方与
志為顧問,這是戰後最先成立的新劇劇團。12月 26日,在《每日新聞》的主辦之下,
於戰爭期間成立的「文學座」、在戰爭末期創立的「俳優座」,以及戰後新成立的「東
京藝術劇場」三個新劇劇團舉行聯合公演,演出契科夫的《櫻桃園》。對於新劇界
而言,這個演出具有重大的意義,戰前的新劇人,除了山本安英、宇野重吉之外,
幾乎都參加了這次的聯合演出。戰後滿目瘡痍的東京,在飢餓襤褸當中共有 9600 名
觀眾前來觀賞這次演出,象徵著新劇在戰後瓦礫當中的復甦。
從 1940 年「新協」、「新築地」兩個劇團在日本政府當局的施壓之下宣佈解
散之後,以理想與苦難所書寫的日本新劇發展史可以說在此告一段落。久保榮因病
療養退出戲劇活動,土方与志被逮捕入獄,導演岡倉士朗被禁止任何的公開活動,
千田是也雖然於 1944 年成立「俳優座」劇團,但是與岡倉士朗一樣所有的公開活動
皆受到限制。整個新劇因政治壓抑而活動停止。隨著戰爭局勢緊張的升高,日本軍
政府實施總動員,新劇當然也在動員之列。1941 年「日本移動演劇聯盟」在「大政
翼贊會」的大會議室裏頭正式宣布成立。其所揭示的目的為:「普及健全的娛樂,
提高國民的信念,樹立國民文化。」10。1945年 8月6日,丸山定夫於移動演劇隊「櫻
隊」的演出活動當中,在廣島遭遇原子彈爆擊身亡。戰爭對於新劇人而言可以說是
在創作以及生命上的雙重壓迫。因此戰爭的結束對於新劇而言無疑地是從桎梏當中
的解放。
1946 年 1 月,「新協劇團」以自朝鮮歸國的村山知義為中心復團,導演土方
与志、八田元夫以及舊新協劇團的演員復歸。3 月,「文學座」舉行戰後第一次公
10 見菅孝行:《戦後演劇》,東京:朝日新聞社,1981 年,頁 41。

12 第一章 日本的「戰後」和小劇場運動
演,演出和田勝一作《河》。同月,「俳優座」演出戈果利(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劇作《檢察官》。1947年 4月,以築地小劇場出身的女演員山本安英為中心,
加上數位年輕演員以鑽研表演藝術為宗旨,成立「葡萄之會」劇團,並且於 50 年代
開始傾注全力於「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的探索。1947年 7月,瀧澤修在《林
檎園日記》演出之後退出「東京藝術劇場」,與宇野重吉、北林谷榮、清水將夫、
岡倉士朗等人,以「提供觀眾彷彿在心中燃起火一般,明亮而且歡樂的戲劇」11 為宗
旨,成立「民眾藝術劇場」。戰後復團的「新協劇團」代表著從「前衛劇場」(1926
年)、「普羅劇場(プロレタリア劇場)」(1927年)、「左翼劇場」(1928年)、「新
築地劇團」(1929 年)以及成立於 1934 年的戰前「新協劇團」等,幾乎於 1929 年
小山內薰去世之後主導整個日本新劇方向的左翼的「社會寫實主義」路線。「文學
座」以及「葡萄之會」則象徵從築地小劇場以來對於表演方法與演員藝術追求的傳
統。「民眾藝術劇場」則象徵著自「大正民主」時期以來民眾戲劇與大眾啟蒙的方向。
從以上動向看來,戰後的日本新劇延續著戰前新劇發展路線以及課題。在 GHQ 所維
持的戰後民主與安定的社會情勢當中,雖然當中仍然發生了 1950 年的「赤色肅清事
件」12,少數的新劇人稍微受到一點波及,除此之外 13,戰後的新劇首次經驗到沒有
檢閱制度以及政治壓迫之下的自由創作。
到了 50 年代後期,日本新劇形成以「文學座」、「民藝」以及「俳優座」三
個大型劇團為中心的戲劇體制。這三大劇團擁有複數的導演以及人數眾多的演員、
專屬的大型劇場(俳優座劇場於 1954 年 4 月興建完成)以及技術人員,宣傳行政等
製作群,以及培養演員的「俳優養成所」14 的龐大組織。從「築地小劇場」以來受盡
壓迫的新劇在戰後日本和平民主的環境當中得到擴展,無論在演出或者觀眾數量上
急遽地擴大,可以說是新劇的全盛期。根據新劇劇團「文學座」的核心人物千田是
也的統計,從戰後到 1955 年的十年間,「文學座」的公演共有 194 次,演出 142 個
11 同前註,頁 59。
12 於 1950 年 5 月,麥克阿瑟發表驅逐日共的聲明,次年 6月,日本共產黨書記被捕,從事電影、新聞 媒體等工作人員只要與共產黨有關者皆被解除職位或者受到相關單位的「關切」,一般稱為「赤色肅 清事件」。
13 如果要說「赤色肅清事件」對於戰後新劇的影響,也許是「三越劇場新劇使用終止」事件。1947 年 以後「三越劇場」成為新劇最重要的演出場地,但是1952年在「葡萄之會」演出木下順二的「蛙昇天」 之後,「三越劇場」突然以經營合理化為理由終止夜間演出,從此斷絕與新劇之間的關係,自此新劇 失去最重要的根據地。另外,「三越劇場」方面並未針對兩者關連性加以說明。
14 戰後戲劇學校最初設立是 1945 年劇團東藝附屬演劇研究所。千田是也於 1946 年設立「舞台藝術アカ デミー」,由千田是也、青山杉作、山川幸世負責訓練。透過「舞台藝術アカデミー」的摸索,千田 是也逐漸形成他『近代排優術』的表演體系,1951年擴大成為「俳優座養成所」,後來成為今天的「桐 朋學園短大演劇科」。

13
第一章
日本的「戰後」與小劇場運動
作品。其中創作劇本共有 99 齣,戰前日本劇作家的戰前作品有 40 齣,戰前日本劇
作家的戰後作品 20 齣,以及戰後劇作家的作品 31 齣。「俳優座」總共公演 93 次,
演出 82 齣戲劇作品。當中創作劇有 66 齣,戰前劇作家的戰前作品有 29 齣,戰後作
品有27齣。戰後劇作家的作品有10齣 15。平均「文學座」劇團每年的公演超過14次,
「俳優座」至少接近 10 次,就劇本創作以及演出的數量而言,比起戰前大幅度地增
加。顯示戰後新劇,無論是在在劇作家的人數、演員的數量、劇團的製作能力與規模,
以及觀眾人數上,比起戰前都有十足的進展。但是,對於戰後新劇的盛況,曾經親
身參與小劇場運動,為小劇場運動奠定論述基礎的評論家菅孝行卻宣稱「新劇的戰
後史並不存在」。他說:
「在戰後思想或者政治的影響之下,新的劇本被書寫出來,符合戰後情境
的舊作品也被重新上演,這些在數量上並不算少。而另外一方面,國粹主
義的戲劇全被清除乾淨。只不過,這些只是在意識型態以及風俗民情上被
置換上戰後的東西,作為一種戲劇的表現性,作為一種與劇場結合的感覺
形式,(戰後新劇)只是戰前新劇原封不動的移植而已。」16
菅孝行所謂的「新劇的戰後史並不存在」,是指儘管在演出以及觀眾數量上的
驟增,戰後新劇並沒有因應「戰後」這個新的文化情境而創造出新的表現形式出來,
反而只是墨守,或者只是延續戰前新劇所開發出來的表現樣態。的確,戰後新劇的
表現形式仍然延續戰前新劇,以「社會寫實主義」作為美學方法與意識型態。但是,
戰前被稱作「社會寫實主義」的表現樣式,主要是面對日本邁向近代國家的腳步,
工業化、資本主義化社會與逐漸增大的勞動階層之間的矛盾日益擴大,面對這樣的
社會情境,新劇人在戲劇創作方法上所作的具體追求,在這當中所獲得的表現樣式。
但是,在「民主化」的戰後,在「冷戰」這種戰後新的世界局勢,「高度經濟成長」
以及「消費社會」所帶來的新的社會結構,以及「敗戰」這個日本人所面臨的新的
情境,戰後新劇並沒有摸索出新的創作方法出來。
不只如此,新劇隨著日本戰後社會「高度經濟成長」而日益繁盛,這點對於小
劇場運動者而言,無異成為「獨佔資本管理體系共犯」。小劇場運動對於新劇的批判,
扇田昭彦作如下描述:
15 見菅孝行:《戦後演劇》,東京:朝日新聞社,1981 年,頁 47。
16 同前註,頁 5。

14 第一章 日本的「戰後」和小劇場運動
「對於他們(小劇場運動)而言,在各種意義上『新劇』已經不是新劇,
也不本著良心來守護的熱情的目標。因為,對於『新劇』創始者們而言實
在很難想像,但是對於這些年輕的戲劇人而言,『新劇』已經如同『後民
主主義』一般,成為與獨佔資本管理體系共犯的一種令人厭惡的補充物,
這樣的共識已經在他們之間存在。」17
1909 年小山內薰受到安東瓦內(Andre Antoine)的影響創立「自由劇場」
(Theatre Libre),為了擺脫商業劇場的束縛,採取「會員組織」的公演方式。
1924 年小山內薰與土方與志創立築地小劇場。正如在一篇〈築地小劇場為何而存
在?〉18 的文章當中所宣示的:「築地小劇場並不是為了現在的築地小劇場而存在,
而是為了未來的築地小劇場。」,小山內薰將築地小劇場定位為「戲劇的研究機構」,
並明白標示出「實驗主義」的方向。到了後來的左翼劇場、新協劇場等以社會寫實
主義為中心的新劇,一方面堅持普羅大眾立場從事戲劇創作,另一方面抵抗軍國主
義政府的外在壓迫。回溯整個新劇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戰前新劇傾向「反商
業主義」、「實驗主義」與「左翼」的意識型態,劇場被認為是與「資本主義」、「商
品主義」等主流社會價值體系對抗的公共領域。但是,戰後的新劇隨著國民所得倍
增,民眾消費能力成長而不斷擴大觀眾人數,這點對於小劇場戲劇運動者而言已經
失去新劇原先與主流價值觀對抗的精神。加上於 1955 年日本電視台開播,新劇演員
頻繁地參與電視劇的演出,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之後,更加深了小劇場運動對於新
劇的批判。
對於小劇場運動者而言,日本的戰後新劇只是「戰前新劇原封不動的移植」,
而未能針對戰後情境創造出新的表現性。而戰前新劇所努力捍衛的「社會寫實主義」
對於戰後的日本社會情境而言已經失去了表現性上的有效性。戲劇研究學者西村博
子更進一步地指出,這種作為藝術表現形式的失效,來自於「安保鬥爭」挫敗感:
「社會逐漸往大家所不期望的方向推進,這種沉重的絕望感,語言終究
不具有任何可以影響人們,改變人們的力量,行動從來未曾改變過現狀,
17 見扇田昭彦〈脱『新劇』運動は何をなしとげたか〉,《現代日本戯曲大系》第8巻,東京:三一書 房,1972 年,解說。
18 見小山内薫:〈築地小劇場は何の為に存在するか〉,《小山内薫全集第六巻》,東京:春陽堂, 1929 年,頁 613-616。

15
第一章
日本的「戰後」與小劇場運動
這種挫折感,在這種年輕人的共通感覺當中,以往新劇藉由描寫現實來
反映歷史辯證的這種方法,急遽地失去其現實性。之後所謂的『小劇場
戲劇』也因此而誕生。」19
對於西村博子而言,1970 年「安保鬥爭」的挫敗感這個戰後情境讓新劇的表
現樣式「失效」。西村博子所說的來自安保鬥爭的「絕望感」或者「挫折感」,其
實我們可以解釋為個人與社會之間失去了本有的關聯性,以及其所帶來的「現實感
的喪失」。如同安保鬥爭運動者對於當時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所抱持的樂觀憧
憬一般,對於用自己的雙手來改變這個社會,這種對於「革命」的「理想」與「樂觀」
原本維繫著安保鬥爭世代與社會之間的關聯性以及「現實感」。但是,安保鬥爭的
挫敗讓這群參與者對於社會失去這種單純的「現實感」。在藝術表現的層面上,如
同西村博子所說,安保鬥爭世代發現:「語言終究不具有任何可以影響人們,改變
人們的力量」,安保鬥爭的挫敗意味著語言的失效。「藉由描寫現實來反映歷史辯證」
這種「寫實主義」藝術所以得以成立,完全建立在這個世界是「可以用語言來描述」
這個暗默的前提之上。但是,1970年安保的挫敗讓「寫實主義」所賴以成立的「言語」
與現實社會之間的關聯性失效,真實世界無法以語言來加以描繪或者表現。語言在
失去其描繪現實世界的「理想」與「樂觀態度」的同時,「社會寫實主義」也失去「現
實感」。因此,我們可以說,戰後的小劇場運動,就是在「語言」或者「寫實主義」
失去其描寫現實社會的效力之後,在這個新的文化情境當中所摸索尋求的戲劇的表
現性。就這點而言,「小劇場運動」的「反新劇」或者「新劇批判」,首先是「反
寫實主義」。
日本戰後小劇場運動的「反寫實主義」當然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於世界蓬
勃展開的「小劇場運動」脫離不了關係。日本戰後小劇場運動受到同時期歐美戰後
劇場運動的影響是不能忽略的。尤其關於沙特(Jean-Paul Sartre)存在主義思
想劇作,布雷希特 (Bertolt Brecht) 的「疏離效果」概念,以及貝克特 (Samuel
Beckett)的劇本《等待果陀》這三者的影響最為深遠 20。戰後歐美前衛劇場被大量地
翻譯介紹到日本,這種熱潮彷彿二十世紀初以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與
易卜生 (Henrik Johan Ibsen) 被大量翻譯引進日本國內的所謂「翻譯劇」時期。關
19 見西村博子:〈初期『小劇場演劇』の特色〉,《園田語文》1996 年 1 月 31 日(vol.10),東京: 園田学院女子大学出版,頁 56-57。
20 川本雄三:〈小劇場演劇の意味〉,《講座日本の演劇8;現代の演劇Ⅱ》,東京:勉誠社,1997年, 頁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