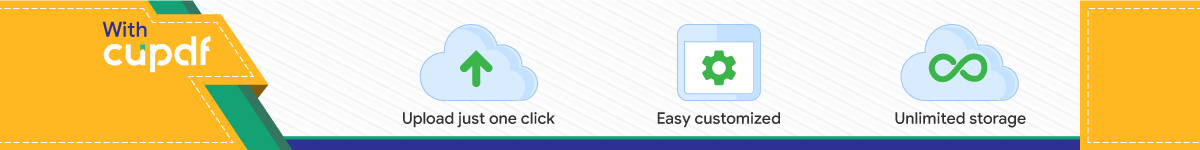

2018年7月14日 星期六 www.xiancn.com
责任编辑陈士娟视觉编辑贾庆华组版马爱贤校对文军10 文 心悦读周刊悦读周刊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槐树底下故事多槐树底下故事多((外二篇外二篇))
◎◎王开林王开林
王磊王磊//摄摄
队里有不少槐树,最大的一棵十几丈高,无论是谁仰望树巅,斗笠不系紧,都准会落地。它威而不猛,代表着乡村的福气和不易形容的庄严。
这棵槐树将虬枝密叶伸展开去,能够荫蔽一两亩地的范围,就算在树底下摆上十张八仙桌,也绝对还有回旋余地。一棵槐树长成这个规模,得经历多少年的风霜苦楚和雨雪欺凌?别说小孩子弄不明白,大人也不知该从何讲起。这棵大槐树究竟有一百多岁、两百多岁,还是更为高寿?队里黄姓、何姓的族谱里都没有明文记载。七八个大人才能合抱的树身,居然空了心,殊不知,这就是槐树的生存之道,它可以长得遮云蔽日,却成不了栋梁之材,因此做屋的工匠提着斧锯从这棵槐树旁边来来回回走过许多回,却从未打过它的主意。做家具的木匠也是如此,他们眼中有槐树,心里却没有槐树。“槐”就是“木鬼”,“木鬼”就是
“鬼木”。华容木匠这样说:“那个鬼木,做什么都不行!”瞧,年深月久,这棵大槐树的好处日益彰显出来,它枝繁叶茂,树冠奇阔,能给众人提供天然的阴凉处所,三伏天,全队男女老少将大槐树底视为避暑乘凉的头号胜地。晴天,晚饭吃得早些,大人小孩络绎而至,不能说争先恐后吧,总归谁都想占个好位置。莫非有人唱戏?没有。莫非有人讲故事?有,我父亲就是主角。
别人讲的是四乡八里的异闻趣事,内容多半只算炒剩饭热剩菜,大家也爱听,也会议论,气氛却不热烈。我父亲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拿捏悬念恰到好处,他讲述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这类老书里的故事,听众反而感觉新鲜奇妙,仿佛身临其境,亲历其事,喜怒哀乐即兴而发。
父亲绘声绘色,讲完武松景阳冈打虎的故事,有人信服,有人不信服,分成两派争论起来。何家二婶子的话最具代表性,她说:
“我家亮子的爹爹爱喝酒,你们是知道的,他力气好大,水牛角抵角打死架,他都能扯得开。可只要喝了半斤八两谷酒和苕酒,他就会醉成一摊稀泥,用铲子都铲不起。真要是老虎赶巧扑过来,别说让他起身打虎,只怕骨头被老虎啃成渣渣了,他都不会哼一声。武松总共喝了十八碗酒,就算他的酒量比我家亮子的爹爹大好多,那还不一样醉成稀泥了,天上劈炸雷都劈他不醒。”
大家争论一番后,没整出个令人心悦诚服的结论,于是都来问我父亲:
“王爹,你说武松打虎这个故事到底靠不靠谱?”
父亲正在抽水烟,每当大家讨论或争论的时候,就是他养神的时候,但他的耳朵并没闲着。
“这叫文学的夸张,不夸张就没有这个效果了。你们想想,武松要是没喝醉酒,挎着朴刀拎着哨棒脚步飞快地翻越景阳冈,就算他碰巧遇上那头吊睛白额猛虎,把它打成肉饼肉酱,也不会显得他神勇无比。写书的人存心要惊吓看书的人,如何把武松的英雄气概和一身过硬的本领百分之五百地展现出来?就非得让他醉个东倒西歪不可,只让他冒险还不行,还要让他在神志不清的时候冒险,做成常人喝蜜喝奶都做不成的奇事来。要是武松喝得醉醺醺的时候,也跟亮子的爹爹一样,天上劈炸雷都劈他不醒,他又如何能够成为一条名震江湖的好汉,让那些恶霸坏蛋闻风丧胆?”
父亲话音一落,大家哄堂大笑,何家二婶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地讪笑着。
空心的大槐树与各种怪异的传说长期纠缠在一起。有人说,树洞里藏着一条水桶粗的蟒蛇,队里丢了鸡,丢了猪,都是被这条蟒蛇吃掉的。谁亲眼见过呢?还有人说,老槐树早已成精,月光明亮的晚上,可以见到树杈上一个趿红鞋穿绿袄的女子荡秋千似的荡着双脚,更神的是她还会唱歌,具体唱些什么?没人听得懂。我在大槐树下打嘚螺,打波,乘凉,总有一百多回,怎么就从来没有见到过大蟒蛇和槐树精呢?好友黄志荣说,大蟒蛇原本就没有;我的火焰高,他的火焰也高,见不到槐树精,也很正常。火焰高就是阳气足的意思。但火焰高的人只是见不到阴森可怕的鬼魂,怎么会见不到妖精?孙悟空的火焰比任何人都要高得多,可是他张眼就能看穿妖魔鬼
怪的原形,觉察到它们的动静。对于黄志荣的这句话我抱有怀疑。
有天晚上,父亲兴致高,接连讲了几个《聊斋志异》中的鬼故事,尤其是那个《画皮》,恶鬼画张人皮披在身上,化成美女,半夜出门,专干剖人腹、掏人心的血腥勾当,令人防不胜防,若不是捉鬼的道士本领高强,根本降伏不了它。这个鬼故事弄得大家毛骨悚然,害怕回家。何队长胆子壮,他说:
“心里有鬼才会怕鬼,心里没鬼怕什么鬼啊!狗不怕鬼,什么恶鬼都怕狗血淋头,你们回家路上,就学狗叫吧。”
这个玩笑起到了压惊的作用,毕竟有不少大狗小狗跟着主人凑热闹来了,回家时,有它们贴身壮胆和保驾护航,就可以放开脚步。
大人们最喜欢的还是《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野猪林》《林冲风雪山神庙》《三英战吕布》《长坂坡赵子龙七进七出》《关公过五关斩六将》这类经典故事。孩子们更喜欢《西游记》,唐僧骑着白龙马,带着三个徒弟去西天取经,沿途各种妖魔鬼怪垂涎欲滴,要吃唐僧肉,孙悟空偏要让他们口水流一地总是吃不成,双方斗智斗勇,孙悟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去天上搬救兵,尽管他费尽周折,但每回都是笑到最后的赢家。这部小说设计得最巧妙又最气人的地方是:孙悟空本事出众、办事得力、救驾有功,却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糊涂师父唐僧,唐僧满肚子的妇人之仁,可是偏偏对这位天神级的大徒弟特别狠心,动不动就念紧箍咒,把孙悟空折磨得死去活来,连个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唐僧眼里人妖不分,上演的总是同样的戏码:先冤枉孙悟空,然后驱逐孙悟空。孙悟空为何不趁机摆脱这个蠢师父,反倒憋着心头的怒火再三再四地将他救出绝境?观音菩萨会做思想工作啊,还有师徒情放不下啊,再就是孙悟空天生就憎恨妖魔鬼怪,不铲除他们心里就不痛快。有一天,黄志荣问了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
“王爹,妖怪要吃唐僧肉就干净利落地吃啊,为什么他们每次都要召集亲友,举行仪式,耽误那么多宝贵的时间?这些可不像是妖怪的作派。”
“妖怪召集亲友,举行仪式,都是为了显摆。你们没看见吗?伍伯在山上打到一只野鸡,都要叫我和何队长去呷酒。”
大家哄笑一阵。伍伯不承认他有任何显摆的意思,他说真要是有唐僧肉吃,吃了还能长生不老,他饱逮之前肯定不会叫任何人来动筷子。就算把它做成酱肉和腊肉,从年头吃到年尾,也不会喊人来打牙祭。
“反正我瞒天过海,不让你们晓得,你们迟早也会晓得,我长生不老啊!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还能看不出来?到那时候,我就是不想显摆都不行。唐僧肉没吃进嘴先大声吆喝,谁作兴这个!”
伍伯的话太在理了,妖怪们臭显摆实在是没有必要,但是我们也要为《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想想,倘若妖怪下手个个稳准狠辣快,取经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可就不容易写到头。唐僧会念紧箍咒,孙悟空不服也得服;妖怪好显摆,现成的唐僧肉,有吃却吃不成。专靠这两大妙招,取经路上的故事才能一难接一难,一环套一环。
父亲在大槐树下讲故事时,我就可以公然偷懒,不用给他的水烟锅装填烟丝,给他点燃纸煤,端茶倒水剥花生壳之类的活计,更不用我沾边,自然有人抢着为他服务。总之,父亲讲故事的夜晚,就是大槐树下的节日。
大槐树上有三个十分显眼的喜鹊窝,每天早晨,成群的喜鹊“喳喳喳”欢叫,岂止是悦耳啊,大家的心情也能好上一整天。我就猜不准,到了晚间,喜鹊们在窝里那么安静,是不是都在听故事?它们高高在上,隔着繁枝密叶,听得清吗?
照妖镜照妖镜
“靠山吃山”,这个说法很在理。小山村有松木、楠竹资源,还出产云母和白石。不过那时候全国尚未改革开放,资源闲置相当普遍,村里有些勤快人利用农闲的日子上山,在这里凿凿,在那里刨刨,何队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视同仁,他不做断人财路的事情,以免招来额外的烦恼。
当年,我只知道白石又叫石英,可用它做玻璃和陶瓷,其实白石的用途很广,至于云母,它可以做绝缘材料。什么是
“绝缘材料”?我一无所知。白石的价格并不高,一百斤只能卖
几块钱,云母的价格要高一些,但产量受到限制。几块钱,十几块钱,现在不算什么,在当年,可不是小数目,补贴家用绝对是妥妥的。
我头一次去开采云母和白石,还不到十岁,央求二姐带我上山。她挑着一担箢箕,箢箕里放着钢钎和锤子,我扛着一把小锄头。在离家两里多地的山肩上,二姐选了个裸露白石的岩坎,下钎凿石。零星的白石易找,成板块的矿脉难寻。上品白石晶洁如玉,中品白石有少许杂质,下品白石杂质较多,供销社基本不收。二姐致力于找寻上品白石,我挖到了中品白石就欢天喜地,心满意足。
云母常与白石伴生,挖到它要有点运气才行,一块云母由许多张薄片叠合而成,这些薄片晶莹剔透,在阳光下熠熠闪亮,能当小镜子使用。有时我会带上几片云母,去学校里送给同学玩,我为这份礼物取了个耸人听闻的名称——照妖镜。云母显影略微有些变形,而且比玻璃镜子要模糊,乐趣就体现在这里,下了课或放了学,我拿着云母照别人,大声咋唬:“妖怪啊!妖怪啊!”我要是用云母照了男同学,他们就会追逐我,要抢夺我的宝贝,必有一番打闹。我要是用云母照了女同学,就会出现几种不同的情形,惹出大麻烦都完全可能。最好的情形是:她嫣然一笑,完全不介意,还说:“照我没用,你应该多用它照照自己!”这样的女生冰雪聪明,不变成花妖,真是可惜了。次好的情形是:她瞪我一眼,扭头走开,嘟哝一声:“讨厌!”最坏的情形我也遇到过,坐在我前排的女生长相介乎丑和很丑之间,但她老喜欢趁老师写黑板的时候扭过头来与我邻座的女同学说悄悄话,三番五次就算了,六番十次我就心烦,于是心生一计,拿出云母照她,尽管我没有吱声,什么难听的话都没讲,但周围的同学人人个个都对我的用意洞若观火,便忍不住哄堂大笑。这下坏了,她居然哭了起来,教数学的张老师也扔下粉笔,走下讲台,他吼道:
“王开林,给我站起来,你在干什么?”
张老师并没看见我已藏进书包的云母,他猜想的可能是我拉扯了前排女同学的长辫子,她受了欺负才哭的。
“他用照妖镜照我!”前排的女同学哭归哭,可不懦弱,来了个恶人先告状,还让周围的同学给她当证人。
“什么照妖镜?快拿出来给我看看!”张老师的怒气倒是消减了不少,脸上似乎还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
我不情不愿地从书包里掏出云母片,交给张老师。张老师好奇地打量了一眼,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这是什么照妖镜?明明是一片云母。”
“他说云母是照妖镜,大家也都这么叫它。”女同学的回答带着咿咿唔唔的哭腔,有点难听。
“张老师,我们班有四十多个同学,王开林用照妖镜照了个遍,你问问他,我们班有多少个妖怪?这是一道数学题。”黄小虎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竟然添油加醋,同学们听了这话,再次笑得前仰后合。
“这件事,我跟你们班主任何老师去说,由他来处理!”张老师没收了我的云母,事后交给了何老师。
班主任何老师对我抱有成见,认定我是个屡教不改的调皮蛋,有一回还批评我是“害群之马”。这下惨了,他
肯定会借“照妖镜事件”给我一个沉痛的教训。
“王开林,你就等着给自己收尸吧!”那位自觉受伤的女同学立刻显得威风凛凛,得意洋洋。
不对啊!就算我有三头六臂,怎么能给自己收尸?她讲这话都讲成了病句,但我无意去纠正她的错误,只为下午的班会提心吊胆。
果然,当天下午,班会的主题就是查明“照妖镜事件”的来龙去脉。何老师让班长李景明先发言,李班长虽不算我的铁哥们,但他为人正直忠厚,这种时候是绝对不会落井下石的。他说:
“王开林玩性重,他带了云母到学校来耍,说是照妖镜,还分送给了两三个同学,大家只是觉得好玩……”
不等李班长陈述完,何老师就用食指重重地敲击讲台,他那老鹰一样严厉的目光扫视全班,他吼道:
“你说什么?他这样做只是好玩?明明丑化了同学的形象,破坏了安定团结,引起了不和,造成了混乱!王开林,你给我站到讲台上来!”
看样子,何老师动了真怒,白脸都变成了黑脸,我只好耷拉着脑袋走上讲台。
“你快讲,你把云母称为照妖镜,是什么意图?是什么居心?”何老师声色俱厉,令我直哆嗦。我的辩解有点滑稽:
“没什么意图,没什么居心,可能是我看《西游记》看得走火入魔了,孙悟空常说妖怪也是人模人样,他有火眼金睛,能看清对方的原形。我崇拜孙悟空,却没有火眼金睛,也没有识破妖怪的本事,就拿云母当成照妖镜,瞎闹着玩。”
我的话音一落,有人发笑,有人交头接耳,竟然还有人鼓掌,这人就是黄小虎,他主动站起来为我作证:
“王开林讲的是实话,我这里就有他赠送的照妖镜,大家纯粹是好玩,没有恶意和坏心眼,是朋友的照旧是朋友,不是朋友的也没有变成仇人,当然啦可能会有个别例外。”
那位丑丑的女同学不干了,她指责黄小虎包庇坏人,与我共裤连裆,这句话有点粗,何老师皱了皱眉头。黄小虎似乎专等她开口说话,好趁机修理她。
“何老师,王开林在课堂上玩照妖镜肯定不对,但要是坐在他前排的女同学认真听课,不回过头来讲小话,违反课堂纪律,她怎么知道背后的王开林在用照妖镜照她?除非她后脑壳上长了一对眼睛;真要是她后脑壳上长了一对眼睛,那不就是妖怪了吗?”黄小虎这话太有趣了,班上同学大笑还不够,竟然有捶桌子的,有打响指的。
何老师将那块云母看了看,好一会儿没吱声,同学们又不得劲了,面面相觑,李班长就站起来告诉何老师,黄小虎讲的是事实。两个人都有错,而且是前排的女同学讲小话,违反课堂纪律,先犯错。于是何老师的脸色由黑转灰,由灰转白,恢复正常,他说:
“今天的事情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反映了同学之间缺乏友爱。她回头讲小话不对,你制止她也行,告诉老师也行,偏要拿个什么照妖镜去照,这不是丑化她吗?伤害她吗?每个人都有自尊心,有的人自尊心强,伤不起的。王开林,你现在向她道歉,她向全班同学做口头检讨!”
说句良心话,何老师这样处理,没给我扣帽子,打棍子,我是心服口服的。他没收了我的照妖镜,还没收了黄小虎的照妖镜,并且规定今后谁也不准许带云母和类似的东西到学校来玩耍,我毫无异议。
那个学期后,我们就升入了初中,我仍然陪二姐挖过几回白石和云母,但我再没有带过照妖镜去学校。黄小虎还为此打趣我:
“听说孙悟空回了花果山,你怎么待在这里?”
我和他相视一笑,何老师没收了我俩的照妖镜,会派作什么用场?这是一个注定找不到谜底的谜。
校内演剧校内演剧
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黄合学校组织文艺表演队,要求高年级每个班各推荐一到两人,班主任何老师推荐了我和女同学何美娇。我们都喜欢演话剧,剧本由文艺表演队负责人徐老师提供,如何分配角色,也是由徐老师拍板。
徐老师个头不高,精精瘦瘦的,眼睛不大不小,但目光炯炯有神。湖南人有一句俗语酷评瘦子,叫作“脸上无肉,做事刮毒”,但徐老师待人很和善,别说什么刮毒了,就连土腔土调的痞话,我都没听他讲过一句。徐老师坚持讲普通话,尽管不太标准,但他从不用方言与学生交流,他要求学生也跟他一样讲普通话,讲不好更要讲,跟着收音机练,跟着广播练,进步就会日益明显。在讲普通话这一点上,我深受徐老师影响,同学中十个有九个讲方言,要是我跟他们讲普通话,就会有人对我翻白眼,还假装没听明白,要我再说一遍。回到家,平日我都是讲长沙话,现在改讲普通话,父亲调侃道:
“这两块钱学杂费交得值,崽伢子练成了干部腔!”这到底是夸奖我,还是嘲笑我?
徐老师熟悉文艺表演队的每名学
生,谁的脾气性格如何,谁有什么爱好特长,无不一清二楚,因此他对各人的角色定位相当准确。比如说,我脾气倔,性情傲,心直口快,比同龄的孩子更具叛逆精神,他就让我在短剧《修课桌》中饰演刺儿头。这部短剧由三个角色演绎,女生小芳是何美娇饰演、班长小强是黄景林饰演,刺儿头小明则非我莫属。
剧情梗概是这样的:小芳与小明是同桌,小明调皮捣蛋,小芳有些讨厌他,不跟他讲话,小明就在池塘里捉了一只癞蛤蟆,偷偷地放在小芳的书包里,结果把小芳吓得哇哇大哭。班长小强将小明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小明怀恨在心,就在留校打扫卫生时,故意将小强的课桌腿弄折。第二天上课时,小强的课桌突然倾倒,他的腿脚被磕伤了。小明暗自得意,满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小芳很细心,她察言观色,认定小明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她就打定主意,先主动跟小明讲和,还邀约小明一同去探望小强。小明担心自己拒绝邀约会引起小芳的不满和怀疑,就勉强同意了。到了小强家,小明看到小强在病床上拆一件旧毛衣,绕着线团,说是天快冷了,这些毛线可以为队里的五保户张爹织一件毛背心。小明问小强:“真稀奇,你还会织毛线衣?”小强回答小明:“我不会织,但有人会织,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直到这时,小明才了解到,小强和小芳一直在做好事,助人为乐,自己却恰恰相反,一直在做坏事,损人不利己,内心顿时羞愧难当。于是他主动请求为小强修理课桌,并且当面向小强说明原委,诚恳道歉。小强原谅了小明的过错,小芳也尽释前嫌,他们三人成为了好朋友。
短剧《修课桌》具有校园话剧的所有特质。尽管情节不算曲折,但三个人的戏分较为均匀,演员通过神情和动作的表演去揭示复杂的内心活动。我演出了小明的狡黠和顽劣,但他在探望小强时深受触动,思想转了个九十度的急弯,由于剧情本身缺乏更充分的铺垫,难免显得有些突兀,不够平滑自然。这部短剧在学校汇报演出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都夸何美娇的扮相好,我的演技高,黄景林的毛线团绕得比皮球还圆。观众长时间使劲鼓掌,这么卖力,很可能把手板都拍痛了。
在《修课桌》之后,徐老师决定趁热打铁,排演另一部独幕话剧《变天账》。剧情是这样的:大陆临近解放时,特务头子胡立名仓皇逃往台湾,逃走的前夕,他留下了一本变天账,是潜伏特务的名册,胡立名的父亲、大地主胡有财将变天账藏匿起来,连他的老婆都对此一无所闻,一无所知。革命群众和当地公安人员已察觉到蛛丝马迹,决心刨根究底。公安局派人将胡有财的院子里里外外每一个角落都仔细搜查了好几遍,还出动了警犬,但那本变天账仍杳无踪影。公安人员审讯胡有财,让他看清眼前的两条路:一条活路,马上弃暗投明,交出变天账;一条死路,抱着侥幸心理,继续矢口否认。正当案情一筹莫展时,胡有财的老婆突患伤寒症,生命垂危,公安局长请示上级,让医院全力抢救,从死亡线上挽回了她的生命。更令胡有财意想不到的是,县里要修筑一条战备公路,胡有财家的祖坟原本在规划图的红线内,必须铲平,现在也特意修改图纸,予以完整保留。这两件事使胡有财深受触动,迷途知返,终于交出了变天账。怎么个交法?这是全剧最高潮的地方,他敲敲脑袋瓜,对公安人员说:“请给我纸和笔,这本账都在我脑袋里记着。”此剧含有强烈的政治寓意,它试图说明:变天账藏在反动派的脑袋里,单纯依靠搜查是找不到的,唯有彻底征服他们的意志,才能迎刃而解。逻辑线没毛病,剧情是否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则见仁见智。
演剧时,我想让好汉扮演警犬,但黄景林抢占了先机,他牵来他家的黑豹充数,黑豹貌似威猛,但性情温驯,有点名不副实,好汉明显要强过它。我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徐老师让我扮演大地主胡有财这个角色。我最想饰演的是公安局长,事与愿违怎么办?徐老师喜欢叫我“小林子”,他对我说:
“小林子,胡有财这个角色对演员的演技要求较高。你想想,他原本是茅坑里的鹅卵石,又臭又硬,但他毕竟不是钢铁斗士,内心是虚弱的,一点点软化后,就不堪一击了。我认为你能够胜任这个角色。”
事实证明,徐老师指导一群小学生排演成人剧,有点过度乐观。《变天账》排演了好几次,效果很差,最终半途而辍了,从未公演过。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稍有差池,比如说对胡有财这个角色拿捏不当,把正剧表演得很滑稽,徐老师就可能招惹麻烦,吃不了得兜着走。
我想来想去,小时候在校园里登台演剧,好处只有一宗:我扮演角色,面对众人,毫不怯场,在其它场合,以真面目接人待物,难度大为降低,什么“离题万里”,什么“语无伦次”,什么“言之无物”,什么“脑袋里面一片空白”,我从未陷身于这种困境中难以自拔。
“自自然然的,大大方方的,不要拘谨,你就知道眼该看哪儿,手该放哪儿,脚该站哪儿,嘴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脸上的表情才会生动活泛,不会僵硬别扭。”
这是徐老师用普通话讲的开场白,至今言犹在耳。谢谢他反复强调,倘若当年他少强调几次,很可能我记忆的大筛子早就将这句话筛得一字不剩了。
Top Rel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