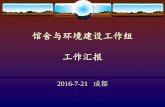本期聚焦 云岭阅读 阅读好人生...
Transcript of 本期聚焦 云岭阅读 阅读好人生...

联大时期中国学人世界与世界观
2019年8月2日 星期五编辑/郑千山 美编/赵行伟 制作/袁文勇 11读书之美
> 本期聚焦
我们一群人夤缘深厚,周末的一个上午,在昆明东方书店的二楼上,有幸聆听著名学者、评论家、画家、收藏鉴定家曹鹏博士谈文化。
曹博士是为他的新书《徐邦达:我在故宫鉴书画》首发式来的。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书画鉴定顶尖级 高 手 的 传 主 徐 邦 达(1911—2012),祖籍浙江海宁,生于上海。生前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杭州西泠印社顾问。其鉴定书画的水平和功力,名不虚传,被业界誉为“国眼”和“徐半尺”(据说徐老过目字画打开半尺就可以下结论)。他鉴定书画的火眼金睛是怎样炼成的?他的人生是怎样的?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徐邦达的书画鉴定为书画鉴定界确立了崇高的标准。当下的书画界,赝品、次品横行,艺术水准参差不齐,徐邦达的存在,让赝品和次品难逃其法眼。
曹鹏介绍,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成立的国家文物局,已具备高水准书画鉴定专业水平的徐邦达成为国家文物局专业分工书画的文物处秘书,而后又供职故宫博物馆,进入国家重点工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为鉴定专家,到各地大博物馆为书画藏品鉴别定级。20 世纪 80 年代后,他还多次应邀出访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参与鉴定了不少海外所藏中国书画。
徐邦达博览古今书画史论著录,一生所过目的书画精品数量惊人,全国省级以上博物馆的书画藏品,他几乎都参与鉴定过。他工作
极其认真,对过目过的字画,他长年坚持记录、查考,在积累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他就书画真伪、书画史、书画家生平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考证,编写出版了多种书画鉴定专业工具书,如《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等等。他参与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的鉴定成果,后来陆续出版为《中国古代书画图目》24卷、《中国古代书画目录》10卷以及《中国绘画全集》30卷、《中国法书全集》18卷。这些都是客观反映中国古代书画收藏家底的基础性文献,为中国书画收藏界所特别珍重。
因为与徐邦达老人多次接触与访谈,曹鹏知道许多徐老的趣闻趣事,比如对书画鉴定对象的过目不忘,比如一生坚持原则却从来没有与人红过脸,又比如爱美食、出手大方,对于在某行业只要有比他更权威的人士在,他一定要谦虚地称自己“不懂”,即便他本人其实也是该行业的
专家……但总而言之,曹鹏认为,活了101岁高寿的徐老已进入了人生的化境,他超凡的书画鉴定功夫,其实与他的人生境界有关,他淡泊名利,又对事业情有独钟。曹鹏说:徐老把书画视为一生的挚爱,把鉴定工作视为技术和品格的考验……徐老一生有三爱——爱书画,爱故宫,爱生活。他活得很纯粹,所以他的业务水准也很纯粹。
“徐邦达骂乾隆是浑蛋,为什么?因为这位皇帝喜欢书画,但每看一幅,他都要钤上他‘御览’的大印,徐老说:这极大破坏了原书画的美,大煞风景……”曹鹏讲述的徐邦达点点滴滴平凡而又传奇的故事,让大家眼前仿佛出现了那位虚怀若谷、充满智慧的老人。
曹鹏曾经是新闻记者和编辑,后来创办《中国书画》杂志,是创始人兼首任主编,出于职业责任和爱好,他曾对启功、黄苗子、王世襄等艺术大家进行过深度追踪访谈,陆
续出版了《大师谈艺录》《启功说启功》《黄苗子说黄苗子》《王世襄说王世襄》《闲闲堂茶话》《闲闲堂书话》等 30余部著作,将各位大师的艺术理念及人生感悟以第一手资料实录下来,这价值连城,不啻为一项利于当代、功在千秋的“文化抢救公益工程”。这次出版的《徐邦达:我在故宫鉴书画》,也是这项工程的一部分。
2008年至2009年,曹鹏曾以中组部“博士服务团”成员身份入滇挂职。他发现,云南不仅自然条件优越,在历史、人文方面也极为独特,只是一直缺乏有力的发现和宣传。在云南,他广泛阅读、研究云南历史文献,寻幽探秘,醉心山水。在云南,他编写了两本与云南有关的书:一本是《云南样样好:第九批博士服务团赴云南挂职散记》,另一本则是《我这一百年:袁思齐说袁思齐》。后来,他还写了云南的茶文化。说起袁思齐,这位去年刚刚以108岁高寿归于道山的百岁老人,是云南书画、篆刻界默默无闻却名副其实的艺术大家。曹鹏认为,袁老的艺术水平精湛,书画艺术质量可居于全国一流水准,但却低调、务实,不慕名利,境高艺自醇。曹鹏找到袁老后,虚心学习,认真访谈,为云南书画界挖掘出了一位值得敬仰、学习的老艺术家,“为往圣继绝学”,他从袁老那里不仅得到了书画实践的新启示,而且还学会了一项快要失传的铜材篆刻技艺,为袁老的艺术理念与实践留下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曹鹏说:“袁老是我人生的一个意外收获,他教会了我很多,告诉我们怎样更好地生活。”
我们感觉得到,曹鹏对云南是满怀深情的。
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主编的“将军文化典藏·散文卷”(10本),最近由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吴传玖散文选》是其中之一。
吴传玖 16岁从著名的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后考上当时被称为“贵族学校”的第三军医大学。1970年在军医大学毕业后,即自愿要求来到云南艰苦的边防部队工作。先到滇西北的迪庆高原——香格里拉当兵锻炼,后到玉龙雪山下的丽江古城,再到有世界第二大峡谷之称的怒江大峡谷。1979年初又同自己任政治部主任的团队奉命调到南疆前线,在老山、者阴山地区指挥作战近十年。最后又调到西藏军区任副政委,成为驻守在世界屋脊上的一位少将。在部队任职期间,他还先后四次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和国防大学深造。他既是在大城市里受过系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干部,又是一个长期工作和战斗在祖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艰苦地区和边防部队的“当兵的人”;既是多次出生入死地参加并指挥过战斗的共和国的将军,又是有良知、有血性、有高度责任感,决心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特别是边防军人热情讴歌、树碑立传的军旅作家。
“迪庆高原少氧的雪,丽江古城多情的水,怒江峡谷酷热的风,南疆边防潮湿的雨,”和世界屋脊上那被
称为“生命禁区”的一座座冰山雪海,都倾注着他深情的爱。从到香格里拉当兵的大学生到共和国的将军,近半个世纪戍边卫国的艰苦历程和传奇故事,给了他不尽的灵感和写不完的题材。在紧张的战斗间隙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迎风冒雪、跋山涉水的行军途中,他争分夺秒,坚持业余写作。写诗,写小说,写报告文学,也写散文,写影视文学,写政治思想教育手册。他至今已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作品400余万字,出版各类著作19部,有些作品在全国获奖,有的散文入选中国散文学会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散文大系》。他最先引起注意并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是 1989年 7月由云南少儿出版社出版,2005年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被选为
“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论著”,并进入 2007年中国现当代诗歌畅销书排行榜的《鲁迅诗释读》。这本列入
“将军文化典藏”的《吴传玖散文选》,就是从他在各地报刊发表的大量散文随笔中精选出来的。
比起小说、戏剧、报告文学作品、影视文学剧本等文学样式来,散文是一种具有真实性、亲切性和随意性的自由自在的文体,是一种更能显示作者才、学、识及其艺术个性和独特风格的文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众美于一身”而显得无
比多样多姿、异彩纷呈的文体。如果说,其他文学样式的作者还可以“藏”在他的人物故事背后的话,那么,散文作者是绝对“藏”不住的,他一藏必假。他必须真实、真诚、真挚地“吐胸中之积愫,诉心底之隐秘”,他必须
“我手写我心。”(朱自清语)。普列哈诺夫说过:“最大的美正是在于真实和朴素,而真实性和自然性是构成真正艺术创作的必要条件。”列夫·托尔斯泰也说:“艺术家的真挚的程度,对艺术感染力大小的影响比什么都大。”
《吴传玖散文选》就是这样一部真实、真挚、真诚地“我手写我心”的文集。80多篇散文随笔,有许多是戍边卫国的战斗故事的,也有写父母亲人和母校、同学的,有写对西安、杭州、大连、青岛、北京、天津、广州、昆
明等城市的印象的,也有写国际题材的,还有写于作家艺术家之间的《文缘》《书缘》和《早》那样的精短杂感等等。总之,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语言朴素,手法多样,而不论写什么,都因为“有我自己”,从自己的切身体会、独特视角、个性感受和真挚感情出发,“我手写我心”,所以能给人新鲜的印象,令人感动,引人深思。
从《香格里拉当兵记》《老兵情》《滇西北军营往事》到《藏北杂记》《我心中那条最美的邮路》,从《峡谷回声》《南疆笔记》到《查果拉哨所记》《岗巴边防巡逻记》《雪域高原上的英烈之魂》,散文选中有 30多篇作品占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作者写自己数十年艰苦戍边的战斗故事和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这些作品不仅真实、自然、朴素地抒写了自己作为一个“当兵的”青年,怎样在祖国南疆、雪域高原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这个大熔炉里,一步步培根铸魂、锻炼成长的生命历程,而且更以真挚深厚的感情、凭刻骨铭心的记忆、精简生动的笔触,为一系列有名有姓的英雄人物树碑立传,热情歌颂了他们身上感天动地、光芒四射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其中有些篇章,特别感人肺腑、震撼灵魂,是最能体现吴传玖艺术个性和独特风格的代表作。
抗日战争期间,由北大、清华及南开三所高校临时组建的西南联大办学八年,在教育、文化、学术、科技等领域,均创造了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后世关于联大史及联大人之研究或回忆性的著作,无疑已是汗牛充栋。但要说到联大时期历史文献的出版,相较而言,则要稀少得多,其中重要的大致有《西南三千五百里》(1939年首版)《西南采风录》(1946年首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卷本,1998年首版)等。2018年出版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张宗和日记》等日记出版物自然也属该范畴之典范。还有,便是云南人民出版社今年6月刚发行上市的《<今日评论>文存》(十卷)和
“民国书刊上的西南联大记忆”(九卷)。作为西南联大曾栖身八年的这片大地,于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终于捧出了必将令全国学界惊艳的丰硕成果,且无一不堪称百科全书级的恢弘史诗。
今天我想重点说的,是煌煌350万字的前者——《<今日评论>文存》(10卷,系“滇云八年书系”之一种,张昌山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联大八年期间,以那些学贯中西、震铄古今的教授们和思想新锐、才华绽放的学子们为主,在连天烽火之中,在教学相长之余,创办了大量报刊,仅刊物,曾系统持续出版、并在国内甚至国际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至少就有《战国策》《今日评论》《民主周刊》《当代评论》《时代评论》《自由论坛》《西南边疆》《边疆人文》及《国文月刊》等九种。这一特殊群体所肩负的救亡与启蒙、继承与创新、表达与引导之重任,便主要藉由这些刊物平台而实现。上面所发表的作品,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固已时过境迁,使命不再,但作为记录和见证历史的珍贵文献,具有历久弥新的永恒价值。
《今日评论》为16开周刊,创刊于 1939 年 1 月 1 日,停刊于1941年 4月 13日,共出版五卷、114期。由西南联大教授钱端升发起并主编,云南大学教授王赣愚协助编辑出版,作者多为联大知名教授,也有进步学子,还有同期活跃于国内国际文化战线和政治舞台的知识分子。他们都以联大为核心,以《今日评论》为阵地,发出自己内心深处关于这个时代的最真实、最铿锵的声音。潘光旦、朱自清、费孝通、罗隆基、陈岱孙、冯友兰、沈从文、钱钟书、陈序经、傅斯年、吴文藻、钱穆……简直就是一份联大精英谱,一份中国联大时期的精英谱!
这份曾远销香港地区及国外的刊物,以指点江山与试图干预、推动国内国际政治的政论为主,亦兼及文史、文学、文化领域。许多作者之间常有激烈的碰撞与交锋,恰集中体现了西南联大思想开放、兼容并包之办学宗旨。在1939年1月8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二期《今日评论》中,有着清华四大哲人之一美誉的潘光旦先生,发表了一篇《抗战的民族意义》。“抗战的最后意义无疑是民族的,而不止是政治的、经济的。”“我们在这里所了解的民族,指的不是笼统的民族的生命,而是这生命所由维持的元气,或活力,或竞存力。抗战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检测我们民族的元气,来量断我们民族的活力或竞存力。”彼时,全面抗战爆发仅一年半,潘光旦便能跳出血与火本身,从民
族长远发展的视角来思考抗战的意义。我联想起大半个世纪后汶川的情形,由潘公之视角观之,大地震的民族意义不也在于它正好给了转型期中国一个机会,来激发本已渐渐迷失乃至丧失的民族韧性和凝聚力?
在深刻分析抗战之艰辛、犀利鞭挞日寇之残暴的同时,许多所收录的文章也具有着强烈的前瞻性,非常有远见地预言了抗战的最终胜利,并不断为战后进行着理论和舆论的准备,《抗战致胜的政治》《战后之整理与建设问题》《抗战建国与地方自治》《战后复苏政策》,等等,便属此类。其中,钱端升教授在《国家今后的工作与责任》中写道:“我们今后若干年内的工作,也就是我们各个中国人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责任,不外抗战与建国。两者是相关的。不抗战,则无国可靠。不建国,则抗战即使获了胜利,这胜利也是极短期间的胜利,难以永久。”“抗战与建国很难截分。抗战时须即建国,建国时或又须抗战。”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那个苦难时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清醒、乐观与睿智,更能窥见这一群体在助推国家与民族发展方面的重要性。这一方面,费孝通于 1941年2月 16日第五卷第六期《今日评论》发表的《农田的经营和所有》则更加典型,文中,这位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学奠基人的学者,对我国农村的农田制度进行了精辟分析,而这种分析,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土地政策重要的理论依据。
以联大师生为主的庞大的作者群体,多出古入今,学贯中西,故其视野并不局限于本地、本国,于国际政治世界格局亦多有观察与论述,而这种观察与论述,往往又与国内战局政局有着某种关联,可互为观照。收录在这套文存中的典范也不在少数,如崔书琴之《论美国对日报复问题》、王迅中之《日本外交政策的检讨》、吴学义之《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观察》、邵循恪之《苏联的远东政策》、陈西滢之《英德战争的观测》等等。联大云南办学的八年,被云南人民出版社称之为“滇云八年”。这,正是该社规划中一个浩瀚体系的总名称——“滇云八年书系”。
丛书主编张昌山在总序中写道:“滇云八年,是艰难而又辉煌的时日。其间成果之多,成就之高,内涵之丰赡,精神之刚毅,特色之鲜明,难寻他例。”这套书的名称和定位,不由让我想到曾在联大研究领域被公认为最珍惜、最具学术价值的那部《联大八年》。2010年,这本只停留于传说中的小册子在尘封近一甲子之后,得以从历史的尘埃中被发掘打捞出来,重新出版,内容是联大刚宣布解散、三校北归之前,部分学生集中创作的关于联大的生活和记忆。其珍贵性和研究的学术价值,便在于其创作的时间、状态与真实历史的同步与交融。因此,显属我在本文开篇所称的非常稀少的联大时期的历史文献。而这套《<今日评论>文存》以及计划中的整套“滇云八年书系”(九大名刊各成一套),无疑,是迄今联大研究及联大时期历史文献中体系最为浩大、价值也最为重大的出版物。从这些弥足珍贵的文本中,我们能够读到联大时期中国学人的世界与世界观,他们的迷茫与探索、思考与观察、呐喊与追求,也尽在其中。
说到乡愁,不能不让人想起读了一辈子的鲁迅先生的《故乡》,想起鲁迅先生倾注在《故乡》的字里行间的乡愁。上小学,语文课本里就有它改写的课文,中学课本又一直把它选作教材,自己不知读了多少遍;当老师,又不知给学生讲述了多少遍。
小说一开始,弥漫在文字里的浓郁的忧伤调子扑面而来:“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地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第二日清早到了家门口,“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那种极具穿透力的个人的特殊感情,有色彩,有温度,有声音,有形象,直击人心。
1919年12月初,临近岁末的一个寒冷的雨夜,为处置祖产,鲁迅从北京辗转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绍兴。此时,周氏三兄弟早已分家,卖掉祖业标志着周氏家族的解体走到了最后一步。因此,小说中一句“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忧伤的调子由此贯穿全篇。老房子已经住了 100多年,变卖祖产在外人
看来,是又一个大户人家败落了,而老宅子里陈年的旧物,处理起来也是颇费一番周折的。许多乡邻前来帮忙,院子里人来人往,在这些帮忙搬家的人群中,便有鲁迅儿时的伙伴章运水,也即小说《故乡》中闰土的原型。
当运水出现在鲁迅面前时,着实让他吃了一惊。这再也不是从前记忆中的少年伙伴了,曾经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曾经的那幅画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以及运水讲述的那些种种趣事,只能在鲁迅的记忆中闪现。而眼前的运水,脸色灰黄,带有很深的皱纹;眼睛肿得通红,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这外表的反差只是第一印象,随之而来运水毕恭毕敬的一声“老爷”,却像一声闷雷在鲁迅的心里激起波澜,令
他不禁打了个寒噤。鲁迅知道,在他们之间已经存在了一条沟壑,“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再也不能如从前那般无拘无束。由“迅哥儿”到
“老爷”,难道仅仅是称呼上的一种变化吗?曾经是活力四射的翩翩少年,到如今已成为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虽然他也想表达自己内心真挚的情感,原本“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中国传统礼法维系的封建等级观念,已深深地在他心中打下烙印,使他不可能挣脱这种无形的束缚,打破“尊卑”界限,一如往昔少年时那般亲密无间。所谓“上尊下卑”,一旦把这种礼法观念当作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那么何谈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是一道冷冰冰的无形壁障,这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将两颗痛苦的心活生生地割裂在世界的两端。这是多么冷酷的现实。正是运水谦卑的这一声轻唤,让鲁迅一下子百感交集,思绪万千,触动很深,察觉了这一谦卑的背后,是中国社会的种种沉重。《故乡》震撼人心,就是
写出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膜,饱含万千愁绪。
一年后,《故乡》问世。以鲁迅亲身经历而创作的这篇小说,于是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也成了乡愁的经典。卡尔维诺在谈论经典时,说过一段同样经典的话:
“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故乡》就是有这样“特殊效力”的作品。说到乡愁,就会让我们想起自己的故乡;说到故乡,就会让我们想到青少年时代几乎人人都读过的鲁迅的《故乡》。
鲁迅是中国现代乡愁书写的开启者,在他的作品里,不止《故乡》,诸如《社戏》《在酒楼上》,分明都写着
“思乡的蛊惑”,透露出深深的乡愁。乡愁是一个人一生对养育我
们的故土无论如何不可能完全挣脱的精神联系,有对已逝美好事物的眷恋,更有失落和悲哀。《故乡》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熟悉而又陌生、隔膜而又依恋的刻骨铭心的乡愁之美。乡愁是悠长的,这种美也是悠长的。
近日,张之道老彝医编著的《彝药本草(上、下卷)》由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2018年 12月版)发行。这部《彝药本草》共收录彝药400种,共74.9万字,分上卷和下卷,全彩色印刷精装。张之道老彝医60年来潜心研究彝医药,从采集的 3000多种彝药标本中精
选出 400种,分成两册,以彝、汉辨析和彝医应用经验,实物药图,汇编成册页,介绍其彝药名、汉药名、主治、用法、用量、文献记载与来源、原植物、识别特征等。图文并茂,是彝医药应用与研究、民间识药用药不可多得的重要著作。
周能汉
《吴传玖散文选》书封
阅读好人生 境高艺自醇——听曹鹏博士谈文化
郑千山文/图
> 新书推荐 用真情以手写心——读《吴传玖散文选》
> 回望经典 乡愁的经典
晓雪
张旗
> 云岭阅读
温 星
《彝药本草》出版> 新书架
曹鹏
《彝药本草(上、下卷)》书封


![金秋迎新之新生阅读书目推荐 - libimg.jnu.edu.cn · 金秋迎新之新生阅读书目推荐 [编者按]: 初入暨南园,新环境,新身份,新角色,你适应了吗?阅读,是大学生必须get的技能之一,进入大学,](https://static.fdocument.pub/doc/165x107/5e14fc5d804e0d3519536706/ececeece-ececeec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