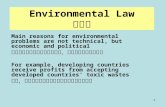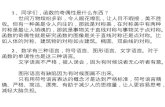一、認識神 從聖經上來認識神 神的屬性 · 馬書5:6-8),這就是神的愛。 1、 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來到世間(約翰福音 1:14)。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決不是半
德希達論正義與法之關聯 - rootlaw.com.t ·...
Transcript of 德希達論正義與法之關聯 - rootlaw.com.t ·...

植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九期 25
德希達論正義與法之關聯
張志銘 台灣大學國發所教授
劉威辰 台灣大學外文所博士生
一 前 言
十九世紀末,奧地利社會學家艾爾利希(Eugen Ehrlich)有鑑於奧匈帝國民間社
會中存在著大量事實上生著效力的法(Recht, jus),相較於國家的法律(Gesetz, lex)毋
寧是一種活生生的法(lebendes Recht; ; lebendiges Recht), 因而深入研究法律的生成
背景, 得到了法(Recht)源於社會,並隨著法律職業的興起而在社會中演進,再而為
國家所接收成為具有實證性的法律,而其在歷史上辯證發展的結果乃成為今天的
法律生活實況,亦即活法艾爾利希的活法理論促成了自由法運動 (Die Freie
Rechtsbewegung) , 強 調 法 律 的 適 用 (Rechtsanwndung) 總 同 時 是 法 律 的 尋 找
(Rechtsfindung),不但直接引領了歐陸法社會學的興起,也間接影響了法詮是學的發
展.。
約在同一時期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蘭德爾(Christopher Langdell)開始著手改
革法學教育;對他而言,法學院應該培養法律人理性思考的能力,而不僅止於製
造司法機器中的小螺絲釘。蘭德爾的「法律幾何學」關心的對象是法律的內緣,
亦即如何將法律事實適用到法律條文的問題。法律人的邏輯思考愈縝密,所得到
的判決也將愈為周延。這種對邏輯的強調、對理性的信仰,很大程度地忽略了法
律的外緣因素。蘭德爾之後,霍姆斯(Oliver Holmes)、法蘭克(Jerome Frank)、
盧埃林(Karl Llewellyn)等人對此多所修正,而有今日的法唯實主義運動(Legal
Realism)。
從法社會學的觀點來看,法律在社會中誕生,在社會中施行,因此也必然是
社會價值的反映。然而,社會更迭的結果,也將使得某些法律不再適用。法律的

26 德希達論正義與法之關聯
歷時性受到重視,連帶地也影響了我們對正義的想像。德希達即認為正義是法律
所排除在外的他者,是不斷後退、無法企及的他者。在這個前提之下,法律似乎
永遠沒有辦法與正義同一。 應該注意的是德希達論法律與正義之關聯之際其心目
中的法(law)乃指廣義的亦即包含法(right; le droit)與法律(law; la loi)在內。
要理解德希達與法(律)的關係,就不得不先談談他的理論及其在法律學門的位
置。論者如沃德(Ian Ward)多將德希達歸類為後現代批判法學的代表之一,這主
要是因為他的解構方法揭露了結構主義二元對立的不足。以下簡要地追溯從結構
到解構的進程,鋪陳德希達的理論繼承與創新,接著研究〈法律的力量〉此一作
品,強調「解構的倫理」、「法律的暴力」(按: Gewalt 一般譯暴力,但在德文中原
為中性,詳下文) 和「正義的可能」三個面向。最後簡短地摘要德希達稍晚的作品
《友愛政治學》,做為對正義和倫理相關問題的解答。
二 由結構到解構
結構主義盛行於二十世紀六零年代的法國,但是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二十世
紀初的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和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普通語言學教程》開宗明義
地表示,語言學研究的對象不應該是某種特定語言在歷史當中的演變,而是所有
人類語言的結構本身。在這個前提下,索緒爾提出了著名的「語言系統」(langue)
和「言語」(parole)的差別。所謂的語言系統,指的是語言構成的結構,而言語
則是每個人運用語言結構所說出來的話。
索緒爾的「語言系統」概念包括、但不僅限於傳統的文法研究;事實上,他
對語言系統的討論是從語言做為符號系統(language as a system of signs)開始的:
The linguistic sign unites, not a thing and a name, but a concept and a sound-image.
The latter is not the material sound, a purely physical thing, but the psychological imprint of
the sound, the impression that it makes on our senses. (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66 ).

植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九期 27
索緒爾強調,語言符號是概念(concept)與聲音圖像(sound-image)的結合,
這也是為什麼當我們聽到一個字的時候,我們可以將這個獨特的聲音和嘈雜的環
境區別開來(因為我們腦海中儲存著這個字的聲音圖像),並進一步驅動我們腦
海中和這個聲音圖像相應的概念。但是這個概念本身沒有意義,意義誕生於語言
符號彼此之間的差異。舉例來說,如果這個世界上只有黑色,那麼黑色就不是黑
色了。黑色這個概念之所以成立,是由於世界上還有灰色、白色等明度相異的各
種顏色,它們之間的差異確定了彼此的存在。
之前我們提到,「概念」與「聲音圖像」構成了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在《普
通語言學教程》裡,「概念」與「聲音圖像」後來被「意指」(signifié,英文為
signified,另譯「所指」)和「意符」(signifiant,英文為 signifier,另譯「能指」)
所取代。這或許是索緒爾理論當中最重要的一組二元對立關係。結構主義的特徵
之一就是二元對立:善/惡、生食/熟食、神聖/污穢等等。二元對立是結構主義認識
世界的方式。透過二元對立的眼鏡,我們所看到的世界是涇渭分明的;然而,這
種認識世界的方式同時也伴隨著風險,因為我們往往會偏愛其中一個、貶低另一
個。
德希達理論的出發點就是對二元對立的批判,更精確地說,他的批判對象是
索緒爾語言學所繼承的意識形態:
The notion of the sign always implies within itsel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even if, as Saussure argues, they are distinguished simply as the two faces of one
and the same leaf. This notion remains therefore within the heritage of that logocentrism
which is also a phonocentrism: absolute proximity of voice and being, of voice and the
meaning of being, of voice and the ideality of meaning. (Of Grammatology, 11).
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在這裡的
作用。意符是聲音符號,意指是概念,它們分別代表了西方形而上學「語音中心
主義」(phonocentrism)和「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的傳統。簡單地說,
西方從柏拉圖以來的哲學家認為人類求取知識的方法就是將外在的物理世界抽象
化,從而得到概念性的規則,因此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論文字學》(Of

28 德希達論正義與法之關聯
Grammatology; De la grammatologie)的英文譯者和著名的後殖民理論學者―才會把
邏各斯中心主義定義為「完全自我意識的自我顯現」(the self-presence of full
self-consciousness)。藉由這個定義,史碧娃克道出了理性長久以來主宰西方哲學
的事實,自我意識的來源是主體對世界的理性認知,而整部西洋哲學史就是理性
的歷史、是理性最完全的顯現。楊大春同意這樣的觀點,他指出:「邏各斯的本
意是言談,而在實際使用中涵意很泛,尤其與邏輯聯繫在一起,談論、說明、思
想、理性、公理、判斷、概念、定義都包含在內…真理的全部形而上學界定都與
邏各斯的要求或在邏各斯血統中思考的理性的要求不可分割」(楊大春<語言身體
與他者當代法國哲學的三大主題>,111-112)。
如果說邏各斯的本意是言談,那麼邏各斯中心主義和語音中心主義的血緣關
係就不言自明了。從索緒爾的脈絡來看,意指和意符是一張紙的兩面,這也就是
說,邏各斯和語音是無法分開的。從思想史的脈絡來看,當人們運用理性歸納出
世界運作的規則的時候,也只有透過語言的方式才能將這些規則表達出來。但是
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無論是邏各斯中心主義還是語音中心主義,都是德希達
批判的對象。
或者我們可以說,德希達反對的是啟蒙理性和它對真理的獨占。啟蒙理性認
為合乎理性的就是真的,不合乎理性的就是假的。這種主張迅速地以科學為名滲
透到各個學科,造成了真理只有一個的錯覺。但是真理並不是單一的,真理是會
隨著觀點不同而改變的。德希達認為,像真理這樣的「超驗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從頭到尾就不存在。所謂的超驗所指,指的是所有能指最後指向的目標,
例如正義、上帝、真理等等,這些概念往往被當成某些論述(法律、宗教、科學)
的根本。為了駁斥超驗所指,德希達提出了在場與不在場的區別。如果超驗所指
真的存在,那麼它們必定是自給自足的獨立存在。這句話的意思是,超驗所指不
需要別的東西來證明它的存在,如果它需要別的東西證明它的存在,那就不能稱
為超驗了。超驗所指的另一個理論預設是它永遠存在。如果它不是永遠存在,而
是處在時間之中、必須經歷生滅的話,那也不成其為超驗了,因為人們將會問「在
它之前/之後有什麼」。這也就是說,超驗所指永遠存在,而且是自己存在的保證。

植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九期 29
用索緒爾的理論來看,超驗所指並不參與任何差異系統,它本身就是差異系統絕
無僅有的特例,是支持整個差異系統運作的軸心,是差異系統的啟動點。
那麼,德希達的在場和不在場的區別是如何推翻這一整套差異體系的呢?我
們已經知道超驗所指的特徵是永遠存在,而且永遠獨立自足,因此,只要我們能
夠證明超驗所指處在時間之中,或是證明它不能單獨出現,就等於是戳破了它所
編織出來的謊言。德希達的方法是這兩種證明的混合。他說,做為在場的超驗所
指不能單獨出現,任何在場都必然伴隨著不在場,因為有在場不在場的區別,有
出現與不出現的區別,所以時間的概念已經在這整個系統裡面發生了。德希達以
此雙重否定駁斥超驗所指的存在。Jonathan Culler 用希臘哲人芝諾(Zeno)的詭辯
為例,說明德希達「在場必然伴隨著不在場」的觀點。Zeno 談到了一支飛行中的
箭,在任何一個時刻,如果觀察者只關注在這個特定時刻的話,這支箭都是靜止
的,所以靜止是這支箭的在場形式。但是在這靜止之中,又隱含有動作的可能,
否則這支箭就不會繼續往前飛了,所以動作是這支箭的不在場形式。完全的在場
是不可能的,連帶地,超驗所指的封閉系統是不可能的,所以邏各斯中心主義/語
音中心主義是有問題的。
從我們的角度看來,德希達一生的著作都是在檢驗各種封閉系統的邊緣
(marges),任何位於系統邊緣的存在都可以用來質疑系統的中心價值。德希達淘
汰了超驗所指的架構,轉而發明了延異(différance)的概念。延異之所以成為延異,
是從 a 這個字母的替換開始的,是 a 給差異(différence)帶來了時間的向度。用索
緒爾的系統來理解德希達的概念,我們幾乎可以將差異等同於 paradigmatic relations
中,各個可互換字詞之間所呈現出來的關係。因此,差異是空間性的、是共時性
的。相較於這靜態的差異,無限後退、不斷推移的延異則是動態的、時間性的。
在繼續往下談之前,有兩點需要進一步釐清。首先,延異這個概念的來源其實有
二,一是哲學的本體論,一是皮爾斯(Charles S. Peirce)的符號學。承襲柏拉圖傳
統的哲學家們認為,萬事萬物都有理型(idea)和表象(appearance)兩個層次。舉
例來說,世界上存在著某種對桌子的極端想像,它包括了屬於桌子的各種美好品
質―桌面平坦、木材厚實、堅固耐用等等。但是在人們生活中,沒有任何一張桌

30 德希達論正義與法之關聯
子能夠企及這個想像,沒有任何一張桌子能夠完全滿足人類的需求。假設有個木
匠,他畢生的心願就是要造出最完美的桌子,於是他四處尋訪合適的木料;但是
我們已經可以想見,就算他找到了百年難得一見的神木,世界上必然還會有比那
更好的。延異的概念有點像這樣,即便表象模仿理型模仿得再像,也不可能成為
理型本身。
在皮爾斯的符號學中,我們也能找到和延異相似的概念。皮爾斯認為符號有
三個組成元素:representamen、interpretant 和 object。皮爾斯和索緒爾最大的差別在
於,索緒爾的 signifiant 和 signifié都不是自然界存在的實體;換句話說,索緒爾的
sign 是完全概念性的,這可以從他將 signifiant 稱為 sound-image(image acoustique)
得知。相較之下,皮爾斯的 sign 則比較偏向自然的存在,對皮爾斯而言,representamen
可以是物質性的聲音(具有音波、音長等物理性質的聲音),也可以是物質性的
存在(自然界中的各種符號)。representamen 可以在觀察者的腦海中產生某種影響
(稱為 interpretant),此種影響同時也可以成為另一個 representamen,使觀察者產
生不同於前一個 interpretant 的 interpretant。皮爾斯稱這種無限指涉的符號學現象為
「the reference ad infinitum」。舉例來說,外在的風向球做為一個符號,被觀察者解
讀為「西風」,而「西風」這一個概念又會影響觀察者,使其產生「秋天來了」
等等想法。這樣子的聯想持續不斷,看不到確切的終點。
德希達認為,延異(différance)的動態概念會造成意義的懸置(aporia),而
意義的懸置則是符號遊戲的契機,是衝破理性鐵牢桎梏的契機,這也是解構的主
要目的。而且,延異一詞中那個看得到、聽不到的 a 也擔負著徹底翻轉西方重語音、
輕書寫的形而上學傳統的任務,這樣的文字學革命將會帶給人們不一樣的未來。
據德希達所說,解構主義不是要以另外一種主義代替現代主義,不是要以非理性
代替理性,而是要把真理從現代主義、結構主義的一元堂中解放出來,讓知識能
夠民主化,這就是德希達所謂解構的倫理。
三 〈法律的力量〉

植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九期 31
在《理論的逃逸》一書中,陳永國給德希達的解構(deconstruction)做了一次
思想上的系譜學考察:「從詞源上說,德里達的『解構』的確源自海德格爾在《存
在與時間》中用的 Destruktion,而海德格爾的 Destruktion 又是從尼采那裡販來的,
英文意思是 demolition,『拆毀,毀壞』的意思。但德里達和海德格爾顯然沒有尼
采那麼徹底,並不想『拆毀』西方哲學傳統。他們的共同興趣在於『翻新哲學』
(innovation)和『重新闡釋傳統』」(理論的逃逸,69)。
德希達本人則是這樣描述他自己的理論工作:我「力圖儘可能嚴格地尊重哲
學原理(philosophemes)或認識原理(epistimemes)的內在的、有規則的遊戲,絕
不曲解哲學原理或認識原理,但又要使它們逐步地發展到毫不適當,山窮水盡而
只得終止的地步。因此,所謂對哲學進行『解構』(deconstruct),可能就是最忠
實地從內部來思考哲學概念的結構系譜,同時根據無哲學資格的或不能在哲學上
命名的某種外部情況來判定這種歷史能夠一直佯裝不知或加以禁止的東西」(《立
場》,6-7)。
所以我們知道,德希達的解構方法既是破也是立,它的著力點在於以哲學本
身的方法去揭露出哲學「佯裝不知或加以禁止的東西」。前面我們已經談過,索
緒爾/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的二元中,總會有一方是被貶抑的(例如「去惡揚善」);
我們談過西方形而上學的理性傳統對思想自由的壓制,也提到了德希達解構方法
的民主、倫理特質。現在就讓我們從法律的角度思考解構的可能性。無論法律的
來源是政府頒布、約定俗成、還是絕對道德,都是以某種「文本」(text)的方式
存在著。這個「文本」不是具有實體的白紙黑字,而是近似於涂爾幹(Emile Durkheim)
「社會事實」(faits sociaux)的概念;而且,因為它以某種文本的面貌出現,所以
它也和語言一樣是符號的系統、是秩序井然的結構。由於法律文本具有強制力,
又是結構性的符號系統,這樣的特質完全符合德希達心目中理想的敵人典型,因
此他將批評的炮火轉移到法律文本上,也就不足為奇了。
〈法律的力量:權威的神秘基礎〉發表在 1990 年第 11 期的《卡多索法律評論》
(Cardozo Law Review)。該文原本是德希達 1989 年在卡多索法學院「解構及正義
的可能性」(Deconstruc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Justice)研討會上的主題演講,分為

32 德希達論正義與法之關聯
上下兩部分,由於時間限制,德希達僅能討論第一部分。一年後,德希達在 UCLA
的「納粹主義與最後解決:探索再現的界線」(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會議上宣讀該文第二部分的內容。刊載在《卡
多索法律評論》的版本完整收錄了兩個部分,並以英法對照的方式出版。有趣的
是,〈法律的力量〉一文本來是以英文寫成的,德希達在研討會上也是以英文宣
讀,後來才被翻譯成法文於 1994 年出版。
事實上,英法文之間的根本差異(或者說,後巴別塔時期語言之間的根本差
異)一直是德希達關心的主題。德希達是這樣開始這篇論文的:
C’est pour moi un devoir, je dois m’adresser à vous en anglais.
緊接著他就把這句法文翻成了英文:
This is an obligation, I must address myself to you in English.
這句英語最大的特點是,它不符合英文文法。正確的英語應該是:
This is an obligation; I must address you in English.
相較於顛三倒四的英文,法文的原句卻是完全合乎法文文法的。我認為德希
達這樣做有三層用意,第一,他強調了 obligation(義務)對他強制力。要在學術
界內發表論文,就必須要遵守學術界的規範。既然大會使用的語言是英文,那德
希達就有義務要用英文。第二,他告訴我們各種語言都有自己的一套符號系統,
完全翻譯是不可能的,因此所有溝通都注定要失敗,即便如此,溝通仍有必要,
因為溝通是打開各個語言系統封閉疆界的唯一方式。第三,法文的句法中,動詞
addresser 的直接受詞是 me(m’adresser),間接受詞是 vous(à vous),而正式英
文中,動詞 address 的直接受詞就是 you。在 je dois m’adresser à vous 和 I must address
you 之間,我們可以看到倫理的向度。在法文中,第二人稱不是第一人稱的受詞,
而是一個介係詞(à)的受詞,但是在英文中,第二人稱就是第一人稱的受詞。換
句話說,英文的句子是很專制的,它將所有的主動權力劃歸給「I」,使得「you」
只能被動地接受宰制。
在這短短的開場白之中,德希達的論述其實已經結束了;他已經講完了自己
的核心關懷,剩下的,只是將這個關懷套用到法律文本的工作罷了。德希達對法

植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九期 33
律文本的看法其實很簡單,兩句話就可以總結:法律權威的誕生靠強力亦即赤裸
裸的強制力量(大會規定用英語報告是一種強力的體現),而法律的維繫也要依
靠強力(英文的主詞動詞受詞語序是很專制的),這個強力就是德希達所說的、
法律的「力量」(force)。德希達特別用德文的 Gewalt 解釋強力一詞 :
在德語中 Gewalt 是指合法權力、合法權威和公共力量。Gesetzgebende Gewalt
是立法權力,geistiliche Gewalt 是精神力量或宗教權力,Staatsgewalt 是國家權威或
國家權力。Gewalt(「強力」)就同時是赤裸裸的強制力量和合法權力或正當權威。
我們如何區分合法權力的法律力量和可能的原始強力?後者[原始強力]必然已
經確立這種權威,但它本身卻不可能被任何先行的正當性賦予權威,因而在這個
最初的時刻它就既不是合法的也不是非法的,或者像另一些人很快指出的那樣,
既不是正義的也不是非正義的。(法律的力量, 415; Force of Law, 926; 927).
法律的確具有權威,而這個權威的來源是法律的力量(force),也就是是正當
性或合法權力(Gewalt);但是在法律剛剛成為法律的時候,在法律還沒有正當性
或合法權力的時候,法律的力量來源就是強力赤裸裸的強制力量(Gewalt)。德希
達的問題因此可以重述為下面這個問題:強力如何/何時轉變成合法權力。
德希達認為合法權力的問題和正義有關,而法律的力量和正義恰好在帕斯卡
(Pascal)的《思想錄》那裡交會:
正義,強力。―遵循正義的東西,就是正義的;遵循強力的東西,就是必要
的。(轉錄自〈法律的力量〉,420 頁)
Justice, force.—Il est juste que ce qui est juste soit suivi, il est nécessaire que ce qui est
le plus fort soit suivi. ( “The Force of Law” 934-35).
這段引言的意思是,正義的東西(ce qui est juste)和強力的東西(ce qui est le plus
fort)是必須要被遵循的,但是同樣的動作(遵循,suivre)卻會帶來兩種不同的評
價:正義的(juste,也可譯為「公正的」)和必要的(nécessaire,也可譯為「強制
的」)。對正義的遵守是出自對公正的渴求,對強力的遵守則是出自強制力的要
求。帕斯卡繼續說道:
正義而沒有強力就無能為力,強力而沒有正義就成為暴戾專橫。正義而沒有

34 德希達論正義與法之關聯
強力就遭人反對,因為總是會有壞人的;強力而沒有正義就要被人指控。因而必
須把正義和強力結合在一起;並且為了這一點就必須使正義的成為強力的,或使
強力的成為正義的。(轉錄自〈法律的力量〉,421 頁)。
La justice sans la force est impuissante, la force sans la justice est tyrannique. La justice
sans force est contredite, parce qu’il y a toujours des méchants ; la force sans la justice est
accusée. Il faut donc mettre ensemble la justice et la force ; et pour cela faire que ce qui est
juste soit fort, ou ce qui est fort soit juste. (qtd. in “The Force of Law”, 936-37)
換句話說,正義和強力是一體兩面、互相成全的。在法律運作的過程中,正義需
要強力對壞人施加壓力、需要強力的強制力量;而強力則需要正義為其背書、也
需要被正義所節制。弔詭的是,當正義從強力那裡的到支持的時候、當正義承認
法律誕生之初的強力的時候,正義就不再是正義了。
正義和強力的關係構成了法律的內在矛盾,而這個矛盾的起源除了法律誕生
之初的強力之外,還有法律權威的神秘基礎(mystic foundation of authority)。德希
達認為,權威的神秘基礎不是某種遙遠而不可及的超驗所指,而是社會生活中自
然而然產生的:
有人說,正義的本質就是立法者的權威;又有人說,就是君主的方便;還有
人說,就是現行的習俗;而最確切的卻是:按照單純的理智來說,並沒有任何東
西其本身是正義的,一切都隨著時間而轉移。習俗僅僅由於其為人所接受的緣故,
便形成了全部的公道;這就是它那權威的神秘基礎了。誰想要追溯它的根脈,就
是消滅它了。(法律的力量, 421-22)。
L’un dit que l’essence de la justice est l’autorité du législateur, l’autre la
commodité du souverain, l’autre la coutume présente; et c’est le plus sûr : rien, suivant la
seule raison, n’est juste de soi ; tout branle avec le temps. La coutume fait toute l’équité,
par cette seule raison qu’elle est reçue ; c’est le fondement mystique de son autorité. Qui
l’a ramène à son principle, l’anéantit. (Force of Law, 936-39).
上面的引文出自帕斯卡《思想錄》,但是德希達認為這些概念其實是從蒙田
來的。他因此轉向蒙田討教:

植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九期 35
於是,法律要維持它的良好聲望,不是因為它們是正義的,而是因為它們是
法律:這就是法律權威的神秘基礎,它們並沒有別的基礎……一切因法律是正義
的而服從法律的人,並不在他應該服從的意義上服從法律。(法律的力,422)。
Or la loi . . . se maintiennent en crédit, non parce qu’elles sont justes, mais parce
qu’elles sont loix : c’est le fondement mystique de leur auctorité, elles n’en ont point
d’autre . . . . . . Quiconque leur obéit parce qu’elles sont justes, ne leur obéit pas
justement par où il doibt. (Force of Law, 938-39).
對蒙田來說,對帕斯卡來說,對德希達來說,法律(loi)都不是正義,那法
權(droit)是不是正義呢?本文在此之前所用的「法律」一詞涵括了法律條文(loi)
和法權(droit),之所以沒有做出區別,是因為在德希達的討論裡,法律從來就不
是單純的條文本身,而是 loi 和 droit、lex 和 jus 兩者的綜合,是和「法」有關事物
的泛稱,如同涂爾幹的「社會事實」。在帕斯卡那裡,至少在相關的討論中,並
沒有 loi 和 droit 的差別,但是在蒙田這裡,正如同德希達觀察到的,法權的概念也
被提出來一併討論了。關鍵是引文的最後一句:「一切因法律是正義的而服從法
律的人,並不在他應該服從的意義上服從法律」(Quiconque leur obéit parce qu’elles
sont justes, ne leur obéit pas justement par où il doibt)。什麼叫做「在他應該服從的意
義上服從法律」(leur obéit justement par où il doibt)?我的理解是,首先,這些人
認為服從法律(loi)是必要的,但是這個必要性是來自於他們對法律(loi)錯誤
的認知:他們將法律(loi)等同於正義了。蒙田的意思是,人們之所以要服從法
律,不是因為法律代表正義,而是因為法律具有其維繫社會發展的功能,同時它
也具有處罰違規者的殘酷力量。遵守法律是我們的義務(obligation),也是我們的
權利(droit);如果法律不存在的話,我們的權利也無法得到保障。總而言之,從
社會的角度來看,法律和法權都是必要的,但是從哲學的角度來看,無論是法律
(loi)或是法權(droit),都不是真正的正義。
總結法律和正義的思考,德希達如是說:
由於權威的起源、法律的基礎和地位在原則上除了它們自身之外就不可能有
什麼依託,故它們自身就是一種沒有基礎的暴力。也就是說,它們本身在「不合

36 德希達論正義與法之關聯
法」的意義上是非正義的。在建立法律的時刻,它們本身無所謂合法與非法。它
們超越了有基礎的與沒有基礎的、基礎主義和反基礎主義的對立。…法律在本質
上是可以解構的,不管是因為它是確立和構成在可以解釋和可以改造的文本層面
(而且這就構成了法律[droit]、法律可能與必要的改造、有時還是修改過程的歷
史),還因為它的最後基礎根本上是沒有基礎的。(法律的力量, 425)。
Since the origin of authority, the foundation or ground, the position of the law [loi]
can’t by definition rest on anything but themselves, they are themselves a violence without
ground. Which is not to say that they are in themselves unjust [injustes], in the sense of
“illegal” [illégales]. They are neither legal nor illegal in their founding moment. They
excee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founded and unfounded, or between any foundationalism or
anti-foundationalism. . . . [L]aw (droit) is essentially destructible, whether because it is
founded, constructed on interpretable and transformable textual strata (and that is the history
of law (droit), its possible and necessary transformation, sometimes its amelioration), or
because its ultimate foundation is by definition unfounded. (Force of Law, 942-43).
這個沒有基礎的法律以暴力開展自己的生命,在歷史中劃開了一道縫隙安
身,並以暴力的方式延續自己的存在。雖說它的出發的可能是對正義的追尋、對
公正的渴望,但是只要它一固定下來,在社會中發生作用,就失去了企及正義的
可能。正義就像是法律誕生之初那被一刀割開的他者,它既是法律的理想自我
(moi-idéal),也是法律的遺憾。
對德希達來說,正義是法律的延異,不是法律的超驗所指。我們已經談過德
希達是如何駁斥超驗所指,又如何以延異的概念取而代之。這兩者的差別在於,
超驗所指的系統是封閉的,系統內所有的存在都會不斷向超驗所指靠攏,但又不
可能完全和超驗所指同一。就好像我們一百公尺賽跑,在跑到終點的過程裡,我
們都必須要通過距離的一半,所以我們先跑到二分之一,也就是五十公尺處,再
跑到剩下來的距離的二分之一,也就是全長的四分之三、七十五公尺處,再來是
全長的八分之七、十六分之十五…我們永遠地朝著終點前進,但永遠都到不了終
點,這就是超驗所指的概念。相反的,延異不在系統裡面而在系統外面,延異的

植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九期 37
存在使得整個系統變得開放,因為這個外在於系統的延異對系統內的各種存在具
有相當的影響力。讓我以一個不很完美的例子說明延異的運作方式:月球。月球
在地球系統之外,但是它對地球上事物的影響力是可以被觀察到的,例如潮汐。
這個例子不完美的地方在於,潮汐是有規則的,但是延異的發展沒有方向可言,
在皮爾斯「reference ad infinitum」的想法中,我們可以看到延異是以近似自由聯想
(free association)的方式存在的。另一個不完美的地方在於,相較於月亮位置的可
預測性,我們永遠不能指出延異在哪裡,因為它是無限後退的、是變動不居的。
將延異的概念套用在法律上,德希達得到了三個絕境(aporias):「規則的擱
淺」(l’épokhè and rule)、「決斷兩難的幽靈」(the ghost of the undecidable)和
「阻隔知識視野的急迫」(the urgency that obstructs the horizen of knowledge)。第一
個絕境告訴我們,如果法官要做出公正的審判,那他就必須再次創造法律,他必
須「既保護法律又破壞法律」(法律的力量 436)。但是這個「再次創造法律」的
信條很有可能會變成規範,限制法官的判斷;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還能說他是
正義、自由和負責的法官嗎?相反地,如果他完全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判決,那
我們也不能說他是正義、自由和負責的法官。第二個絕境告訴我們,「沒有歷經
決斷兩難體驗過的判斷,不可能是一個自由的判斷」(法律的力量 437),換句話
說,我們一定要把所有來自大寫他者的要求(例如意識形態)剷除在外,才能夠
真正做自己的決定。可是,一旦我們做了決定,這個新的決定一定有某些規則可
循,而這些規則將會使得這個新的決定變得不自由、不正義。最後的一個絕境告
訴我們,正義必須是當下的正義,「一個正義的決斷永遠是當下『立刻』的要求」
(法律的力,439-40),可是這個當下性和正義無限後退的特質相衝突,所以正義不
可能和法律共存。
但是我們也不用那麼悲觀,德希達主張,解構方法就是正義的途徑、是倫理
的途徑,我們在前面已經談過這點。對法(律)的解構可以揭露出法(律)的內部矛盾,
將法(律)封閉的系統打開來,讓法(律)壓抑的部分曝光,使得各種不同的力量(政
治、社會、經濟、哲學等等)進入其中,法(律)系統的民主化可以保障個人不受法
律暴力的迫害,讓法(律)與時並進。因此,法(律)的解構是必須的,遵循解構的道

38 德希達論正義與法之關聯
路,正義就會到來(à venir; avenir)。
四 正義在哪裡?倫理如何成為可能?
回到德希達演講的開頭:This is an obligation, I must address myself to you in
English。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德希達對法(律)的態度,也知道他對法(律)、暴力和正
義的想法。如果法(律)是這樣欠缺正義、充滿強力的存在,那麼,我們是不是只能
淪為待宰的羔羊?在法(律)之外,有沒有其他的可能?德希達的答案就在他的「I
must address myself to you」裡面。在這句話中,「你」(you)不是被動接受我的動
作(address)的受詞,而是和主體地位平等的他者,一個活生生的人。像這樣比較
倫理化的態度,也可以在法國女性主義學者伊希嘉黑(Luce Irigaray)那裡看到。
她有一本著名的論文叫做《I Love to You》,書中最重要的論點就是反對男性的主
動和女性的被動,她強調,男女之間應該是平等的,兩方都是人,不應該有什麼
區別。
德希達因此主張要回到亞里士多德的共同體政治理想,也就是友愛(friendship,
amitié)的理想。對亞里士多德來說,政治家的責任之一就是要最大地創造友愛;
他必須要避免不完美的友愛形式,例如奠基在互利的友愛,而專注在能夠達到幸
福(eudemia)的友愛,也就是彼此因其為彼此而締結的友愛(“a genuine friend is
someone who loves or likes another person for the sake of that other person”),是彼此希
望對方能夠幸福的友愛(“wanting what is good for the sake of another”)。德希達
看到當前的民主政治已經不再能夠產生完美的友愛了,所以他語重心長地呼籲:
「喔,我的朋友們,根本就沒有什麼朋友」。對他來說,真正的朋友應該像兄弟,
就如同法國大革命的口號「博愛」(fraternity)一樣:
為什麼朋友應該像兄弟?讓我們夢想這麼一種友愛吧!這種友愛超越了同宗
的兩個人之間的親近感,超越了血緣關係,超越了最自然和最不自然的親子關係,
從一開始它就在名字上留下了它的簽名,就像在這麼一對朋友的雙重鏡像上留下
它的簽名一樣。(友愛的政治學及其他, 4)。

植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九期 39
為什麼像兄弟呢?因為它必須和過度的「感性之愛,愛欲」(eros)區別,但
是為什麼不乾脆就是兄弟呢?因為它必須要擺脫血緣的、命定的結構,必須要將
友愛的親親疏疏擴散到博愛的層次。雖然博愛的概念似乎給民主的困境提供了解
答,可博愛仍然是一種「基督教的兄弟共同體」(友愛的政治學及其他, 370-71),
這種服務於某個封閉領域或是某個超驗所指的概念是有問題的。因此德希達只能
將這種終極的友愛形式寄託在將來,就如同他將對正義的想像寄託在將來:
自由和平的體驗,可能謙恭地體驗這種友愛,而這種友愛最終就是正義,就
是超越法律的正義,以非尺度來度量的正義。我們何時準備體驗這種自由與平等
呢?(友愛的政治學及其他,404)。
引用書目
中文部分
雅克‧德里達著,夏可君編。《友愛的政治學及其他》。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法律的力量:權威的神秘基礎〉。收錄於《友愛的政治學及其他》。
——,楊恆達,劉北成譯。《立場》。台北:桂冠,1998。
伊恩‧沃德著,李誠予,岳林譯。《法律拼判理論導引》。上海:三聯書店,2011。
楊大春著。《語言、身體、他者:當代法國哲學的三大主題》。北京:三聯書店,
2007。
陳永國著。《理論的逃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外文部分
Culler, Jonathan.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Ithaca:
Cornell UP, 1982.
Derrida, Jacques.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1997.

40 德希達論正義與法之關聯
---. “Force of Law: The Mystical Foundation of Authority.” Cardozo Law Review 11
(1990): 920-1045.
Irigaray, Luce. I love to You: Sketch for a Happiness within History. Trans. Alison Marti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Kraut, Richard, "Aristotle's Ethic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10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 =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0/entries/aristotle-ethics/>.
Peirce, Charles S. “Excerpts from Letters to Lady Welby.”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Ed. The Peirce Edition Project, Nathan Houser, et al. Vol. 2.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8. 477-91.
---. “Logic as Semiotic: The Theory of Signs.” Semiotics: 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 Ed.
Robert E. Innis.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5. 4-23.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Ed. 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e. Tr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