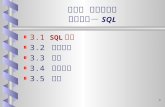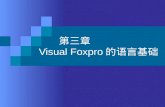《三言》小說中承衍敘事研究 ──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等為例 ·...
Transcript of 《三言》小說中承衍敘事研究 ──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等為例 ·...
-
靜宜中文學報 第五期 2014 年 06 月 頁 123-150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
123
《三言》小說中承衍敘事研究
──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等為例
張怡微 *
摘要
中國古典小說中,隱匿著大量的「重寫」現象。白話小說、話本小說、
擬話本小說的取材常常是從流傳已久的故事中獲得啟發,加以改編而形成各
個版本略有不同的故事。這種改編行為,可能是文學商業化形態之下最早的
類編輯文化。《三言》的成書,從一開始就站立於傳播的角度,使得它更重視
普通讀者而非高級知識分子的審美情趣。
與神話改寫、史乘重寫不同的是,立足於世情秩序的經典重構,處處滲
透著世俗價值的碰撞。本文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為例,在「前文本與重
寫故事群」、「新文本的話語模式探析」兩個面向上,爬梳《三言》中「鼓盆」
故事源流發展及「莊子休」形象再造的意義。通過「試妻」這一馮夢龍從民
間故事中擷取並植入鼓盆故事的佈局,探析改編小說中的「變異」橋段旨在
療癒的讀者文化心理。
《三言》誕生的時代,因其政治、經濟及傳播技術本身的發展,令重寫
問題日益複雜。《三言》中〈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一篇在傳播意義上的成功,
有馮夢龍有意迎合的意圖,也有因其改編後的故事無意間符合世界民間傳統
的審美意趣,從而得以廣泛流傳的必然。
關鍵詞:前文本、重寫、世情小說、莊子休、鼓盆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學生。
-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Providence University Vol. 5, Jun 2014, pp.123-150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Providence University
124
Research on Re-writing phenomenon of in Inherited and Redeveloped from the
Original Fable
Zhang Yi-Wei(張怡微)*
Abstract
Re-writing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 short story of is a well-known re-written one. It based on the fable described by ZhuangZi, and then it was adapted as Chinese Opera in different dialects. The most famous adaption of the fable was in which was written by FengMenglong. And the new story was translated by the French Jesuit missionary 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 in 1735, that was published in France. The story was also one of the earliest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which was translated in western language so far as we know.
This paper try to explore the re-writing issue in , mostly focus on . And it will consist of two parts. A part for < Protext of the Re-written stories>, the other part for <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Newtext>. By close reading, the paper's main conclusions may as follow: First, FengMenglong tried to deconstruct the classics and then put the new values of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Re-written stories of . Second, as a publisher, Feng was not only an editor, but also a bookseller. So that, he considered the needs of the common readers rather than elite readers. And that also became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in his re-writing . Finally, according to Andrew Schonebaum's research,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short stories became 「Fictitious Medicine」. On one hand, the medicine is helpful to the read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ories make the new diseases to readers that could be treated by itself. Thus,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actors beca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Re-writing issue of the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research after the late Ming Dynasty.
* Doctoral Student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National Chengchi Unversity
-
125
Key words:Protext, re-written, the secular stories, ZHUANGZIXIU, GUPENG
-
靜宜中文學報 第五期
126
一、前文本與重寫故事群
中國古典小說中,隱匿著大量的「重寫」現象。累積型小說因此而逐漸
取得了極高的文學成就。最重要的是,累積型的經典文學文本,將中國哲學
中儒、釋、道的時空範疇作為文學敘事的刻度加以規定,日漸形成某種判例,
為後世反復摹寫比照。如經典名著的續書,便是在既有的時空、人物設定框
架之下,為底本注入新的情節或價值觀念。到了明代,經濟、政治等外部社
會的劇烈變化,與出版文化的技術更新,更是為「重寫」這一文學行為增添
了傳播意義上的便利,並創造了新的閱讀維度上的體驗,使得閱讀逐漸能夠
突破士大夫階層的志趣,走入尋常百姓家。
白話小說、話本小說、擬話本小說的取材常常是從流傳已久的文本中獲
得啟發,加以改編而形成各個版本結構、或情節略有不同的故事。這種改編
行為,可能是文學商業化形態之下最早的「類編輯文化」,即通過收集文本、
編纂修訂、營銷發行,以期獲得傳播之後的商業回報。如《三言》的成書,
從一開始就站立於傳播的角度,這似乎和古典文言小說面向知識份子讀者群
的目標背道而馳。甚至大木康指出,《三言》原本就是爲了印刷發表而編出來
的1,預先便將普通讀者作為目標受眾的意圖十分明確,這種眼界和編纂模式
頗具現代色彩2。明清小說史上繁盛的續衍現象也是改編、重寫既有故事的創
作形式,自成一體。「世情」小說因其文學質地的通俗性,則更增添了改編意
圖實現的可能。
荷蘭的杜威‧佛克馬(Douwe W.Fokkema)對重寫問題的思考由比較文學的向度切入,打破了學界原先對於中國文學重寫問題認識的窠臼。他將「重
寫問題」定義為「以前的作家們處理過的題材,只不過其中也暗含著某些變
化的因素──比如刪削,添加,變更──這是使得新文本之為獨立的創作,
1 大木康,〈從出版文化的進路談明清敘事文學〉,《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七卷第三期
(2007 年 9 月),頁 177。作者寫道:「據馮夢龍編的《古今小說》封面的綠天館主人識語,馮夢龍答應了書店老闆的請求而編這部白話小說的集子。也就是說,《三言》原本就是爲了印刷發表而編出來的。」
2 陳翠英,《世情小說之價值觀探論──以婚姻為定位的考察》(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31。文中轉引:「現代文學理論史可以大略分為三個階段:醉心於作者[浪漫主義(Romanticism)和十九世紀];獨鐘於本文[新批評(New Criticism)];近年來則顯然轉而留心讀者。」原文引自 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esota Press,1984,p.74,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臺北:書林出版社,1994 年),頁 97。
-
《三言》小說中承衍敘事研究 ──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等為例
127
並區別於『前文本』(protext)或『潛文本』(hypotext)的保證。3」試圖將「重寫理論」視為不僅僅是技巧的、恆常的文學、文化現象。在他看來,這
是因為「神聖文本的特殊地位在現代已經喪失,它們不再是人們心中的神聖
之物」4。神聖文本在逐漸瓦解其神聖性的過程中,是以何種價值理念解構與
重建,並通過「小說」的方式加以一再呈現、遂成風潮,卻值得我們仔細去
研判。而在這一認知前提之下,《三言》故事群無疑是一個適切的觀察對象。
《三言》的許多故事都有來源。例如:《喻世明言》中的〈範巨卿雞黍生
死交〉脫胎於《後漢書‧獨行列傳》中〈雞黍之交〉的故事;《醒世恆言》中
的〈杜子春三入長安〉其實來自《唐人傳奇》中的名篇〈續玄怪錄〉。另外的
名篇,包括〈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等故事,對後世戲
劇、文學、影視的影響同樣巨大。許多故事被一再改良演繹,順應時風,有
些故事則在流傳中不斷形塑著意識形態與德行教化。唯一不變的就是原初敘
事核中的人物、時空架構和主要戲劇衝突。大量學人曾對經典小說中的人物
原型及故事核加以考據,但「重寫」問題作為一種文學佈置的技法,卻不是
以挖掘故事最初來源作為其絕對價值。對《三言》而言,不斷流變增補的「故
事核」業已成為了不斷流變、累積型的「前文本」,向著未來承衍。好的「前
文本」,影響甚至會大於底本,成為後世重寫主要針對的新「前文本」。5
在前述學者的研究基礎之上,本文並無意對《三言》中所有的故事類型
做原型梳理,而是嘗試從神聖通俗化,及以「夫婦之倫」而展演的審美意趣
為角度切入,分析〈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等名篇中的文學處理,及這種處理
方式在《三言》框架之下有何獨特的指向。
事實上,「前文本」本身的流變,並不在一開始就帶有解構經典的明確意
圖和使命。陳平原在〈小說的書面化傾向與敘述模式的轉變〉一文中提出語
言本身對於敘述流變的影響。「同一個故事,在文言小說家筆下,可能是倒裝
敘述、限制敘事;而在白話小說家筆下,則只能是連貫敘述、全知敘事。6」
3 杜威‧佛克馬,〈中國與歐洲傳統中的重寫方法〉,范智紅譯,《文學評論》1999 年第 6
期,頁 144。 4
杜威‧佛克馬,〈中國與歐洲傳統中的重寫方法〉,頁 145。 5
祝宇紅,《「故」事如何「新」編──論中國現代「重寫型」小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6。「底本」一詞,為祝宇紅所採用。在本文可以理解為考據所得最早的「故事核」,而「前文本」,則是相對於當下研究對象而言最近的一次重寫改造成果。「前文本」是隨著當下文本的流變而不斷流變的。
6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61-262。
-
靜宜中文學報 第五期
128
他例舉《三言》中的八篇小說7,指出白話文體不僅裁剪了前文本中的時間順
序,還補充了諸如主要人物心理活動、次要人物私下議論、及出場人物背景
介紹等描述。白話利於敘事、描寫乃至抒情,改編則發揮了文體本身的長處,
也為世情面向的故事找到了更為適切的寫作容器。
正因如此,考察「重寫型」小說,我們至少要考慮到四個方面:重寫文
本、前文本、作者、寫作語境。除了這些因素,明代以後,「讀者」也是重寫
問題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面向。對前文本的熟悉程度、受眾的閱讀接受心
理,這些都有形無形地影響著重寫者的創作8。故而「重寫」與其說是一種遊
戲策略,不如說是一種侵入底本的文學行為,帶著勢如破竹的技術力量與潤
物無聲的受眾期望。在這背後,不僅有政治、經濟、技術的推動作用,另有
其主觀的價值意圖,不斷地通過解構經典、降格神聖的方式,將底本世俗化、
人情化。本文也旨在這四個面向之上,梳理《三言》故事中的被反復書寫的
故事核是如何呈現其面對前文本及受眾時的文學策略。
7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261-262,八篇依次為 ①明人宋懋澄《九龠集》
中〈珍珠衫記〉一則,結尾一段補述新安人死,其婦為楚人後室。這一情節在《古今小說》卷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則是根據事件發生時間順序,插在小說中間;②唐人牛肅《紀聞》中〈吳保安〉一則,寫到仲翔感激吳保安棄家贖罪之恩,「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然後才追述當初仲翔被俘如何受盡苦楚,幸得吳保安搭救。在《古今小說》卷八〈吳保安棄家贖友〉中,這仲翔被俘受苦一節按時間順序放在前面敘述;③唐人李復言《續玄怪錄》中〈薛偉〉一則,寫薛偉病瘉,自述其夢中化魚,求縣吏釋放無人答理事。而在《醒世恆言》卷二十六〈薛錄事魚服證仙〉中,則從薛錄事變魚寫起,一直到歷盡艱險,醒來重述一遍遊歷;④《原化記》中〈義俠〉一則寫俠客聽仕人述賊負心,方知上當,補說賊如何求他取仕人頭。而在《醒世恒言》卷三七〈李汧公夯邸遇俠客〉中,則先寫賊求俠客殺仕人,再寫俠客無意中聽仕人抱怨方知上當;⑤唐人小說《補江總白猿傳》以歐陽紇為視角人物,從其擄妻軍中,到失妻,到入山尋妻,到殺猿救妻,最後才因得妻而知妻被擄後生兒諸事。《古今小說》卷二七〈陳從善梅失渾家〉則是全知敘事,一會兒寫陳從善,一會兒寫紫陽真人,一會兒寫如春,一會兒寫申陽公,按照事件先後分頭敘述。⑥唐人薛漁思《河東記》中的〈獨孤遐叔〉、唐人李玫《纂異記》中的〈張生〉和唐人白行簡《三夢記》之一,皆以「生」為視角人物,寫其如何於歸家途中見妻子與少年嬉戲,回家追問,方知是闖入妻子夢境。《醒世恒言》卷二十五〈獨孤生歸途鬧夢〉則先述生上路歸;次述白氏思夫,上路尋訪,遇不良少年纏擾;再述生歸途見妻與少年古寺夜飲;最後才是生進家門時,「那白氏心中正自煩惱」。⑦《續玄怪錄》中〈杜子春〉一則,述杜子春如何敗家,如何三遇老者、贈錢,如何入山會老者,如何因愛念未消煉丹失敗……這一切敘述都限於杜子春的耳目和行蹤。《醒世恒言》卷三十七〈杜子春三入長安〉,除結尾外基本保留原作情節,只是敘述時不再堅持以杜子春耳目為限,而是穿插了勢利親戚的內心活動,酒保的私下議論,以及杜子春出走後妻子韋氏的生活狀況;⑧唐人薛用弱《集異記》中〈李清傳〉一則,寫李清七十高齡辭親友入雲門山,此後的敘述限於李清洞中見聞以及被遣歸家後的所作所為。《醒世恒言》卷三十八〈李道人獨步雲門〉則於李入山洞後,補寫眾人如何為李祭奠,此後又三處介紹眾市民如何猜測李之由來,甚至李道人屍解後還補寫朝廷官員的心理、感想等。
8 祝宇紅,《「故」事如何「新」編──論中國現代「重寫型」小說》,頁 7。
-
《三言》小說中承衍敘事研究 ──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等為例
129
首先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一篇為例。
(一)、「鼓盆」故事之承衍概述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9一篇,出自馮夢龍所編著之《警世通言》第二卷。
其中「搧墳」、「戲妻」、「劈棺」等戲劇性元素,被後世擷取、強化並改編成
各種方言的曲藝形式在民間傳播,影響甚廣。《古典戲曲存目匯考》宋元佚名
中錄雜劇《莊周半世蝴蝶夢》,疑與史九敬先所作有關10。元明雜劇闕名中有
《蝴蝶夢》,存明崇禎間的版本,題材已與《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同11。只是,
要到《三言》以後,才有一個比較整飭的故事形態出現並基本確定了下來12。
《三言》之後,〈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故事已經從說書人口中脫胎,成爲了
舞臺化的文本,大多是以浪漫的「夢蝶」抒情開篇,加上戲劇化的「劈棺」
為高潮,再雜糅一些莊子的軼事,隨即成戲。到了後世,《夢蝶劈棺》這一橋
段在很多藝術門類中都有保留與微調,在京劇中有《大劈棺》、《蝴蝶夢》,弋
腔、秦腔、徽劇均有《蝴蝶夢》,而川劇則有《南華堂》。河北梆子有《夢蝶
劈棺》、《莊子搧墳》等,側重點雖不同,但故事情節大同小異13。李良子認
為,「中國古代小說和戲曲的創作中,經常出現同一題材反復出現的狀況,莊
子鼓盆故事就是一個代表。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由於某類故事在流傳中本身具
有的『集體共用型』的特徵,但由於不同體裁的表現手法不同、不同作者的
風格和闡釋不同以及文人的創作心態的影響,這類故事在同樣的框架下呈現
出了不同的面貌,因此也得以在不斷重複中共存」14。
李良子所言的「集體共用型」作為一種重寫型小說的特徵,不僅僅是指
寫作類型意義上的分類,更是一種人人可說、可用、可傳播的改編質地。同
樣一個故事,為何僅僅幾個橋段會被擷取並一再重寫,同樣一組「故」事「新」
編,投入流通市場檢驗,為何每則小說流通範圍、影響力也大不相同。
9 本文所提及篇目〈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引自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北京:中華書局,
2009 年)。 10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614。 11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上)》,頁 657。 12
李良子,〈舊瓶新酒:淺談「三言」與戲曲之敘事關係──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故事流變為例〉,《渭南師範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3 期(2010 年 5 月),頁 38。
13 馬明傑 劉仲武,〈燕趙劇壇一顆星──感受李玉梅〈夢蝶劈棺〉的藝術魅力〉,《中國戲劇》,2004 年第 8 期,頁 18。
14 李良子,〈舊瓶新酒:淺談「三言」與戲曲之敘事關係──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故事流變為例〉,頁 38。
-
靜宜中文學報 第五期
130
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為例,它作為小說個體的命運頗為亮眼。早在
1735 年,短篇小說〈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就由耶穌會傳教士殷弘緒(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翻譯,收入於《中華帝國全志》第三卷,於法國巴黎出版15。殷弘緒在該書中一共翻譯了三篇中國小說,包括〈呂大郎還
金完骨肉〉、〈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和〈懷私怨狠僕告主〉。這也是迄今為止為
人所知最早譯成西文的中國古典小說。1747 年,法國啓蒙大家伏爾泰寫成了哲理小說《查第格》,其中第二章「鼻子」──查第格裝死以試探其妻的故事
情節與〈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如出一轍,伏爾泰之受馮夢龍小說影響明晰可
識16,更可見該小說在傳播學意義上的生命力。〈莊子休鼓盆成大道〉與啓蒙
思潮的關係是別個問題此處暫且不論,但顯而易見的是,該短篇小說的命運
軌跡隨著出版、譯介力量的介入,承衍軌跡頗為奇峻。它代表著明代以後,
因應印刷技術、域外傳播等元素影響,使得小說的流傳已非作者、出版者所
能主宰。小說在歷經了時間、空間的考驗之後,獲得了不同方言、語言、及
不同文化的豐富洗練,遂成為經典,這背後有技術層面、經濟層面的因素,
但小說本身的內在性質中也必有其應然合理之處。
莊周妻死鼓盆的寓言作為故事核,在後世不斷發展。從情節上觀察,其
中包括元明間無名氏作《蝴蝶夢》雜劇,故事結合《莊子‧至樂》篇「莊周
妻死鼓盆而歌」的典故與〈齊物論〉篇「莊周夢蝴蝶」部分情節而成;明人
謝寤雲作《蝴蝶夢》傳奇,計四十四齣,分上下卷,自標目、蝶夢始、歸圓、
赴召終。其中穿插了掃墓、托疾與試妻的幻境。「莊周試妻」的橋段被反復當
做前文本加以裁剪改編,亦是後來《大劈棺》故事的來源17。〈莊子休鼓盆成
大道〉的故事在譚正璧《三言二拍資料》中無記載,但在近年發現的明朝無
名氏的話本小說集《啖蔗》中有錄。《啖蔗》久逸於中土,現有韓國傳抄本存
藏於漢城中央圖書館。其中《叩盆記》一篇,即是馮夢龍〈莊子休鼓盆成大
道〉之所本。
且放眼世界,寡婦搧墳在德國民間故事中亦有原型,偽死試妻在印度、
俄國、歐洲、非洲、中南美等地民間故事中有記載。新寡婦女急於改嫁,從
15 宋麗娟 孫遜,〈「中學西傳」與中國古典小說的早期翻譯(1735-1911)──以英語世界
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2009 年第 6 期,頁 185。 16
蔣向豔,〈從《查第格》看伏爾泰與道家思想之關聯〉,《中文自學指導》,2006 年第 6 期,頁 39。
17 謝易真,〈試探莊周喪妻鼓盆寓言故事的變異與發展──由「妻死」到「試妻」展開〉,《慈濟技術學院學報》第十八期(2012 年),頁 106-107。
-
《三言》小說中承衍敘事研究 ──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等為例
131
而劈棺的故事則在小亞細亞、歐洲等地民間故事中亦有傳播18。在金榮華看
來,馮夢龍不過是將這三個有國際淵源的民間故事傳統合為一個故事融入莊
子的傳說中。但事實上這種說法並不可靠,只能說明世界民間故事中早有類
似被反復演繹的母題19。而莊子鼓盆的故事,又因馮夢龍的改編,成為了新
的「前文本」繼續承衍了下去20。道家的來源,勸世的骨骼,世情的血肉是
馮夢龍改編莊子休故事的大致筆法。但從細部探索,《三言》中馮夢龍為每部
小說所提煉的籠統的教化哲理,又往往會與他實際的編撰意圖相悖,形成荒
誕、遊戲的氛圍。我們不妨細讀來看。
(二)、世俗化的莊子休形象及其重構意圖
在《三言》中〈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的前文本自然與莊子的傳說相關。
但作為哲學家的莊子,顯然和小說裡改編後世俗化的莊子很不相同。作為中
國最重要的精神傳統之一,「道」與儒、釋兩家鼎立,「老子的思想固然影響
很大,但作為情智兼具的形象似乎還是無法與莊子相比並。21」所謂「情智
兼具」,有天道之情、自然之情、友倫之情,但顯然,這些「情」到了《三言》
這個通俗的敘事容器之中卻自然而然被降格了,《三言》故事從不對神聖性負
責,馮夢龍似乎有意為之,《三言》因其訴諸普通讀者的定位而對前文本加以
適當改造。這種改造行為與其說是文學意義上的二度詮釋,不如說還包含了
商業上的妥協。這種妥協使得莊子,或其它《三言》故事中的聖賢形象,濃
縮為民間傳說中的一塊骨骼被加以採用,通過世俗化的改造賦予其靈肉。
《三言》所賦予莊子的身份,首先是個丈夫,其次是一個門外漢眼裡的
古怪哲學家。他的人生故事所指向的,也不是超脫的形而上追求,而是一個
道德的教化訓條。小說兜兜轉轉,說了一場哲學家的悲劇婚姻。小說有意無
意模糊了莊子生於戰國後期的真實背景,《三言》裡的莊周夫婦,無論是生活
情調還是生活道具(紈扇/釵)都顯示出繁瑣、迂迴的日常意趣。
18 金榮華,〈馮夢龍《莊子休鼓盆成大道》故事新探〉,《黃淮學刊》第 12 卷第 2 期(1996
年 6 月),頁 52-53。 19
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 年),頁 356。文中編號 1350【多情的妻子】亦有相似母題,故事情節為:一個人假裝死了,妻子準備嫁給第一個來他家的漂亮年輕人。
20 謝易真,〈試探莊周喪妻鼓盆寓言故事的變異與發展──由「妻死」到「試妻」展開〉,頁 108-109,文中爬梳《三言》之後莊周喪妻鼓盆寓言故事的流傳發展。
21 陳引馳,《莊子精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
-
靜宜中文學報 第五期
132
故事敘述了莊周師事老子後出遊南華山下訪道,途中見一渾身縞素的少
婦持紈扇連搧新墳不輟,遂驚問其故。那婦人道:
「家中乃妾之拙夫,不幸身亡,埋骨於此。生時與妾相愛,死不能舍。
遺言教妾如要改適他人,直待葬事畢後,墳土乾了,方才可嫁。妾思
新築之土,如何得就乾,因此舉扇搧之。22」
因婦人坦誠,莊周深有感觸,甚至還幫婦人一起搧墳。雖然頗感惆悵,
說出「生前個個說恩深,死後人人欲搧墳。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
心23」的名言,但並未反應過激,也沒有試圖教化她。回家後,莊周卻突然
心血來潮,惹妻、激妻、更慾試妻忠心,終心生一計。莊妻田氏,在莊周問
她時信誓旦旦不更二夫,卻在莊周忽然暴病猝死、入殮一周後為不知從哪裡
冒出來的翩翩男子楚王孫撩撥,心猿意馬、迫不及待地要嫁給這位少年秀士。
兩人的勾搭還全在莊周靈堂之上,本就荒唐至極,且莊周屍骨未寒時兩人就
要結婚,竟也沒有為眾人所質疑,甚至還受人撮合幫助。直到洞房花燭之夜,
楚王孫忽然心疼難忍,說必得一新近死者的腦髓熱酒吞之,方能治癒。田氏
立刻尋來砍柴板斧劈棺,要取亡夫莊周腦髓。這時,田氏說了一段刺耳的話,
譏諷莊子為人、睥睨兩人舊情頗不值一提,這一段後文可細講。殊不知那新
歡是莊周行道法分身隱形而來,莊周恰於此時復活,自導自演了一出裝死重
生的鬧劇後,譏嘲妻子一番,最終使其妻愧疚懸樑自縊。由此,莊周悟徹了
一切還返空虛的人生之道,鼓盆且狂飲放歌:「夫妻百夜有何恩?見了新人忘
舊人。甫得蓋棺遭斧劈,如何等待搧幹墳!24」最終,莊周放火燒了屋宇、
砸碎瓦盆,大道成仙。
這個典故出自《莊子》。
《莊子‧至樂》中莊子妻死,惠施來弔唁時,見他不僅沒有悲哀之色,
且正像個簸箕一樣坐著並敲著瓦缶唱歌,惠施指責他「不亦甚乎!」,莊子辯
解: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
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
22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頁 10。 23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頁 11。 24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頁 14。
-
《三言》小說中承衍敘事研究 ──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等為例
133
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
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25」
在莊子看來,人生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人的生命之存在與結束其實不過
是氣的聚散活動而已26。故而妻死根本不值得哭泣,哭也沒有用。但奇怪的
是,惠施死時,莊子的態度卻很不同。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
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
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
言之矣。27」
暫且不論莊子和田氏的感情好不好,但顯然,在同一文本中,莊子對於
惠施的死與對於妻子的死,態度有差。至少在面對惠施之死時,莊子並沒有
「鼓盆」,也沒有以死亡觀為庇蔭來加以刻薄,相反還講了一個動人的譬喻,
以示友倫,讀者可以感受到他莫大的沉痛與失落。28
但到了《三言》中,馮夢龍沒有隻言片語對其友倫的描述,莊子的形象
顯得異常冷漠。簡單來說,《三言》不但降格了莊子形象的神聖性,甚至沒有
給他一個有情義的普通人形象。小說中的莊子夫婦在面對配偶生命存無的態
度和表現上根本就不像是正常夫妻,面對死亡,見識短的女方還知道要裝一
下假惺惺的悲傷做一下場面,境界高的男方索性連悲傷都免去了,大喇喇唱
起歌來還敲打瓦缶。故事最終,莊子通過詐死逼得田氏慘死。難堪至此,回
看小說中還是屢次提及莊周與妻子很「恩愛」,令人感到諷刺。
馮夢龍不是不會寫恩愛,他寫商人的恩愛就要比寫知識分子的恩愛用力
得多,這就是小說中潛在的編撰意圖。如〈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一篇,蔣興
25 郭象注,《莊子》(臺北:藝文出版社,2007 年),頁 345。 26
郭象注,《莊子》,頁 403。見《莊子‧知北遊》:「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
27 郭象注,《莊子》,頁 450。
28 陳引馳,《莊子精讀》,頁 10。文中寫道:(這一段)「真切地體現了莊子的精神取向。他是一個在汙濁的世間堅持自己生活信念的人,他是能夠超越當下的世俗攀求而守護自己本來生命的人。『世俗攀求』中,不僅包括男女情欲,情欲的續接,也有婚姻體制本身。莊子並非一個僅僅對現實持嚴厲態度的人,他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其中最大的樂趣就是與人們展開情智兼具的論辯,而他最好的辯友應該就是他曾嚴加譏諷的惠施。」
-
靜宜中文學報 第五期
134
哥婚後要出門做生意,都能因與嬌妻「成雙捉對,朝暮取樂,真個行坐不離,
夢魂作伴29」耽擱三年有餘。終於決定要走了,不料「淒慘一場,又丟開了30」。
因捨不得對方,「又挨過了二年31」。蔣興哥好容易離家做事,嬌妻三巧兒受
人引誘出軌終被拆穿(與田氏相似),蔣興哥「心中好生痛切32」、「又苦又恨33」、
「悔之何及34」。三巧兒再嫁,蔣興哥「並不阻擋。臨嫁之夜,興哥顧了人夫,
將樓上十六個箱籠,原封不動,連匙鑰送到吳知縣船上,交割與三巧兒,當
個陪嫁。35」旁人也並非當他的作為是尋常禮數,「有誇興哥做人忠厚的,也
有笑他癡呆的,還有罵他沒志氣的,正是人心不同。36」同樣寫夫婦恩愛,〈獨
孤生歸途鬧夢〉中亦有相似描寫。
「耽擱三年」、「又挨過了半年」、「十六個箱籠」……這些描寫足證蔣興哥婚姻內部愛的遺跡,但我們只在田氏回應新歡楚王孫提出的三則忐忑時,看
到她關於自己和莊周夫妻關係的描述:
「這三件都不必慮。兇器不是生根的,屋後還有一間破空房,喚幾個
莊客抬他出去就是,這是一件了。第二件,我先夫那裡就是個有道德
的名賢?當初不能正家,致有出妻之事,人稱其薄德。楚威王慕其虛
名,以厚劄聘他為相。他自知才力不勝,逃走在此。前月獨行山下,
遇一寡婦,將扇搧墳,待墳土乾燥,方才嫁人。拙夫就與他調戲,奪
他紈扇,替他搧土,將那把紈扇帶回,是我扯碎了。臨死時幾日還為
他淘了一場氣,又什麼恩愛!你家主人青年好學,進不可量。況他乃
是王孫之貴,奴家亦是田宗之女,門第相當。今日到此,姻緣天合。
第三件,聘禮筵席之費,奴家做主,誰人要得聘禮?筵席也是小事。
奴家更積得私房白金二十兩,贈與你主人,做一套新衣服。你再去道
達,若成就時,鬥夜是合婚吉日,便要成親。37」
29 馮夢龍編撰,〈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喻世明言》(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3。 30
馮夢龍編撰,《喻世明言》,頁 3。 31
馮夢龍編撰,《喻世明言》,頁 3。 32
馮夢龍編撰,《喻世明言》,頁 17。 33
馮夢龍編撰,《喻世明言》,頁 16。 34
馮夢龍編撰,《喻世明言》,頁 16。 35
馮夢龍編纂,《喻世明言》,頁 18。 36
馮夢龍編纂,《喻世明言》,頁 18。 37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頁 13。
-
《三言》小說中承衍敘事研究 ──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等為例
135
這段話十分重要,首先是田氏毫不經意就提議將莊子的靈柩抬到破空房
裡,這實在和莊子「鼓盆」的冷酷程度比不出個上下來。「人稱其薄德」這句
話出自田氏之口也很有意思。這裡的「人」並不是馮夢龍筆下的眾人,而是
馮夢龍借田氏形容亡夫時所列舉的模糊的人證,很不可靠。頗有意味的是,
作為妻子,田氏似乎也不認為莊周路遇寡婦一事無可指摘。相反,出於女性
本能,她認為事情的真相是「拙夫就與他調戲,奪他紈扇38」。田氏不是沒有
依據,因為小說一開始就說莊周已經結過三次婚了,這種前提的預設,也出
自改編者之手,有其設計上的用心。馮夢龍描寫莊子「心下不平,回到家中,
看了紈扇39」開始喟歎。田氏敬莊子為「先生」,可見還是尊崇禮教,對莊子
的怕和愛交纏。她一見紈扇,「忽發忿然之色40」,卻也不敢直接罵丈夫,只
是「向空中把那婦人『千不賢,萬不賢』駡了一頓41」,這個動作也充滿著婦
人十分逼真的膽怯,她要與這薄情寡婦的德行做對比,更是將自己誇得溫良
恭儉讓。至少在莊子活著的時候,田氏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過錯。她的懷疑是
真、怕是真、壓抑是真、憤怒也是真。她全部的過錯,都發生在莊子死後。
她的戀愛自由建立在不幸福的婚姻自然瓦解的基礎之上。她對於楚王孫愛之
迫切,恰恰可以反映她的隱忍壓抑。而不幸的是,莊周的死卻是一個騙局。
是莊子詐死在先,田氏涼薄在後。後世的戲曲改編中,也可見到民間對這段
故事的評判42。
而針對調戲之說,前文馮夢龍心平靜氣寫的卻是「將纖手向鬢傍拔下一
股銀釵,連那紈扇送莊生,權為相謝。莊生卻其銀釵,受其紈扇。43」這便
是針對同一事件,男女的心理差異,也是夫妻隔閡之淵源。馮夢龍站立於男
性立場解讀這次風波,以示田氏的過激反應。馮夢龍似乎不那麼同情最後慘
死的田氏,但也對莊子幸災樂禍的乖張形貌充滿了戲謔嘲諷。莊周試妻的故
事,也因此發生戲劇性的變異。使後世傳承者誤解莊子思想,不察莊子生死
觀,僅僅並藉著「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結構,投射及反應出「試妻以張
38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頁 13。 39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頁 10。 40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頁 11。 41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頁 11。 42
錢南揚,《戲文概論》(臺北:本鐸出版社,1982),頁 125。據錢南揚的《戲文概論》所述,川劇《南華堂》演這個故事的結局是「玉帝知道了莊周對待妻子的情況,大為不滿,責其無故戲妻,由天仙貶為地仙。把莊周對付妻子的全部圈套,認為是違法行為,完全加以否定」。
43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頁 10。
-
靜宜中文學報 第五期
136
夫權」的觀點44。這不是《啖蔗》中〈叩盆記〉所賦予的變異,〈叩盆記〉故
事精簡,且以敘事散文與詩歌吟唱相間的筆法寫作45。《莊子》一書中,只有
夢蝶與喪妻鼓盆的記載,並沒有「劈棺取腦」以救新歡的情節。是馮夢龍將
之加以鋪陳繁衍,賦予了莊子更具體的負面形象,用意何在呢?
(三)佈局、道具及其隱喻
關於莊子之後的行為,歷來都說他「試妻」,但事實上,說他「戲妻」實
不為過。「戲」在三言二拍中,並不是什麽輕鬆的詞,相反,作為一種推動悲
喜劇情節的絕對助力,往往會帶來讀者意想不到的效果。〈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中,陳二姐為丈夫酒醉戲言所害賠上了性命,還連累了路人崔寧。丈夫劉貴
畢竟也遭賊人之手慘死,只能算無巧不成書。但莊周既沒有喝酒,也沒有真
死,他頂多是不怎麼喜歡自己的妻子,卻設計耍她一番,害她無地自容最終
自盡。他還毫不內疚,甚至鼓盆唱歌。就像田氏分明是硬透了心腸才去劈棺,
被拆穿後竟還能做出「煨熱」行為試圖粉飾。可以說通過閱讀小說,讀者終
於認清了這一對極品夫婦,也印證了所謂一切情緣皆虛妄的道家論調。在此
風波過後,莊子成大道也就在市民的情理上水到渠成了。
馮夢龍恐怕正是深知民間讀者的心理訴求,才寫能寫作出這篇離奇的婚
姻哀歌。在明代重釋經典,擷取《莊子》中的幾則寓言作為藍本,馮夢龍所
要面對的,是《莊子》哲學脫俗的超越境界與普通百姓接受習慣上的矛盾。
莊子所謂的「寓言」,按王先謙《莊子集解》的解說就是「意在此而言寄於彼」。
之所以需要另外說一套,而不直接說出來,《寓言》篇的解釋是:「非吾罪也,
人之罪也。」正是因為莊重的言談,出於種種不那麼恰當的世俗理解,往往
無法為人接受,所以《莊子》要用「寓言」來表達,用「天下」篇裏面的話,
就是「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46」莊子的境界與普通百姓的理解之間
遠隔千山萬水。而莊子寓言的真意對於普通百姓來說,也過於高深和隱晦。
44 謝易真,〈試探莊周喪妻鼓盆寓言故事的變異與發展──由「妻死」到「試妻」展開〉,
頁 107。 45
季羨林等整理,《韓國藏中國稀見珍本小說-啖蔗》第 1 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 年)頁 229-230。〈叩盆記〉故事:「夫妻百夜有何恩,見了新人忘舊人。甫得蓋棺遭斧劈,如何等待搧乾墳。莊生又曰:「教你看兩個人」。用手一指外面,田氏回顧,只見王孫與蒼頭踱將過來,吃了一驚,轉身不見哪有甚麼王孫、老蒼頭皆莊生分身隱形之法,田氏自覺無顏,解帶自縊。莊生見田氏已死,解將下來,就將劈破棺中盛放了,把瓦盆為樂器,鼓之成韻,倚棺而做歌。」
46 陳引馳,《莊子精讀》,頁 32。
-
《三言》小說中承衍敘事研究 ──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等為例
137
馮夢龍的初衷僅是爲了圓「鼓盆」之說,採用民間故事所喜歡的橋段加以嫁
接、虛構,以豐富故事情節。
從結構佈置上來看,開篇馮夢龍將「夢蝶」之說粗略帶過加在小說人物
的輪廓上與其它戲劇改編形式類似,但隨後就佯裝平淡地描述了一個現實中
的「莊周」前史:「雖宗清淨之教,原不絕夫婦之倫,一連娶過三遍妻房。第
一妻,得疾夭亡;第二妻,有過被出。47」,且不論這種描述中是否有戲謔顛
覆的意圖。田氏因怒而斥責莊子時道:「似你這般沒仁沒義的,死了一個,又
討一個,出了一個,又納一個。48」而後撕碎了「紈扇」。過了幾日,莊周發
病時,分明是要死的人,竟還不忘記說「可惜前日紈扇扯碎了,留得在此,
好把與你搧墳。49」可見,在馮夢龍的設計裡,莊周還真的惦記著那把「紈
扇」。以至於這整件事情的因果鏈,變得像是莊周對於妻子撕扇的不滿和復
仇。
在田氏看來,莊周路遇寡婦是一件不太妙的事,兩人還因此「淘了一場
氣50」。「淘氣」這一說法其實很有意味。「紈扇」像是一個信物,但又不確切
直指莊周與寡婦的因緣。田氏心有醋意,索性淘氣地毀了這件莫須有的信物。
設想莊周要是收下了寡婦的「銀釵」,事態還將演變成什麼樣。但毫無疑問,
莊周對這種夫妻間的「醋意」調情是不領情的,小說也無意要借此彌合兩人
的愛情。至少,「紈扇」搧亡夫這一細節確鑿,確立了「紈扇」作為一種嘲諷
夫妻關係的重要道具,強化了戲劇衝突,成為引發夫妻矛盾的導火索。「紈扇」
那麼「甜美」,象徵愛情,又致命地摧毀了愛情,帶有符號化的隱喻,香港學
者黎必信甚至詮釋道,「文中用以搧墳的『紈扇』為田氏所毀,而用以『斧棺』
的斧頭雖未被破壞,但夫妻之情卻因而破裂至無可挽回的局面,無獨有偶,
其破壞者實亦田氏本人,與紈扇之破滅亦正好對應51」。「紈扇」的出現與消
失,就像是一個厄運信號的來臨。
劉祥光在〈婢妾、女鬼和宋代士人的焦慮〉一文中曾經明確地指出,唐
宋故事裡對「來路不明的女子」是有其敘事淵源的52。路上出現的身份不明
47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頁 10。 48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頁 11。 49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頁 11。 50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頁 13。 51 黎必信,〈對應敘述與經典重釋──論〈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的主題建構〉,《中國古代文學
研究》2009 年第 4 期,頁 58。 52
劉祥光,〈婢妾、女鬼和宋代士人的焦慮〉,《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臺北:東華書局,2005 年),頁 9。
-
靜宜中文學報 第五期
138
的女子,往往預示著男主人公悲慘命運的開始。在〈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一
篇中,無論是那位從天而降的搧墳婦人,還是那位軟弱的、貌美的楚王孫都
屬於這一類隱喻的符號,是需要抵制的、孱弱貌美卻身份不明的威脅。馮夢
龍藉助這種民間邏輯幫助莊子在凡塵完成了「吾喪我」的哲學命題,由人而
入天。由一點一點喪失自己所擁有的一切,而得成大道。
從「搧墳」的炎涼,到「劈棺」的惡薄,再到「鼓盆」的生冷,傳遞了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一篇對於夫妻關係「剜肉粘膚,可離可合53」的認知。
與其說莊子本人真的那麼冷酷、田氏真的沒有三巧兒好命嫁得到如意丈夫,
不如說在《警世恒言》中的「莊子」只是一個象徵,代表了俗常百姓對於莊
周遁世哲學及超越性生死觀的幻想與不諒解。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中曾
經尖銳質疑道:「莊學的根本目標是否欲使人心成為石頭?54」但眾所周知,
莊學對於死亡的達觀,雖然具有甚高的境界,但遠超常情之外,不是一時即
可為人接受的。在《三言》這一常描寫、頌揚「多情」、「飲恨」、「遺恨」、「薄
情」等塵世間恩怨的敘事容器中,莊子休的超越性思想實在是有些格格不入。
莊子遠超常情的哲學境界,看在普通百姓的世界裡,往往是難以理解、甚至
有些絕情的。正因如此,老百姓們解釋不了莊子「妻死鼓盆」的典故,就只
能借由馮夢龍創造〈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將之說圓了。馮夢龍深諳其道,增
添了大量的因果鏈作為細節植入故事底本,進行邏輯逆推。在這個改編故事
中,莊子哲學的真意是不重要的。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文本再造背後的社會
依據,馮夢龍如何解構神聖、為何要如此大刀闊斧將知識分子形象荒誕化,
卻將商人形象加以美化,恐怕都可以從他個人的仕途經歷、明代社會的政治
經濟狀況中找到依據。
一方面,馮夢龍一生在科舉上不得意,57 歲才補了貢生,61 歲被選任為福建壽寧知縣。因此,他發憤著書,將大半精力貢獻在蒐集、整理通俗文
學的事業上。馮夢龍將前人說書的底本〈叩盆記〉加以潤飾成〈莊子休鼓盆
成大道〉,這是一篇揉合庶人說書與文人賦詠、整理的一篇民間通俗小說。加
以在中國古代,一般百姓讀書無幾,他們的知識多半口耳相傳,往往得諸娛
樂性的俚歌俗曲和說唱戲劇。而這些「說書」的講唱者,他們將故事的「基
形」加以觸發聯想的能力是豐富的,附會誇飾的本事更是極盡發揮55。
53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頁 9。 54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211。 55
謝易真,〈試探莊周喪妻鼓盆寓言故事的變異與發展──由「妻死」到「試妻」展開〉,頁 112。
-
《三言》小說中承衍敘事研究 ──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等為例
139
市井起源的複雜也正在於明代市民社會的興起帶動了群體經驗結構的轉
型。公共空間的開展,意味著小說總難免帶有世俗消費的取向與趣味。對於
世俗因果報償的群體性耽溺,在後世改編的戲劇唱詞中顯得尤為明顯。以莊
子休的故事為例,後代承衍如改良京劇《蝴蝶夢》中,就有一句「莊生空言
齊物論,不責男人責女人!」而在河北梆子《夢蝶劈棺》中,更有一句「寡
婦搧墳無情義,先生留扇欠思忖」索性把民間道德律的是非做了更明確的研
判。
只是用這樣俗世格調的情節作為傳播的代價,一方面降格了莊子學說的
真正意味,但也凸顯了莊學與民心之間的鴻溝。黎必信指出,「這種將嚴肅的
哲學命題轉換為淺顯的因果關係的結果,使小說更貼近民眾的水準。馮夢龍
原意既非宣揚教義,而只考慮小說的教化作用,故其改動相對更著眼於小說
的趣味性上。56」我們更可以大膽推斷《三言》中的所謂宗教、聖教故事,
都只是帶著教化面具的世情故事,它歸根結底並不指向「教」本身。無論是
道家成仙,還是佛家成聖,都是馮夢龍說故事的一種修辭、技術及手段。為
的是滿足俗眾追求自由、金錢、長生不老等人間願望的訴求。
事實上,《三言》說來說去說的最好的,還是人與人之間的糾葛,人的命
運與偶然性的衝突,人的處境與義理道德的矛盾。正如許懿豐在〈譎詭幻怪—
《三言》幻異故事研究〉中總結的:「世情作品必定奠基於俗世社會,所描述
的情境亦多為生活周遭耳目所及,故亡者托夢顯靈,夢魂出遊呈現的景象並
未逾越人間此一空間界域,此亦是世情類作品與其他宗教、歷史類著作的極
大差異。57」
樂蘅軍在談到自己對於古典小說研究的進入時曾經說過:「小說總有一面
是讓人放在一般人生見地上去談的。從小說敘事所呈現的人生景象上,領略
人生中鹹酸之味,以致鹹酸之外。要之,總不外乎是從人存在的情境中看人
生故事。這看法可能是沒有章法的,但誠如理論家說的,作品中總有些反復
出現的意象而至主題,而這就是我們探知小說中人生情境的引導地圖58」。《三
言》中的故事,無外乎都指向了千變萬化的「人生情境」。
56 黎必信,〈對應敘述與經典重釋──論〈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的主題建構〉,《中國古代文
學研究》2009 年第 4 期,頁 58。 57
許懿豐,〈譎詭幻怪—《三言》幻異故事研究〉,(臺北: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藏碩士論文,2004 年),頁 20。
58 樂蘅軍,《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3 年),頁 15。
-
靜宜中文學報 第五期
140
故而萬變不離其宗的,是以人情為中心的敘事脈絡。莊子休形象的再造,
充滿了世情生活中夫妻之倫的細節描摹。馮夢龍試圖將筆下的哲人、聖人、
仙人,都置於小老百姓會面對的道德困境中。至於哲、聖、仙的精神風貌,
反倒只是表現為某些異於常人的表現作為豐富小說情節的修辭,不再去做更
深層次的追究。這樣一方面能迎合說唱、書籍的商業需求,另一方面也促進
了民間故事改編的蓬勃發展。
二、新文本的話語模式探析
(一)解構與反諷
李良子所言之「集體共用型」,在〈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的傳播過程中的
應驗並非偶然。西方文學中就有「醒世寓言」(parable)之源流,是基督最擅長的一種訓導方法。馬克‧特納(Mark Turner)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認為,「醒世寓言」是「用一個故事影射另一個故事」或其它許多故事,不論這種
影射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在廣義上,醒世寓言不僅僅是一種文學或教誨手
段,還是一種「基本的認知原則」59。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故事往往更具有
這種逼真性寫作方法的特質。《三言》中的道教人物,往往會突然做夢,往往
會遁世,又往往會夢回、詐死還魂,最終會回到有時差的人間來得到一個果
報,或悲或喜,得道或失道,終究有一個說法。李道人、杜子春都是如此,
爲了滿足讀者對於超越性宗教充滿神秘意趣的想像。莊子以詐死懲妻燒屋識
破人間名教乃身外之物得道成仙。杜子春雖未通過考驗,但也暗示未來成仙
可能,只是未知幾時60。
從方法上來看,與《三言》中其它道教故事不同的是,〈莊子休鼓盆成大
道〉一篇,馮夢龍明顯受到《莊子》修辭手法的影響。莊子本人就是寓言專
家。《莊子》一書的寓言特質,不僅表現在敘事結構上,更表現在語言的反諷
譏誚上。且這兩種特質,往往是一同出現的。如《莊子‧外物》中,莊子向
監河侯求貸以維持生計被推脫受辱,他就假借魚之口說出,「曾不如早索我於
枯魚之肆。」這是他一貫言談、行文的風格,即所謂「寓言」──「藉外論
59 M.H.艾布拉姆斯,《文學術語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5。 60
康韻梅,〈試析〈杜子春〉和〈杜子春三入長安〉的敘述話語及意義建構〉,《台大中文學報》第 14 期(2001 年 5 月),頁 36-37。
-
《三言》小說中承衍敘事研究 ──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等為例
141
之61」。《逍遙遊》以鯤鵬始,《秋水》以河伯遇北海若始,都是以這樣的「寓
言」方式呈現。《莊子》中不乏生動的比喻來針砭世情,但這種比喻本身還不
是「寓言」,寓言背後一定站立著某種穩定的生命觀。這種生命觀,到了馮夢
龍這裡,就簡化為世情倫理、簡化為人的在世性情,他是要用這種敘事邏輯
去討讀者買帳的。因而,本文雖然不贊成用莊子學說來詮釋三言二拍中以「莊
子」為小說人物的虛構形象,但不可否認的是,馮夢龍在創作〈莊子休鼓盆
成大道〉時,有意承襲了《莊子》在敘事美學上意圖、技巧,他在學習《莊
子》的敘事方式、也在學習《莊子》對於語言的虛構,並加以世俗化的想像。
馮夢龍所能調動的資源,就是民間對於「世情」體悟的經驗檔案。這之中,
包含著創作者對於小說人物行動術的設計、小說人物對於命運轉折時的應變、
眾人的反應等等……包羅萬象的人情世故,都可以成為馮夢龍推斷人情脈絡的現實邏輯依據。更因為世情人倫本質上與《莊子》對現實持嚴厲態度的超越
性生命觀是矛盾的,這種天賦的格格不入感,反倒是為〈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建立了奇趣的敘事圈套。
馮夢龍一般不對《三言》中的故事做明確的價值判斷,也不對更深層次
的精神景觀做探討,但〈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作為文本範例,無論從選材、
改編、結構、修辭上,都不失為一個馮式敘事範例。
小說開篇馮夢龍說了一通勸世道理。
「富貴五更春夢,功名一片浮雲。眼前骨肉亦非真,恩愛翻成仇恨。莫
把金枷套頸,休將玉鎖纏身。清心寡欲脫凡塵,快樂風光本分。62」
這個勸世入話,在我們做完小說的文本分析以後來看,基本上是懸置的,
沒有太精確的針對性,僅僅是表明大致的意圖,放之四海皆准。畢竟這個故
事裡的莊子以那麼不堪的方式死了老婆、碎了瓦缶、燒了屋宇,雖然也轟轟
烈烈脫凡塵,但不知道有什麽快樂風光可言。《西江月》的入話,僅是要人在
宏觀意義上割斷迷情,參破凡塵,是為勸世。但是紅塵正因割不斷、理還亂
才能產生世情故事。
此外,馮夢龍將孝悌二字高於儒釋道,沒有解釋論證。但又說孝悌被世
人放在夫婦之情之後,同樣出於信口。在這裡小說敘述者與「世人」的有意
61 郭象注,《莊子》(臺北:藝文出版社,2007 年),頁 496。 62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頁 9。
-
靜宜中文學報 第五期
142
對立,似乎是要站在一個故事之外的立場之上。用李志宏對於中國白話小說
中「敘述者聲音」的反省思考來看,符合古典白話傳統小說的習慣63。總的
來說,出版者或者說創作者預設了讀者仰賴敘述者在講述故事時順便加以道
德詮釋與教誨的要求,且這種教誨也一定要基於「基本的認知原則」,是批量
生產、專供快速傳播使用的。尤其當小說的結局最終訴諸於因果報應循環和
大團圓結局的普遍文化心理時,《三言》裡「集體共用型」故事模範就應運而
生了。入話往往還會和正話的反響產生背離,顯示出揶揄的效果。
「若論到夫婦,雖說是紅線纏腰,赤繩系足,到底是剜肉粘膚,可離
可合。64」
「近世人情惡薄,父子兄弟倒也平常,兒孫雖是疼痛,總比不得夫婦
之情。他膩的是閨中之愛,聽的是枕上之言。65」
這兩段話其實是矛盾的。父母兄弟平常、兒孫自有福,但比不上夫婦之
情。然夫婦之情,也是一場虛幻。這裡有一個奇妙的遞進關係,卻與〈莊子
休鼓盆成大道〉沒什麼直接關係。在莊周與妻沒有第三者(無論是人是鬼)
破壞的前提下,與其說是田氏自取其辱,不如說是莊子自作自受,莊子三位
妻子沒一個有好下場,但怎麼能枉論這全是天下夫婦之大運命。總的說來,
作者不過是想說富貴、功名、骨肉、恩愛統統都靠不住;人世間,但凡著落
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是虛妄的。判語都下死,再來說故事,就令故事有
了一種自然的宿命感。這種宿命感不僅是小說結構造成的,也是入話時的教
誨造成的。它基於傳播學意義上的優勢恰恰會削弱故事的天然力量,用宇文
所安的話來說,「在真正的悲劇裡,這種先於劇情而有的過錯和因果報應的正
義,比起壓倒一切的、神秘莫測的必然性來,不值得一提;一出僅僅宣揚因
果報應、描寫罪與罰的戲劇,談不上是悲劇。66」田氏的遭遇哪怕能得到民
63 李志宏,〈《儒林外史》敘述者形象及其論述的可靠性問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
刊》第 20 期(2011 年 7 月),頁 128。文中提到的一段分析「中國傳統白話小說的敘述者大多置身於故事之外,以『異敘述的』(heterodiegetic)身分進行講述,扮演著技巧設計者兼展示者的角色。在小說創作過程中,真實作者透過敘述者敘述行為的操作和敘述職能的發揮,將小說世界中的紛紜萬象都歸入到敘述方式的整飭秩序中。在交流情境的創造中,敘述者利用各種具逼真性的敘述方式,提供讀者一套因果循環、善惡論證的道德體系和價值規範,從而建構出一個有序化的小說藝術世界。」
64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頁 9。
65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頁 9。
66 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社,2006年)頁 77。
-
《三言》小說中承衍敘事研究 ──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等為例
143
眾的同情,她的命運也因前置的「集體共用型」教誨,不能成為嚴格意義上
的悲劇。因為這種前意志,本身就是不可靠的,馮夢龍不負責建立起該意志
的合法性,僅僅嫁接人與人的倫理,無法構建意志與命運之間更神秘的運作
秩序。
而什麽是人與人的關係?這裡指的是倫理,倫理背後是「禮」,小說中也
假借田氏說過「自古道:『怨廢親,怒廢禮』67」。馮夢龍在《三言》序中說,
「借男女之真情,發明教之偽藥」。十六世紀是中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商品
生產的發展促進資本主義的萌芽,首先在思想領域,產生了由王學左派和李
贄為代表的反理學思潮。在文學創作中也得到生動的反映。馮夢龍是一位深
受李贄思想影響的人物68。馮夢龍越是把入話的教化做的有模有樣,越是讓
正話的解構顯得諷刺十足。我們暫且這樣粗糙的理解,無論馮氏真實的意圖
是否確鑿,有一點是可以得到確證的,在「莊子戲妻」這個故事模型裡,馮
夢龍試圖借用「莊子」所建設的「象」來傳達一個道德上的教化。他的方法
是先懸置道理,再用世情的現象加以還原事情的原貌,從而令這些道理顯得
不那麼合理,以此解構,且不做過分的渲染和強調。但這本身已經構成了對
於經典的懷疑。明中後期的哲學思潮表現為一種對傳統價值觀的質疑,馮夢
龍與明代心學的關係亦有學者考證研究。他用遊戲的筆觸重釋傳統經典的哲
學命題,或許受到了心學盛行的影響。
從表面上來看,〈莊子休鼓盆成大道〉所要表達的似乎只是婦人薄情、自
取其辱,婚姻不可靠、承諾不可信。但事實上,〈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基本實
現了對「鼓盆而歌」故事的一種顛覆。小說對於「莊周」的哲學家身份設計
是很模糊的,對丈夫身份威嚴冷漠的描述卻很具體。馮夢龍同樣不會拯救他
筆下的任何人物,也不對他們做任何啓蒙。他甚至沒有任何意圖引導讀者向
著超越性的方向行走。黎必信援引布斯《小說修辭學》的觀點加以揣測,「有
意造成讀者關於基本真理的混亂……對真理有意的改動,目的在於打破讀者關於真理的新年,以便在提供真理時他容易接受。69」這在馮夢龍於入話中改
編「夢蝶」的詮釋中反應更為明顯。他將物物、人人界限消解融合的生命觀
直接轉換為莊子「資質不凡」、具有仙緣的傳說,在簡化敘事負擔的同時,其
實質上還是在用戲言挑戰話語權威,他將「莊周夢蝶」的故事元本完成了從
67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頁 11。 68
盧興基,《市井悲喜劇──中國古代話本卷》(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年),頁 10。
69 布斯,《小說修辭學》(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282-412。
-
靜宜中文學報 第五期
144
道家主題到道德家主題的轉變,以至最終還趕上了女性婚戀問題的盛行,令
後世重讀不斷豐富著他的寫作意涵,真理的混亂也由此演變為一種真理圈套
的遞嬗。
《三言》所依據的敘事框架及其世情經脈,在不斷簡化禮教深淵層級的
同時,也在另一程度上張揚著人的兩難、人被困陷在自然的那種既定的機械
運轉中逃脫不了的盛衰榮枯,這個過程偏巧是普通讀者在回顧自己命運時見
得最多的東西,馮夢龍將它的樣式打造成哀歌。
一方面,馮夢龍擴充了莊周妻死鼓盆典故的意蘊,從生死觀,擴大到夫
妻相處、男女地位、富貴、情欲、奇幻之術等議題,顛覆了對於經典文本的
詮釋方式,拓寬了後代改寫典故的想像空間。另一方面,作為並不得志的士
人,通過商業介入文學寫作的方式徹底改造經典文本,也不失為馮夢龍個人
情志的補憾。
(二)出版傳播與小說療癒
許暉林在「白話小說、書籍史與閱讀史:明清文學研究的新視角」研討
會發言上,援引了討論小說讀法的集中面向。其中,Andrew Schonebaum的〈虛構的醫藥:中國小說的療效〉將晚明的小說閱讀放在流行出版品的脈絡
之下加以理解,他認為,晚明以後,小說成為雙重形態的虛構藥劑,一方面
能夠治療善讀的讀者,另一方面則製造出它本身所要治療的疾病,並且扮演
醫學書籍的角色,提供讀者關於疾病與治療的詳細描述70。「小說有毒」這個
說法,Andrew Schonebaum為我們理解新文本的創生帶來極好的認知面向。
首先是小說創造了它本身所需要的人的處境,其次是通過再度使用文本
加以療癒,這也是世俗世界觀逐步通過文學加以傳播的重要方式。前文提到,
大木康從出版文化的進路為明清小說研究提供了更為具體的面向。事實上,
經濟力量和技術力量的提升也的確對小說改編的敘事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馮夢龍改編〈莊子休鼓盆成大道〉故事時,已將話本小說置於精英文化與
大眾消費文化的平衡點之上。權威性的解構與沉淪,哪怕並非出於馮夢龍創
作《三言》的本意,卻畢竟造成了這樣的結果。「集體共用型」在不斷製造傳
播學意義上的文化風潮同時,也不斷對重讀「經典」施加著蠻力。王璦玲指
70 許暉林,〈「白話小說,書籍史與閱讀史:明清文學研究的新視角」研討會論文評述〉,《中
國文史研究通訊》第十八卷第三期,頁 18。
-
《三言》小說中承衍敘事研究 ──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等為例
145
出︰「權威性、中心性在此沉淪,遊戲心態、解構神聖,形成了一種敘述態
勢的核心……文學經典神聖性的消解與消費化趨勢,體現著現代性中的世俗化需求,而通過戲仿,改編後的文學經典,其實已不復原初意義上的文學經典,
充其量,原作與改作兩者間,也僅只是保持著可辨識的互文性關係而已。71」
莊子走下神壇,才能彌合高雅與通俗、經營與大眾之間的鴻溝。而在這種世
俗化的過程中,馮夢龍賦予在《莊子》中只出現過一次的妻子以很大虛構空
間。
馮夢龍將「善讀的讀者」瞄準了普通百姓,《三言》致力於市場面向的創
作方式,使得莊周從前文本的「妻死」者演變成一個「試妻」者。《莊子》中
鼓盆的意圖建立於超拔俗世的生命觀之上,而《三言》將之變質,甚至還低
於俗世對於死生的哀憫本能。但變質的效果很明顯,太多改編作品要為之平
反。如《川劇傳統劇本彙編》第十五集有高腔《南華堂》,就是《蝴蝶夢》的
改本,他的結局是:「玉帝知道莊周對待妻子的情況,大為不滿,責其無故戲
妻,由天仙貶為地仙。72」即為《三言》的改編「一方面能夠治療善讀的讀
者,另一方面則製造出它本身所要治療的疾病」的例子。
而那位搧墳寡婦,則像一個幽靈一樣害的莊周家破人亡,其實還原到事
情本身來看,似乎也還有空間值得推敲。寡婦要搧墳以減少待嫁的等待時間
──這是寡婦鑽了丈夫遺言的空子,然而她並沒有違背對丈夫的承諾。因為
她如果完全不顧丈夫的遺言的話,何不直接去改嫁,而要辛辛苦苦地搧墳呢?
莊周對她也無惡感,不然不會收下她送的紈扇。這個收紈扇的動作設計者馮
夢龍應該對寡婦應該也沒有太大的反感(不然就應當如莊子詐死後提到田氏
時改稱「婆娘」的睥睨語氣),世相如此,馮夢龍恐怕早就習以為常。他將自
己看待寡婦的立場,兩次植入莊子故事,所針對的,恐怕是理學家提出的「從
一而終」。守節是以犧牲女性一方的利益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倫理規範。它只
對女性一方提出單方面的約束,是封建社會男權中心的產物,明代商品經濟
的發展帶來的個性解放,首先在這一領域出現裂罅。《金瓶梅》裡眾多婦女的
改嫁,似乎在性放縱中,表現著商業社會務實的準則。但像孟玉樓的改嫁,
姑媽楊氏提出的「少女嫩婦的……不叫他嫁人,留著他做什麽。73」也表明了一種人性的原則。它呈現一種全新的道德規範,在道學家看來,簡直是不可
71 王璦玲,〈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導言一:重寫文學史──「經典性」重構與明清文
學之新詮釋〉,《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臺北市:聯經事業出版公司),頁 2。 72
錢南揚,《戲文概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 年),頁 159-160。 73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一)》(臺北:里仁出版社,2007 年),頁 96。
-
靜宜中文學報 第五期
146
思議的事74。但在民間,卻是老百姓熟視無睹的現象。人們最關心的,不是
寡婦能不能嫁人,而是寡婦多快就嫁人,嫁給誰,是否之前就有鋪墊……這種時間的焦慮本身就是倫理問題。這就是女性從性別意義角度上建立起的精英
與世俗文化之間的橋樑。因而〈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看似是在戲說莊子,其
本質上還是一個婚姻故事。
我們不妨可以假想,〈莊子休鼓盆成大道〉故事中的莊周若是試出了妻子
不更二夫、對楚王孫毫不動情,結局會如何。探討這一議題的價值在於,馮
夢龍在將「故」事「新」編時,其實還是帶著腳鐐起舞。他有一個預設的「意
志」在指引「命運」。在小說中,「命運」只是一個現象、一個最終結果的陳
述。而「意志」所要包含的,則是雜糅了社會秩序與世情倫理等綜合效應的
邏輯力量。
所以與其說這一則故事裡是莊周設局,不如說是作者佈套。小說人物(而
非哲學家)莊週一步步跳進自己挖好的陷阱,最後將瓦盆打碎、取火從草堂
放起、屋宇俱焚、連棺木化為灰燼。四處遊蕩,終身不娶。看似全然出於一
種沒事找事的意圖,但莊周卻設計得很用心。他用心的去毀滅婚姻、毀滅家
庭,帶有強烈的象徵意味,最終毀滅自己,也像是字面上呼應了「喪我」的
逐求。《莊子》典故為馮夢龍的改編建立了基本框架,也寫好了結局,馮夢龍
卻為莊子故事注入了大量的民間世相、困惑及其解決方式。
「莊周試妻」的故事情節由馮夢龍所造,在現代日常生活中極為罕見。
更因其夫婦相處細節所呈現的冷漠、怪異並不符合常情,也為讀者創生了懸
疑、獵奇的審美方向。到了後世,這一段增補橋段居然成為大量戲曲改編的
基礎,甚至 1949 年以後一度在大陸禁演75,「小說有毒」的力量可見一斑。
「大塊無心兮,生我與伊。我非伊夫兮,伊非我妻。偶然邂逅兮,一
室同居。大限既終兮,有合有離。人之無良兮,生死情移。真情既見
兮,不死何為!伊生兮揀擇去取,伊死兮還返空虛。伊吊我兮,贈我
以巨斧;我吊伊兮,慰伊以歌詞。斧聲起兮我復活,歌聲發兮伊可知!
噫嘻,敲碎瓦盆不再鼓,伊是何人我是誰!76」
74 盧興基,《市井悲喜劇──中國古代話本卷》,頁 15。 75
雷競璿,《崑劇蝴蝶夢──部傳統戲的再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 年)。 76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頁 9。
-
《三言》小說中承衍敘事研究 ──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等為例
147
篇末這段話,述盡了莊子一生與妻子的情感糾葛。他似乎帶著某種怨念
選擇了逍遙,就像民眾常以為感情不順的人才出家是同樣道理,這種解讀其
實是很荒唐的。但這樣的荒唐又承接上了莊子在歷史與哲學意義上的最終歸
宿──逍遙。只能說是歪打正著。
《逍遙遊》稱「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易經》的關鍵是天
地人,《莊子》化成神明、聖王、天地、萬物和人。在天地的層面化出來,向
上是神明,向下是萬物。天地為體,神明為用。天地是萬物的合,萬物是天
地的散。而聖王關涉的是有生死的人。天人、神人、至人三種人,在天地中
居於神明層面,在人中自居為民。莊子「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
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77」,直接修的是神明的層面。而在人間世,把自
己化到民裡邊去,在七種人處於最低一等,也是七種人的基礎。但無論怎麼
親民、如何隱居,莊子會出現在三任妻子和一個路遇寡婦周圍演繹這番前世
今生的糾葛,才是馮夢龍所造的小說之毒。
三、餘論
與神話改寫、史乘重寫不同的是,立足於世情秩序的經典重構,處處滲
透著世俗價值的植入。《三言》中〈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一篇在傳播意義上的
成功,有馮夢龍有意迎合的意圖,也有因其改編後的故事無意間符合世界民
間傳統的審美意趣,從而得以廣泛流傳的偶然。白話小說的本質不是隸屬廟
堂的,而是立足生活的,寫實性極強,多為「現實世界中人性的欲望78」的
展現,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現實世界中人性的欲望,在《三言》誕生的時代,
已然包括了「讀者」與「編者」的考察面向。「重寫」問題,也因此而日漸複
雜起來。我們更應該重視「前文本」的流變,在經濟、政治變動之下所可能
受到的影響。改編行為在療癒當下讀者心理的同時,也正在不斷創生著改編
本身所製造的新問題。文學經典神聖性的消解與消費化趨勢,體現著現代性
中的世俗化需求成為了「重寫」議題的重要動能。我們在試圖理解這種動能
的同時,更應該去釐清「重寫」中變異問題所輻射的社會世相。無論是哪個
時代的老百姓,人們歸根結底關注著的,還是和自身處境最相關的議題,喜
歡看的也是自己能夠治療的他人之疾。
77 郭象注,《莊子》,頁 581。 78
樂蘅軍,《古典小說散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 年),頁 225。
-
靜宜中文學報 第五期
148
引用文獻
一、古籍文獻
郭 象注,《莊子》臺北:藝文出版社,2007 年。 馮夢龍編撰,《喻世明言》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馮夢龍編撰,《警世通言》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一)》臺北:里仁出版社,2007 年。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M.H.艾布拉姆斯,《文學術語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 年。 王璦玲,〈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導言一︰重寫文學史──「經典性」重
構與明清文學之新詮釋〉,《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臺北市:聯經事
業出版公司。 布 斯,《小說修辭學》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
版社,2006 年。 季羨林等整理,《韓國藏中國稀見珍本小說-啖蔗》第 1 輯,北京:中國大
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 年。 祝宇紅,《「故」事如何「新」編──論中國現代「重寫型」小說》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陳引馳,《莊子精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年。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 陳翠英,《世情小說之價值觀探論──以婚姻為定位的考察》臺北︰國立台灣
大學出版社,1996 年。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 劉祥光,〈婢妾、女鬼和宋代士人的焦慮〉,《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
臺北:東華書局,2005 年。 樂蘅軍,《古典小說散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 年。
-
《三言》小說中承衍敘事研究 ──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等為例
149
樂蘅軍,《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臺北:大安出版社,
2003 年。 盧興基,《市井悲喜劇──中國古代話本卷》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錢南揚,《戲文概論》臺北:本鐸出版社,1982 年。 錢南揚,《戲文概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 年。
(二)論文
1.期刊論文
大木康,〈從出版文化的進路談明清敘事文學〉,《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七
卷第三期(2007 年 9 月)。 宋麗娟 孫遜,〈「中學西傳」與中國古典小說的早期翻譯(1735-1911)──
以英語世界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2009 年第 6 期。 李志宏,〈《儒林外史》敘述者形象及其論述的可靠性問題〉,《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語文集刊》第 20 期(2011 年 7 月)。 李良子,〈舊瓶新酒:淺談「三言」與戲曲之敘事關係──以〈莊子休鼓盆成
大道〉故事流變為例〉,《渭南師範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3 期(2010 年5 月)。
杜威‧佛克馬,〈中國與歐洲傳統中的重寫方法〉,范智紅譯,《文學評論》
1999 年第 6 期。 金榮華,〈馮夢龍《莊子休鼓盆成大道》故事新探〉,《黃淮學刊》第 12 卷第
2 期。 康韻梅,〈試析〈杜子春〉和〈杜子春三入長安〉的敘述話語及意義建構〉,《台
大中文學報》第 14 期(2001 年 5 月)。 許暉林,〈「白話小說,書籍史與閱讀史:明清文學研究的新視角」研討會論
文評述〉,《中國文史研究通訊》第十八卷第三期。 蔣向豔,〈從《查第格》看伏爾泰與道家思想之關聯〉,《中文自學指導》,2006
年第 6 期。 黎必信,〈對應敘述與經典重釋──論〈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的主題建構〉,《中
國古代文學研究》2009 年第 4 期。 謝易真,〈試探莊周喪妻鼓盆寓言故事的變異與發展──由「妻死」到「試妻」
展開〉,《慈濟技術學院學報》第十八期(2012 年)。
-
靜宜中文學報 第五期
150
2.學位論文
許懿豐,〈譎詭幻怪—《三言》幻異故事研究〉,臺北: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館藏碩士論文,200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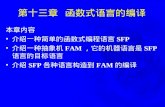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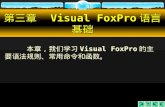

![令和2年12月6日【日] › ~soukyoku › img › img001.pdf2020InternationalKeI甘unKotoCompetition 喜嚢 義幸、言≡三三三ユニ ・-.三や止む・.丁三 二・二三](https://static.fdocument.pub/doc/165x107/5f0e91707e708231d43fde49/oe212oe6-a-soukyoku-a-img-a-2020internationalkeicunkotocompetition.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