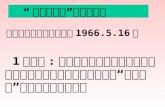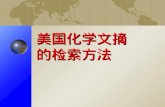文化工業 —— 因繁榮而即將作廢的類概念 Industry.pdf ·...
Transcript of 文化工業 —— 因繁榮而即將作廢的類概念 Industry.pdf ·...
-
台灣產業研究 MOOK 3,張苙雲主編,《文化產業:文化生產的結構分析 》
台北:遠流,2000 年 12 月,頁 11-45。
文化工業 —— 因繁榮而即將作廢的類概念
摘要
本文回溯「文化工業」概念出現於四0年代的思想史背景及其在批判理論中的脈
絡。就社會史背景討論「文化工業」與現代性的關連,特別以國族國家與消費社
會為軸線。進而分別就地方、國族、全球與次文化等不同層面討論「文化工業」
的政治模稜。最後本文探索「網際」文化工業崛起的新視域,及其文化政治的新
挑戰。
Culture Industry——A Genus That Will Soon Be Obsolete By Its Prosperity
Abstract
"Culture Industry," an ironical term coined by Horkheimer and Adorno,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words in critical studies of culture since its debut in the 1940s. This article traces its origin in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s of Critical Theory. Researches in social history are used to illustrate the intrinsic relations between culture industry and modernity, specificall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states and consumer societies. The article further discusses the political ambivalence of culture industry at various levels: the global, the national, the local and subcultures. At the end it suggests to perceive the new challenges emerged with the horizon of the Internet Culture Industry.
1
-
文化工業 —— 因繁榮而即將作廢的類概念
Culture Industry—— A Genus That Will Soon Be Obsolete By Its Prosperity
1947:概念的緣起
「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1 這個概念,首度出現於霍克海莫與阿多諾1947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啟蒙的辯證》。將「文化」與「工業」並置,顯然表現反諷的意涵。據阿多諾的回顧(Adorno 1991[1975]),他們用這個概念取代原來初稿中的「大眾文化」(mass culture),有極為嚴肅的用心。他們要徹底避免一種詮釋:好像所指涉的這些事物是從大眾之中自然產生的通俗形式。不!文化工
業是與此極端對立的概念。文化工業的每一支產業、每一種產品,都是為了大眾
消費而設計剪裁,都或多或少依據計畫而製作生產,而且也都相當程度地決定了
消費的性質。每一支個別產業之間,或則具有類似的結構,或則互補交織而為一
個體系。當代技術能力,以及經濟與管理上的集中,使得這樣的體系得以交織得
毫無間隙,自上而下整合它們的消費者。誠然,文化工業必須計算推測千百萬人
的意識與無意識,若不順應大眾則無以自存,然而,「消費者是頭家」只不過是
文化工業的意識形態,消費者不是主體,只是被計算的客體、推測漲跌買賣的對
象,只是市場調查報表裡依屬性分類而以紅藍或綠色標示的區域,是產業機制的
附屬。
以思想史而言,「文化工業」概念所源出的脈絡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
論」。這批異質但頗具才華的德國猶裔知識分子,在流亡的不同階段裡,開啟了
一系列原創而影響深遠的批判議題,或許是從卅年代到八0年代大約六十年之間
最為活躍的思潮之一。文化工業的批判並非孤立的議題,而與國家資本主義政治
經濟體系的批判、威權國家與威權人格的批判、自由主義抽象個體性的批判、工
具理性的批判、現代性神話的批判、與新興大眾傳播媒介的批判等形成互為脈絡
的系列議題。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的批判,猶如葛蘭姆奇(Antonio Gramsci)對文化霸權的解析,取代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將焦點移至文化
工業如何藉著「製造」大眾對既存社會的「認可」而複製資本主義霸權並確立社
會整合的社會心理基礎。 阿多諾與霍克海莫採用「文化工業」一詞,強調大眾文化的產品乃自上而下
作為社會控制與規訓工具的支配/管理/施給的文化(administered culture)。例如「娛樂事業」(Entertainment),藉著不斷重複而複製了將既給生活方式當作「世界本
1 “Industry” 可中譯為「產業、企業、工業」。就本文的脈絡而言,這些譯名的替換並無妨
礙,本文沿用批判理論中譯習見的「文化工業」,與本書所謂的「文化產業」,或有觀
點的強調但指涉卻無差異。
2
-
如此」的圖像,使得受眾接受既存社會就如天經地義那般自然。而「廣告業」
(Advertising)則逐步將風尚樣式與技術鎔接於文化工業的娛樂,也因而成為對既存社會與既給生活方式的廣告。有聲電影的結構消泯了劇場觀眾想像反省與回應
的空間,音樂的商業化使得即如爵士與古典樂都不免於暢銷排行的拜物性格,「民
意」(public opinion)成為商品,而運動(sports)則成為從眾者慶賀其從眾行為的儀式(Horkheimer and Adorno 1969:120-167)。
「文化工業」概念出現的時刻,正是當報紙、廣播與電影興盛而成為支配文
化形式的時刻,也是當電視被初步引介的時刻。阿多諾與霍克海莫早在四0年代
即預見了電視將綜合廣播與電影,在商業化之下將成為文化工業最具勢力的一
環。2 法蘭克福學派的作者們曾經目睹希特勒如何超絕地運用大眾傳播媒介創造法西斯景觀,而在流亡美國的時候,又目睹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如何精彩地
運用大眾媒介作為宣傳的工具。因此國家對於媒介的控制與政治運用,以及資本
家對於娛樂事業的控制,就為批判理論解析「文化工業」作為社會控制工具的模
式提供了歷史的根源。 無論在法西斯社會、自由民主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即如二次大戰之後冷戰
時期的支配局勢,都不脫批判理論對於文化工業造就單向度社會的精確描述。社
會學家 C. Wright Mills 在五0年代即充分運用這些洞見,強調媒介作為社會控制與操控公眾的工具,捏塑個人夢想與行為,特別是藉著促銷「個人成功」的夢想
而誘導順從於中產階級價值。Mills (1951:333-336)認為娛樂性媒介是社會控制的強勢工具,人們在心智鬆弛而身體疲憊的勞動之餘暴露於娛樂媒介之下,媒介中
的角色輕易地成為認同的對象,為個人問題提供了輕易的刻板化解答。Mills(1956)也指出大眾媒介促銷支配的政治象徵與政治人物,造成政治商品化的趨勢,使政
客的廣告類同商品行銷,而媒介捏塑民意的操控角色強化了支配菁英的權力。
Mills 預見了哈伯瑪斯稍後在《公共領域之結構變遷》的理論:由個人參與公共社群的政治性/社會性論辯與行動的公眾(publics),轉型而為遍受大眾媒介操控的大眾(mass)。大眾媒介由一小群菁英控制,而不容許回饋參與的單向傳播,抹除了公共領域的民主條件,助長了社會消極性並將公共領域分裂支解為私有的消費
領域。 其他的批判理論家如佛洛姆,馬庫色與哈伯瑪斯也為社會理論提供了認知文
化工業的重要觀點。佛洛姆的《逃避自由》(Fromm 1941:128ff)提醒大眾傳播如何鈍化個體的批判思考能力、新聞媒介如何捏塑公眾意見。馬庫色的《愛慾與文
明》(Marcuse 1955:104)指出大眾媒介操控人們的心智與本能,結果是個體自主性的消蝕:「隨著意識的消逝、隨著資訊的控制、隨著個體熔毀於大眾傳播,知
2 Horkheimer and Adorno (1969:124)。阿多諾並於 1954 發表了一篇經典論文 “How to Look
at Television”(Adorno 1991:136-153),分析電視作為文化形式及其影響的重要性。
3
-
識也成為支配/管理/施給的、禁閉的。個體並不真的瞭解發生了什麼,娛樂與教育機器將人們籠罩在麻痺的狀態下,任何不受歡迎的思想都遭排除」。這種「媒
介操控理論」對六0年代的新左(the New Left)有廣泛影響。馬庫色在《單向度的人》(Marcuse 1964)以商業廣播與電視的空虛無聊來說明媒介已成為社會控制的新形式,泯除個性與思想,孳生「假性需求」(false need)以及順利複製先進資本主義所必須的單向度行為。哈伯瑪斯的早期著作《公共領域之結構變遷》
(Habermas 1989 [1962])則為文化工業的興起與自由民主公共領域的沒落提出了歷史的分析:早期的自由資本主義形式具有一個民主的公共領域,由開明的公眾
批判地討論政治與社會議題並在辯論與共識中形成「輿論」,逐漸轉變到壟斷資
本主義的形式,由大眾媒介形塑「民意」,由消費者被動接受文化工業的產品。3
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最早注視文化工業與大眾傳播的社會功能及其後
果,並且深刻地影響了諸如 C. Wright Mills、David Riesman、Alvin Gouldner、 Stanley Aronowitz 以及新左的稍後世代。也影響了傳播研究的批判傳統以及論辯「通俗文化」的理論。當然,對於文化工業危險性的關注不限於法蘭克福學派。
阿圖塞在其重要論文「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Althusser 1970)指出媒介的支配力量來自於反映資產階級位置的優勢意識形態:「藉著新聞報紙、廣播與
電視,傳播機器每日餵食每位公民一定劑量的國族主義、沙文主義、自由主義、
道德主義等等」。即便是波迪厄晚近兩篇論「電視」的演講(Bourdieu 1998)也持續類似的批判:目前電視的形式「對民主與政治生活是一種危害」,電視提供自
由的幻覺,幾乎所有進入螢幕的圖像都徹底受到企業與政治興趣的媒介,追求收
視率的結果是迎合短淺的注意,新聞流為預先包裝的音切與煽情的鏡頭,重要論
辯永遠由熟悉的講頭(talking head)發表即便是彼此「差異」都已定型的意見,無能引介主流之外的觀點…。
然而對於文化工業的政治效應,「危害自由民主」、「取消個體性」、「麻痺蠢
化」等負面批判,已被認為是法蘭克福學派理論的模式。批判理論的觀點卻也因
此被批評為文化菁英主義(cultural elitism):知識菁英對俗眾的文化經驗欠缺感受。更令部份左派學者(例如 Enzensberger 1982, Fiske 1987, Kellner 1989)感到失望的理由是:阿多諾等人對於文化工業的悲觀描繪,看不到解放的可能,也提不
出策略。對於文化工業所指涉的,特別是新興傳播媒介所創生的文化形式,他們
覺得有必要尋求積極肯定的觀點。而這個政略光譜的對立觀點,卻也早與文化工
業理論同時出現。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對於新興傳播媒介與文化之間關係的見解可以說是
法蘭克福學派的異數。他並不蔑視藉新媒介形式而傳播的文化產品,敏銳地體察
3 也有評論如Mark Poster (1995:12)指出,哈伯瑪斯不過是重複了阿多諾與霍克海莫的結
論。
4
-
到人民抗拒霸權結構的能力,並且在新媒介形式裡看到平等主義的誘因。例如電
影,將原來低階層無法接觸到的藝術作品普及到人民的日常生活。原來高高在上
具有神聖光環(aura)的藝術作品,原本就是階層與地位的權威政略。但是當機械時代的技術能夠大量複製藝術作品的影像與音樂,將其輕易流通到社會各個角
落——包括工人階層——的時候,藝術也就喪失了它的光環。此外,新媒介的技術結構也可能增進批判思考的習慣:例如電影不斷流動的影像未必遏阻思考,也
可能造成激盪而提高心智活動;觀眾得以佔有鏡頭的位置而不再認同於演員,帶
入了批判的距離;集體觀賞的經驗,未必全然被動接收,也可能鼓勵批判的態度;
技術上容許分解重複作品的片段,也有助於養成分析性解讀的習慣;比起昔日藝
術作者與觀眾的遙遠距離,新的媒介原則上使作者與觀眾之間更易於相互轉換。4
班雅明察覺到了其它批判理論家不曾考慮的可能性:新傳播媒介的解放作
用,以及基進媒介政略的潛力。這個觀點雖截然不同於批判理論的主流基調,但
並非完全孤立。與班雅明同時的Siegfried Kracauer5 也體察到電影這樣的新大眾媒介具有威脅傳統文化美學階序的顛覆潛力。當電影首度於一八九五年以大眾娛
樂的方式出現於德國的時候,德國政府深恐電影可能煽動低階層誘發騷亂而急於
規範檢禁。而德國文化(Bildung)的衛道之士也焦慮地攻擊電影對以劇院為典型的高雅文化帶來危害。這些徵候卻是Kracauer以Peter Bürger所謂「前衛」(Avant-Garde)觀點所敏銳洞察的新大眾媒介的挑戰。當然,沒多久,德國官方卻發現了電影的另一種潛力——操控大眾意識的功能——而且終於受到納粹的完美運用。Kracauer (1947)同樣洞察了這種惡性的趨勢,他在流亡美國期間完成了1910-1940 德國電影的著名研究,指出納粹政權的所有構造,在威瑪時期的德國電影都可找到軌跡。班雅明與Kracauer對於新媒介形式的態度是模稜複雜的,他們覺察到媒介科技的進步具有民主化的潛力,但不同的實現方式卻可能將其完全
逆轉。科技決定論是沒有根據的,傳播科技的發展並不會自動保證任何特定的政
治方向。 卅年後 Enzensberger (1982:47-52)呼應班雅明的見解,描繪出與阿多諾等批
判理論基調截然對反的圖像:新媒介帶來了構作平等、自由主體的進步政治力
量,「電子媒介的公開秘密…在其動員力量…媒介使得大眾參與社會過程成為可能…媒介具有可觀的威脅力量…首度帶來了對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挑戰」。然而
4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Benjamin (1969)。雖然班雅明
主要論及電影與攝影等影像藝術,但其邏輯可及於其它如音樂等亦可受機械複製的藝
術作品。 5 Kracauer為二0年代法蘭克福匯報副刊編輯,與Adorno, Horkheimer, Benjamin為同一世代
的法蘭克福知識分子,但不屬於法蘭克福學派,且與Adorno尤其是Horkheimer觀點相左私誼不睦,其淵緣細節見Martin Jay (1993:363-9).
5
-
這種對「可能性」的過度樂觀,或許又淺薄化了班雅明與 Kracauer 所警覺的模稜與複雜情境:傳播媒介本身受到國家與資本主義各種重要社會機制的媒介。
文化工業與國族國家
「文化工業」作為理論概念的思想史源起雖是廿世紀四0年代,但「文化工
業」的社會史脈絡卻深遠的貫越了現代性(modernity)的幾乎所有面向。我們僅從兩個面向——國族國家(nation-states)與消費社會(consumer societies)——略作社會史的回顧。
從早期現代歐洲(early modern Europe)的文化史研究,我們注意到自十六世紀
資本主義萌芽期,印刷出版業就已是個結合技術、商業與文化影響力的關鍵產
業。華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是個偏重物質經濟的研究,卻沒有忽略十七世紀
荷蘭在歐洲不僅享有先進技術與商業優勢,更享有支配性的文化影響力
(Wallerstein 1980:44, 66)。當時英格蘭與蘇格蘭青年留學荷蘭受大學教育,迪卡兒、史賓諾沙、洛克及許多歐洲知識分子所樂居的「哲學家天堂」,也就是當時
印刷出版業最為蓬勃繁榮的阿姆斯特丹、安特衛普與鹿特丹。無論是在荷蘭這些
國際商業城市還是在里昂、鄱堤耶(Poitiers)這些法國地方城市,印製或出版些什麼,都是由業主依據獲利的考量而決定。這是個道地的早期資本主義文化工業,
卻對社會結構造成深遠的衝擊。 麥克魯漢(M. McLuhan 1964)曾極具洞見的指出活字印刷技術的發展造成國
族主義、工業主義、大眾市場、普及教育;他認為活字印刷牽涉了大量生產的同
質化擴張原理,是瞭解西方力量的要訣,印刷書籍容許教育過程無止境的擴張,
精確複製的意象足以釋放巨大的社會能量,使個體脫離傳統社群的藩籬,提供個
體之間相互結合的新形式。在麥克魯漢式的表述之下,這項洞見經常受批評為技
術決定論。我們卻不難以社會史研究來還原印刷出版業作為早期資本主義文化工
業的社會脈絡。E. L. Eisenstein (1968, 1969) 指出早期現代歐洲的識字菁英與城市人口深受印刷出版業的影響。N. Z. Davis (1975)則指出早期現代法國,無論城鄉與階層,印刷出版的商品讀物以各種方式成為凝聚社群、構造「人民」與「公
眾」的影響力。R. Darnton (1982)則以法國革命前印刷流通的地下讀物重新詮釋啟蒙運動。在這樣的脈絡之下,我們不難理解 B. Anderson (1983:41-49)的強調:現代國族意識的發展,無論是十八世紀末法國革命的經驗或是十九世紀蔓延歐洲
以及其後成為世界風潮的國族主義,關鍵的條件即在於印刷出版物成為商品
(print-as-commodity),或所謂印刷出版的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 中國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的國族主義發展與國家建構過程,也不例外。對晚清
以來報刊雜誌與小說的研究(Lee and Nathan 1985),表述了類似的觀察。讓我們
6
-
想像,在沒有現代報業的狀況下,例如 1840-1842 年的鴉片戰爭,戰敗、簽訂南京條約、割地、賠款,卻沒有媒介足以對「人民」造成任何激動。然而當 1890年代,當上海、廣州、天津等通商城市出現十幾份中文報紙,包括每日銷售萬份
以上的滬報與申報,並且與外國的戰事由戰地特派員每日拍發電報報導戰情(首
次應用於 1884 年中法寧波海戰),國族的想像才隨著共同的閱讀經驗而出現。儘管這些報刊是道地的商業經營、其技術引進與新聞報導皆出於銷售考量,其政治
與社會衝擊卻極為深遠。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之役的每日戰況,以及戰敗後馬關
條約的協商過程、賠款、開放口岸、割台灣與讓遼東半島,使得閱報的人民有「國」
之將亡的迫切感。我們已熟知這是「國民革命」的發端,但社會史而言更具意義
的是此後數年間報紙種類、銷售以及政論雜誌的急速成長。梁啟超於 1901 年計算了八十種報紙與一百廿二種雜誌。同時,識字人口所廣泛閱讀的文類,小說,
例如《官場現形記》、《廿年目睹之怪現象》、《老殘遊記》、《孽海花》等通俗出版
品,也攜帶了社會批判與政治意識(阿英 1973)。我們可以說,廿世紀初,以上海租借區與日本東京為兩大中心的中文印刷出版業,以及隨著鐵路、郵務、內河
航運而快速擴展的書報銷售網絡,成了現代中國初期國族意識的下層結構,也是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的前提條件。
國族國家的一個核心任務就是文化整合。現代國家的建構過程必須創造一個
統一而整合的國族文化,將一組共同的象徵、神話、記憶、民族英雄、事件、地
景與傳統交織於人民意識,將地方性差異同質化,將國界之內的異質社群予以同
化。這種由國家領導的文化運動、或是國族主義的同化事業,被認為是現代性的
核心徵候(Bauman 1990)。繼印刷出版業之後,廿世紀的電影、無線廣播與電視等文化工業,由於語音、影像不受限於識字階層而經由全國性網絡播送,成為塑
造國族文化的重要機制。特別對於廣大農村人口的低度開發國家,這些文化工業
的傳播影響力往往比民生物質的變遷更為廣遠與快速。 然而一九四九年之前,處於戰爭與流徙的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家建構過程是
個失敗的例子,未曾掌握關鍵文化工業的領導地位。一九三七年抗戰前夕,約有
九十三家廣播電台粗估約十萬收音機用戶,三百家電影院,卻大多集中於上海與
少數大城市(Chu 1937:192-194; Löwenthal 1938:47-48)。而依據中國電影史學者程季華(1963:112)的說法,早自 1931 年起,共產黨就透過左翼劇協等周邊組織,實際「領導」了現代中國的電影運動。對於出版業與報業,國民政府不幸地承繼了
軍閥時期的兩手策略:賄賂收買與查禁迫害。特別是抗戰之後,國民政府投入巨
資,藉買斷或收購股權而控制了國內許多大型報社與出版社,建立了一個官僚新
聞體系,受其控制的所有報紙必須複製中央新聞社發佈的內容,不容有獨立的編
輯立場,更別提不利於政府的報導。新聞專業的判準——責任、真實性與新聞價值——都屈從於政府的宣傳任務。結果這些報刊越大,名聲越差。對於異議作家與出版業主,則運用懲罰性檢禁,包括吊銷執照與各種報復措施。隨著查禁書單
7
-
越來越長,各城市的警察忙著檢查沒收顛覆性出版品。內戰情勢升高之後,查禁
與封館的密令經常以大規模警察搜捕來執行,便衣人員也開始騷擾書局與書報
攤。異議出版品的作家、報人與出版業主經常收到匿名電話與恐嚇信函,隨之而
來的是暴力突檢,逮捕、綁架與「失蹤」(Ting 1974,張靜盧 1957)。收買與壓制不足以擊敗政治鬥爭的對手,卻撕碎了公眾言論,摧毀了國民政府代表人民發
言的合法性。民眾無法接收可信的資訊,對國家政治事件的輿論民意也就無法形
成,於是國民政府與共黨鬥爭所迫切需要的公眾士氣加速潰散,徒然為自己留下
無數敵意的謠言。D. Barnett (1963:97) 在 1948 年見證了淪陷前夕城市居民不再相信政府任何訊息的普遍犬儒態度:「當中央新聞社宣稱某個城市解圍,我們猜
想那個城市已經淪陷或即將失守。」6
一九四九年之後,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與大陸的中共政權各自進行建構國家的文化整合過程,傳播媒介與文化事業都以服務國家為優先任務,而且都受當權政
黨的控制或領導。不同的是,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並未剷除民營文化產業的商業化
性格,而是在不同時期發展出不同的合作關係與共生結構(見本書林麗雲、鄭陸
霖)。然而大陸的中共政權從五0年直到七0年代末的三十年間,倒是剷除了「文
化工業」的資本主義商業性格。出版、廣播、電視、電影製片、演藝團隊全部由
中央委員會宣傳部透過各種管道而控制,地方組織與單位各由省市與各單位黨委
書記管轄領導。報紙的主要新聞,無論國內或國際,皆仰賴新華社提供,地方報
紙則複製出現於人民日報的重要理論與政策文字。不僅新聞媒體如此,學術研
究、文學、藝術、教育、體育,所有泛屬「文化」的事業組織也都遵循同樣模式
(Nathan 1985: 152-154)。七0年代,中共政府致力普及收音機,不僅推展到組織與工作單位,而且鼓勵家戶擁有,八0年代則體認電視的巨大傳播潛力而積極普
及7, 其作用一如五0年代發動大量人力將擴音機連線至偏遠村落以及將電影放映設備普及到工廠與公社。媒介的快速擴展,創造了中國歷史前所未有的廣大「受
眾」。中國逐步造就了梁啟超與孫文長久以來所夢想的:教育人民、建構國族國
家的政治宣傳機器。
6 國共內戰後期的幾場大型戰役,被視為中國命運的決定性轉折,例如遼東戰役與淮海戰
役,被軍事史家當作現代史傳統戰爭的最後經典,有許多專書討論。然而我認為爭奪人民
意識的文化戰場可能更具決定性,卻不見社會學者的深入研究。例如Theda Skocpol(1979)《國家與社會革命》,宣稱以結構觀點,對法國、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歷史比較研究,對於
爭奪人民意識的文化場域卻是一片空白,對此問題較深入的批評與對話,見Chu (1990)。 7. 評審認為「中國電視之普及,實乃因經改之後,必然有以廣告流通商品的需要所致」。我認
為兩者並不排斥。但時間上而言,中共文宣部高級官員於 1981 年,經改方才開始的時候,已在人民日報上表示:「電視是最為大眾導向的宣傳工具,千百萬人民可以同時收聽收看…目前,沒有其他宣傳媒介足以勝過電視」(見A.Nathan 1985:164-165)。相對之下,廣告流通商品,倒是後來衍生的「市場」需要。中共「政府」積極普及電視的著眼,首重宣傳控
制。
8
-
這套體制很不同於阿多諾等人以美國大眾文化為模型的描繪。批判理論顯得
有深度是因為它洞察「文化工業」如何藉著商品化的娛樂與廣告而提供幻覺、欺
瞞、麻痺、製造假需求與偽意識。然而共產體制之下,這種「批判」的深度取消
了,文化事業與傳播媒介的作用不再是藉著商品化的娛樂與廣告而提供幻覺、欺
瞞與麻痺,卻是直接的政治宣傳工具,赤裸坦白地展示批判理論所謂「文化工業」
的真實功能:自上而下作為社會控制與規訓工具的支配/管理/施給的文化(administered culture)。揭穿欺幻假偽的批判修辭,喪失了理論的魅力。指控文化工業具有「危害自由民主」、「取消個體性」、「麻痺蠢化」等負面政治效應,對資
本主義西方社會而言具有內在批判的銳利。然而對邏輯全然不同的共產體制,特
別是懷抱建構國族國家使命的政權,這樣的批評卻只不過是冷戰對立意識形態的
外部攻訐,西方本位的價值偏見。 一黨專政的國家,在其國境之內無遠弗界、水銀瀉地的媒介壟斷,當然能夠有效的傳達社會控制與規訓的政治訊息,自上而下遞送支配/管理/施給的文化。然而人民對於媒介宣傳的訊息如何接收與反應,卻是另個複雜的問題。這個體制
下的中共在八0年代之後,至少面臨兩個極不確定的前景。第一個是內部衍生的
弔詭:黨國壟斷的媒介宣傳造成類似四九年之前國民黨所遭遇到普遍不信任的犬
儒態度,人民轉向各種另類的小道消息以及接收國外廣播(Lee and Nathan 1985:378)。第二個是外來的挑戰:隨國際市場的擴張而快速流動的資本與資訊,對現代性定義之下的任何國族國家都是一種挑戰,國族認同與國家主權都因此而
必須持續重新協商,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消費社會來臨的中國大陸也不可能例
外。
文化工業與消費社會
由國家領導的文化整合運動或國族主義的同化事業,轉變為包容異質社群、
容許國族認同與文化界域的跨越與重劃,被認為是從現代性過渡到後現代性的核
心徵候之一(Bauman 1993:135-141)。而消費社會的文化被認為是晚期資本主義的後現代文化(Jameson 1984: 87)。我們不必執著於「後現代」這個過度流通的稱謂,然而國族國家與消費社會究竟有何消長關係,而「文化工業」又如何置於消費社
會的脈絡之中理解? 早年經歷東歐共產社會,近年研究消費社會與後現代文化的社會學家
Bauman 曾對九0年蘇聯東歐共產體制的瓦解提出評論:
事實上,鼓動反抗共產體制經濟而終於擊垮共產主義的,並非資本主義鄰邦令人
嫉羨的先進生產力,而是資本主義社會所享有的誘惑而迷人的豐裕消費。是這種
自我增進、享樂、立即滿足,自我陶醉的、後現代的文化,以及由消費樣式所界
9
-
定的生活,徹底暴露了共產主義宣傳教條的陳腐廢話。是這樣的文化徹底擊潰了
共產主義企圖與資本主義對手競爭的希望。人們不想重履十九世紀那種現代化與
工業化的磨難,而要分享後現代世界的歡愉,是這種擋不住的欲望,激起了對共
產主義壓制與無能的廣大抗爭(1992:171)。
這段評論指出消費社會的文化具有解放的作用,對於將近半個世紀之前以資本主義大眾消費社會為模型的「文化工業」批判理論,似乎是個未曾預見的反諷。
當然這並非宣告文化工業理論對於「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批判無效。每個人都
能自由選擇、自由逛街購物,並不因而就平等幸福。自由不能完全化約為消費自
由,否則人們就只能藉著購物來自我肯定。然而對於消費社會常見的描繪:享樂
主義、物欲貪婪、自私自利、精神貧困、追求即時快樂、助長表現式的生活風格、
養成自戀或自我中心的人格…同樣不足以理解消費社會的機制。社會學的發問,不在於消費社會本身道德或不道德。理解消費社會,同樣必須拉開社會史的景深。 消費社會的顯著特徵,最初受到注意的背景是一次大戰之後美國出現以廣告業、電影工業、時尚與美容工業、大眾報刊雜誌、大眾觀賞的運動競賽等因素而
造成新的品味、趨勢、經驗與觀念持續發展的消費文化。這也就是文化工業批判
理論所回應的社會背景。然而當這些特徵受到注意之後,社會史與經濟史的研
究,從原本侷限於生產與勞動的研究視野,轉而注意以消費為問題意識的回溯研
究。消費社會的源起,於是至少回推到十八世紀英國的中產階級。Mckendrick et. al. (1982) 將這個時期稱為「消費社會的誕生」:交通與傳播的進步使得貨物與人的流通更為便捷,時尚與消費的品味趨勢與社會仿效,以靈敏的意識與快速的步
調表現於服飾與家居物品。Porter(1990:190-196)指出當時商店與報紙的廣告,加上全國市場快速進步的物流(retailing),使得家俱設計、裝潢擺設、衣飾布料、髮式帽款、寵物與盆栽的類種,都追隨令人炫目的流行步調。國家節慶或紀念事件
的象徵圖案,印製於手帕或瓷杯上銷售,一如今日的紀念品商店。進口的茶、咖
啡、巧克力等等原是昂貴的奢侈品進入了國民飲食。商業化娛樂、音樂、戲劇的
購票觀眾,以及咖啡館、遊樂園、酒館、劇院、演奏廳都快速成長。
十九世紀,隨著廣告業、百貨公司、假日遊樂場所、大眾娛樂休閒的發展,
消費社會更擴及西歐與美國的工人階級。從這個過程來看,大眾消費似乎具有民
主化(democratization)、平等化、消泯階級對比的作用,劣勢階級似乎首度得以在大眾流行的範圍之內,仿效優勢階級的消費活動與生活方式。然而波迪厄的《區
別》(Bourdieu 1984)提醒我們持續存在的對反趨勢:消費活動、品味與生活風格,仍然是身份地位的戲局,而且是極為認真嚴酷的戲局。社會學很早就認識了這個
辯證關係:模仿與仿效的結果並非趨於平等,而是體現並完成了差異與分化的動
態結構。齊莫爾(Simmel 1997[1905])指出這是時尚流行(fashion)的動力,現代生活的個體置身於快速變換的流行與繁多目迷的樣式之中,其表現主體性的「提升」
10
-
與「模仿」卻同時是階級分化的「排拒」與「限制」。齊莫爾討論時尚流行時特
別關注於現代都會的中產階級,然而伊利亞斯在其《文明化過程》(Elias 1978, 1983)卻指出藉時尚流行、舉措禮儀、生活風格而表現自我與品鑑他人的消費藝術,宮
廷社會的貴族早已非常嫺熟。環繞宮廷社會的早期資本主義城市,已出現了相當
規模的消費社會,其條件不僅是商業化的器物——車馬僕傭、家俱地毯、餐飲器皿——而且包括生活中飲食起居與兩性關係的行為舉措與態度。
由消費的問題意識所開啟的社會文化史研究,絕大多數以早期現代歐洲社會
(early modern Europe)為研究對象,因此容易流於以「消費社會的源起」來解釋「西方的崛起」。Craig Clunas (1991)警惕於這種偏誤,而研究中國明清時期(early modern China)的物質文化與社會地位,卻發現中國仕紳階層與同時期歐洲菁英有極為近似的消費社會:服飾、家具、書畫、瓷器、玉雕與種種賞玩的器物,不僅
有高度商業化的市場,而且衍生出各種品味與鑑賞的文學、書籍與觀念。而器物
與藝玩的商品消費、鑑賞的能力、舉措言語的雅俗,既是區辨身份的社會策略,
也交互譜出一套差別分化體系的象徵性語言。 如此回溯,我們摸索到消費社會的一項關鍵特質:商品、器物、經驗與形式
的繁複與廣泛到達相當程度,令某些人口得以分化其慾望、志趣、獲取、消費,
因而形成區辨的符號體系,而且是個藉時尚流變而實現的動態體系,仿效與變異
同樣是推轉這個符號體系的動力。隨著商品與市場的擴展,這個符號體系的分化
程度越趨繁複,其整合的人口也從早期現代的菁英階層逐步擴及中產階級與勞工
階級,終於形成本世紀顯著的大眾消費社會。 阿多諾的文化工業理論認為支配生產過程的工具理性也成為支配大眾消費
的特徵,休閒、藝術與文化都透過文化工業而出現,其消費都受到交換價值的支
配;廣告、媒介與展示商品的技術,藉著附加的影像而連結整套的感覺與欲望,
最平凡的消費品——肥皂、電器、汽車、飲料——足以連結浮動的符號:浪漫戀情、異國情調、青春、成就、社群歸屬、科學進步…於是交換價值的支配,顛覆了器物原初的使用價值。阿多諾文化工業理論的商品批判仍然保留馬克思將交換
價值對立於使用價值的脈絡,布希亞在七0年代觀察消費社會(Baudrillard 1981, 1996, 1998),卻拋棄了這些舊範疇,進一步運用符號學(semiology)來分析商品/符號的邏輯:消費,牽涉積極的符號操弄。晚近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在於商品符
號的生產。廣告與媒介得以操弄符號,意味著符號相對於器物有全然的自主性,
可以自由進入多樣的連結關係。 馬克思假定了有個滿足自然需求的使用價值,以對比商品交換價值的拜物性
格。布希亞(Baudrillard 1975)卻點出了馬克思未覺察的矛盾:使用價值之為「價值」,已然預設了符號體系,因此由使用價值所界定的勞動與需求,也早已在符
11
-
號體系之內被界定。消費活動並非回應於任何自然的需求,消費者選擇飲食衣
著、修飾容貌體態、享受他人服務…都是回應社會認可的符號。以 Mary Douglas(1982:16)的話來說:對消費者而言,消費的愉悅,並非自然需求的滿足,而是一種實現其社會義務的愉悅。布希亞發展商品邏輯的符號學批判,將原本馬
克思理論唯物的強調,轉向了文化的強調。他稍後的著作(Baudrillard 1983a, 1983b)描繪藉媒介而無盡複製的影像與過度生產的符號消泯了擬象與真實的區別。詹明
信(Jameson 1984)則以布希亞的脈絡指出:在符號飽和、影像氾濫的消費社會,「文化」已具有新的廣涵意義:我們社會生活的任何事物都可說是已成為文化的。
這個新視野,波迪厄的「文化資本」概念與布希亞的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可
謂相互呼應:「文化」能夠成為「資本」,意味著與經濟資本一樣,可以計算、可
以交易、可以兌現、可以獲利,也同樣有其統治的模式與積累的過程。波迪厄
(Bourdieu 1987:243)指出文化資本的三種形式:具體表現形式,例如自我呈現的風格、談吐、儀態等;客體化形式,例如書籍、錄製的音樂與影像、器物、建築;
以及體制化形式,例如教育資格、文憑、證書、獎項、智慧產權的專利。這三種
文化資本的形式,大大擴展了我們對於文化工業類型的認識。 原初批判理論所界定的文化工業,僅屬於客體化形式的大眾文化產品,而且
是象徵性階序中較低階的產品。例如,當我們將不同的文化資本形式置放於晚近
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的脈絡中,可以看出特別以城市為單位而競爭的文化工業,不
限於爵士、搖滾樂、電影、購物中心、主題公園以及種種通俗文化場所,更包括
博物館、美術館、歷史建築與藝術資產的保存——所謂「資產工業」(heritage industry)。巴黎、羅馬、佛羅倫斯等城市在這方面的文化投資與聲望積累,趨於象徵性階序的頂端。然而文化工業產品的象徵性階序並非固定不變,而且高階與
低階之間有既鬥爭又相互依存的生態關係。例如紐澳良原屬下層生活區域的酒
館、妓院、爵士樂,巴爾的摩的舊區與碼頭,都可再度上流化(gentrification)而提升為吸引觀光客眷顧的盛名景點。紐約的蘇活區因為低租金而成為藝術家聚落,
藝術家生活風格的氛圍卻吸引新中產階級的移入而再度上流化。七0年代以降,
許多城市逐漸認識必須動員「文化」以作為「資本」的誘因,積極結合企業領袖
與都市計畫專業,以擴充「藝術基礎設施」(the arts infrastructure)來消除大量失業人口,換言之,藝術與文化的形象(images),可以直接轉譯為地方經濟的就業機會(jobs)(Featherstone 1991: 106-107)。
阿多諾(Adorno 1991:85)曾悲嘆文化工業消泯了純藝術(high arts)與通俗藝術
的界分,並且取消了各自原有的抗爭空間。確實,自六0年代以降,不僅藝術本
身形成顯赫的國際市場,前衛藝術原有的挑釁、逾越、反文化的波希米亞姿態,
在都市官僚、投資人與開發者看來,不再是麻煩問題,反而是為低租金衰敗區域
培植有機土壤以供上流化再開發的先拓者。現代藝術已喪失了任何抗爭的危險
12
-
性,不僅就都市空間而言如此,布希亞(Baudrillard 1981:110)與波迪厄(Bourdieu 1993:106)以不同的方式指出了一項事實:現代藝術的前衛運動自我標榜對既存藝術體系的摧毀、批判、創新、不斷超越,然而所有尋求斷裂、歧出、差異、革
命的企圖都在這廣涵的符號體系之下立即被接受、同化、整合、消費。所有顛覆
的創意、想像、姿態,非但絲毫沒有撼動這個符號體系的秩序,反而成為輪轉這
個體系的動力。前衛藝術,一如時裝與汽車的年度新款式,推動了形式不斷循環
交流的時尚,一場藉消費而整合的大戲局。 藝術、時尚、次文化、娛樂、出版、影視、媒體、音樂、觀光旅遊…自紐約、
東京、倫敦、巴黎、洛杉磯、聖保羅之類的世界城市以全球化的幅距而傳佈:文
化工業隨著日漸廣涵的文化資本形式而貫越金融、傳播、資訊等等傳統的概念領
域。這個消費/符號體系的動力,不斷拆解傳統的雅/俗、菁英/俗眾、大眾/小眾、藝術/生活、品味/粗鄙等等文化階序,就這個角度來看,常被指為後現代的「文化脫序」。然而同樣的符號/消費動力卻同時活躍地在個人之間、階級之間、區域之間與城市之間持續進行新的分類、階序與區隔,就這個角度來看,顯然是文化
支配藉分化而整合的力量。在消費文化的脈絡下,生活風格、認同與區辨、外表
與自我呈現、時尚的設計,不斷拓展並培養動態易變的品味感受,而任何新樣式、
象徵性物品與經驗形式的生產都已成為文化工業。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與文化
資本理論之後,我們很難再以傳統熟悉的產業範疇來定格文化工業,而必須在生
產與播散消費的流動中見證複雜交疊的變形:科技、金融、媒介影像、資訊、觀
念、人物——無論是追星族的偶像、前衛導演或名作家——文化工業遍在!
文化工業的政治模稜:地方、國族、全球、次文化 我們仍然面臨類似阿多諾與班雅明半個多世紀前的模稜政治判斷。文化工
業—符號消費體系,若如阿多諾描繪的,是支配控制,那麼我們更感到絕望,因為今日這個體系更為廣涵而遍在;若如班雅明所期待的,具有解放的潛力,那麼
我們或許可以樂觀,因為今日這個體系的活力與豐富更勝往昔。我認為,這仍然
是我們所身處的模稜狀況,也應該是同時兼具的警覺。政治抉擇,或許不在於抽
象地否定這個體系,因為任何批判否定的激進姿態,可能都是這個體系歡迎的變
異與延伸,成為學術場域、輿論場域、政治或社運場域裡消費的利基(niche),媒體與出版業甚至樂於徵召批判的意見、贊助否定的姿態。猶如拒絕商品的 DIY生活方式,拒絕商標廣告的無印良品,拒絕美學成規的前衛藝術,卻立即成為新
的市場利基,為消費體系增添新的可選符號。毫無例外,文化工業包裝行銷任何
批判否定文化工業的觀念與人物。我們其實找不到出路,因為沒有界外(No exit, for there’s no outside)。
體認這個絕望情境之後,我們還是有政治抉擇的責任,因為,既然文化工業
13
-
成為遍在的體系,也許我們自覺或不自覺的已成為文化工業的門房、掮客、或業
者。文化工業—符號消費體系,是抗拒的對象或是解放的潛力,隨著局部的情境與分殊的價值而無定論。因此沒有教條準則,以下是我就前文已討論的範圍,略
作推演的幾個立場。 日漸全球化的符號消費體系對於國家建立或保有國族共同文化的企圖,構成
了強勁的威脅。某些階層、某些專業的生活風格、工作環境、習性與行為態度,
已跨越國界而在世界城市之間形成匯通與聚合。另方面,原本由國家打造國族文
化所企圖同化的各種特殊群落、地方性與異類生活方式的群體,卻得以藉由符號
消費而獲得認同,得以策略性地表現其抗拒同化的獨特性。在國族建構過程發揮
重要功能的文化工業——報紙、廣播、電影、電視——並非不再服務於國族認同的建構。國家慶典或皇家婚禮之類的儀式、國際衝突對抗的事件(例如波灣戰爭
或科索夫使館誤炸事件)仍然藉由媒體事件而經營國族傳統與共同體的神聖感。
然而在文化產品與資訊流通的全球脈絡中,卻越來越不容易以國家領導的同化運
動來統一或消除地方性與異質性的認同。Featherstone (1996)指出「全球化」與「地方性」並非敵對概念。當代的全球情境並不意味著文化趨於統一或同質,文化資
源也並未趨於貧乏或稀薄,相反的,地方文化可以在全球情境中援取更為豐富的
象徵性劇目,建構獨特認同的集體象徵、感情、記憶與歸屬感。然而,全球化確
實意味著知識、習俗時尚、生活方式的發展,越來越獨立於國族的控制。 鞏固國家主權與國族傳統的立場,常以「文化帝國主義」論點來反擊全球化
趨勢,指控由跨國企業支配的文化工業,將其文化產品與資訊由核心播散至邊
陲,並以這種能力來削弱並解離國族文化。然而當前的全球化脈絡很難再被簡單
化約為西方文化的霸權。地方通俗文化的音樂、飲食、衣飾、工藝都可能包裝而
進入世界都會與他處的文化超級市場(cultural supermarket)。而商品、資訊與影像經常由多種文化傳統與生活形式的混類、合成而產生。將文化因素分解、混類、
拼湊、合成的過程經常被視為後現代的多元文化特徵,然而以歷史而言,多元文
化社會(multicultural societies)並非源起於倫敦、巴黎這些核心的城市,而是里約熱內盧、加爾各答、新加坡與香港這些邊陲的殖民社會。樣式多變、交錯異位的
合成文化,首先發生於這些邊陲。戰後時期,這些前殖民社會的移民與文化持續
流入西方都會之後,核心的城市才沖積出多元文化社會,並相應地在文化傳統、
社群與國族的認同建構上出現新的複雜度。因此,將全球化視為由西方核心流向
邊陲的單向支配,不再是個確切的圖像。 對於追求統一、純淨、完整國族文化的基本教義立場,威脅未必來自西方核
心,任何「外來」——來自概括的他處(generalized elsewhere)——的文化成分,與內部抗拒同化的異質成分,都足以造成不純(impure)的威脅。地方主義與異質認同,若援引全球脈絡的文化工業而抗拒國族的同化事業,當然被視為雙重威
14
-
脅。捍衛國族文化主權的立場指控:「全球化理論是(西方)特定支配勢力的自
我代表」。但這項指控也弔詭地反指控了「國族化」本身。因為國族化也總是以
部份代表全體,將核心族群與優勢階層的興趣與志向,表徵為無異議的全體共
識。國族化依據優勢群體而發展的集體共同形象(we-image),也連帶對劣勢群體外加並內化集體恥辱、不名譽、不配、污名的形象,方言、習俗、生活方式從而
依尺度而判分正確或不當、典雅或鄙俗。換言之,國族化本身就是內部殖民化過
程,統一形象之下是階序差等的控制關係。因此當地方性弱勢社群得以依托較廣
的全球文化脈絡,國族化的控制力減弱,可能相對是個民主化的解放歷程。 以同樣的分析我們可以理解許多藉由符號消費而出現的新「種族」,特別是
在大城市出現的青少年次文化或同志次文化。這些是抗拒的認同,抗拒「同化」
於成人規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或異性戀體制。他們消費的形式與經驗,原宿、
龐克或同志,往往有跨國的脈絡。他們藉著消費同類出版物、音樂、服裝髮式、
身體造型、社交場所、搖滾或銳舞演奏會…而發現彼此並維繫認同。環繞著一個次文化認同,就幾乎可以識別一個我稱之為「次文化工業」(subculture industry)的系列:書刊雜誌、書店、CD 唱片、服飾店、美容與身體造型專鋪、Pub、Bar、健身房、跨國偶像、演奏會事件…即便是廣告製作、時裝設計與櫥窗展示也都不會忽略吸引他們(特別是同志)的形象。
若以馬克思主義商品批判的觀點,無論這些認同的抗議姿態是什麼,他們是
徹底被資本主義市場收編或開發的消費者;資本家未必認可龐克或同志作為社會
主體,卻歡迎他們作為消費主體。然而換個立場,歷史學者與文化研究者卻指出,
資本主義與消費社會確實是這些新「種族」得以出現的歷史條件(D’Emilio 1993, Clark 1993, Hebdige 1979)。符號與樣式的消費活動,使得同類得以相互發現、社交、傳遞經驗、建構集體認同、維繫社群生活、甚至宣示政治議題。事實上,
次文化的出現、認同形象的可見,相對於原本受到禁制消音、邊緣化、污名化、
必須躲藏遮掩的存在,已經是獲得自主的解放。次文化以樣式作為抗拒(style as resistance),經常受到質疑,因為商品化成功的邏輯就是開發樣式,例如女同志穿著男性寬外套與大頭鞋,原初為了好玩並抗議女性時裝與鞋款的拘束不便,卻
被時裝界開發為高價位流行款式。然而如 Hebdige (1979:93)指出的,次文化就是因為樣式創新而吸引了媒體的注意,也為認同政治開創了「可見的」社會空間。
當消費文化成為「認同」與「政治」的必要條件時,「資本主義收編」就相對顯
得是迂闊的批評。
Cyberia.com ——網際文化工業及其餘數:代結語 「文化工業」批判理論出現的年代是電影、無線電收音、電視,也就是廣
播(broadcast)模式的年代,無論技術上使用無線電波或是同軸電纜,其特徵為寡
15
-
頭的製作者將資訊發送給大量的消費者。Mark Poster(1995)將這個階段稱為第一媒介時代(The first media age)。這個時期唯一例外的媒介是電話,在電話系統中任何人可以發送訊息給任何人,而且收訊者/發訊者位置可以普遍互換。晚近模仿電話這種民主結構的媒介科技是網際網路(Internet)。電話線路傳送資訊的能力原受限於技術因素,直到八0年代後期,科技創新引進了光纖電纜、數位製碼、
音訊/文件/影像的傳送、壓縮資訊的技術、無線傳訊頻域大幅拓寬、切換技術創新,到廿世紀末葉,網際網路的使用持續快速普及。資訊高速公路的構築,使得
無論是有線或無線的資訊傳輸能力快速提昇,可以在片刻內將任何形態(音訊、
文件、影像)的資訊傳送到網路上的任何一點。「高速公路」的譬喻僅指涉資訊
的流動,還未包括網際空間(cyberspace):會議廳、工作區、虛擬社區、購物廣場、網際法庭、線上銀行,甚至一個包含提供市政資訊的市政廳、公務區、圖書館、
咖啡座、郵局、博物館、以及提供狂野幻想的後街暗巷等等虛擬公共空間的數位
城市(Digital City)。8
新科技的潛力引起熱中於未來的預測:電視、電信、電腦、家電、出版與
資訊服務等既有傳播科技將進一步匯聚為一個整體的互動資訊工業(interactive information industry)。例如,目前傳送電視節目給用戶的轉換器將也可以從用戶家裡傳送影像到他處,甚至發展為電視電話,同一個系統,任何人只要用一台攝
影機就可將影像傳到世界各地(Elmer-Dewitt 1993:52)。而無線電信的科技將促使區域性無線網路系統的出現,可以同時交換聲音、資料、影像的寬頻弱波無線網
路將取代長頻強波的主機廣播系統(Gilder 1993:107)。對比於第一媒介時代的電影、無線收音、電視等媒介單向播送、缺乏互動可能性、由寡頭製作內容、由大
眾被動收聽收視的廣播模式,Poster(1995:18-22)將資訊高速公路整合衛星科技、電視、電腦、電話而出現的新媒介系統,雙向的、除中心的、多元而且製作者/發送者/消費者可以互換的傳播,稱為第二媒介時代(the second media age)。若將第一媒介時代標籤為廣播模式(the broadcast model),第二媒介時代或許可以標籤為網際模式(the internet model)。從廣播模式到網際模式,意味著傳播關係的新形構,也具有符號政治經濟學的深遠意涵。
前 Lotus 1-2-3 的開發者 Mitchell Kapor(1993:55)指出網際模式因為創造了新
的發言位置而開啟了新的政治機會:廣播模式的媒介使用者對於資訊取得的時
機、內容、理由、來源(when, what, why, from whom)所能有的控制十分有限(關機、轉台),也因此養成消極被動、愚鈍與平庸的消費主義。而網際模式的媒介
使用者則因為能夠直接掌握資訊交換的時機、內容、理由、來源與去處,因而可
能培養批判性思考、積極與民主的特質。這個類似於 Enzensberger 的樂觀論調,或許也同樣流於過度簡化的圖像。在 Time、Forbes 之類雜誌對新媒介科技的報
8 參考 1994 年開站的De Digitale Stad(Digital City),荷蘭阿姆斯特丹在網際網路上的虛擬城市,見Brants et. al. (1996)。
16
-
導裡,確實常見這種預想未來的樂觀主義。隨著網際社會的興起與網際空間的日
趨重要,媒體與文化論辯燃起了一波「電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 tele-democracy)的興奮論調。簡單的科技烏托邦或科技決定論傳佈著電子通訊帶來的福音:只要一台基本的個人電腦和數據機,任何人就可以參與、互動、甚至
塑造範圍極廣的多媒體空間,不再受限於往日被動接受報紙、廣播、電視的狹窄
選擇;任何人從他的書桌就可以進用網際網路所提供的全世界任何主題的大量資
訊來源,也不再受限於地域、殘障、性別、種族這些在往日造成壓迫與卑屈的個
人特質;在網路上發表資訊也如進用網路一樣簡單,沒有任何中央的權威來管制
誰能做什麼、在哪裡、為什麼(who can do what, where and why)。從這個論調聽來,似乎是史無前例的解放,個人從來未曾享有如此巨大的可能性。
然而對於新傳播科技轉變社會形構的過程,我們有理由謹慎的質問:若資
訊社會意味著工業資本主義之後一個新的社會形構,那麼資訊社會預示了什麼新
的文化政治?資訊基礎架構的設計、構築、操作與經營的成本是真實的,擁有或
掌控這些傳播系統的權力,熱烈展望未來的著眼,是其民主潛力,還是其權力與
利潤潛力?從本書鄭陸霖分析的台灣有線電視產業,我們可以試著推問台灣未來
多媒體文化工業的政治經濟切面。我們不妨用「網際文化工業」(cyberculture industry)的問題意識,來預想目前急速發展,我們仍未能清晰理解的狀況。網際空間的發展將貫越並重組所有既知的文化工業形式,從娛樂到出版、從廣告到新
聞…由於其穿透各種傳統疆界(不只是國界)的滲透力,將顯著地影響符號消費與生活方式的全球脈絡、國族的文化主權、地方與次文化的認同建構、社運的動
員方式、公私領域的界分…。換言之,所有本文討論的「文化工業」問題及其政治模稜,都將因而推向更複雜的層次。Manuel Castells(1996:xv)《網路社會的崛起》,卷首第一句便告白:「這本書進行了十二年,我的研究所企圖捕捉的對象,
卻以遠超乎我研究能力的速度擴展」。許多社會學者或許有同感。在工業革命衝
擊之下解釋現代社會而出現的社會學,顯然遭遇到了資訊革命的挑戰,許多狀況
的新發展,我們還只能約略覺察。然而社會學的一些基本常識,仍然足以使我們
對當前的科技陶醉(techno-euphoria)提出一些懷疑。 網際網路使得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對任何主題自由地進用所有
資訊。這是個流暢的玩笑。電腦與周邊設備、上網費以及連線電話費,總計年開
銷大約可以養活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四口之家。即便是在台灣,能享用網際網路
的也是受過教育的中上收入家庭。也並非所有網路上的資訊都是免費的,從政府
到研究機構與尖端商用科技,許多真正有用的資訊是鎖碼的。網路上的資訊流通
與貨幣流通一樣,有複雜的市場與層級結構。網際網路使用者的精確人口普查並
不容易,而且以其成長速度,可能需要每月或每週更新。但是美國與歐洲的一些
統計數字已可提供網際網路使用者的人口學側描。例如白宮電子郵件系統的使用
者資料顯示:比美國人口(母體)年輕、教育程度高、男性、75%擁有大專學位、
17
-
50%擁有研究所以上學位、41%的使用者隸屬於大專院校、只有 20%的使用者為女性(Hacker 1996:223)。阿姆斯特丹的「數位城市」(Digital City)市民的側描則是:年輕(58%為卅歲以下)教育程度高(四分之三受過大專以上高等教育)有職業的男性(女性人口從 1994 年的 9%成長為 1995 年的 15%)(Brants et. al. 1996:242)。上網的年輕知識菁英,或許已經在網際空間發展草根性的組織與動員策略、抵制
並挑戰資本與媒體的支配、嘗試草根性虛擬社區的民主實踐。然而網際人口學的
側描,顯然與慶賀「電子民主」的烏托邦相距甚遠。 網際空間基本上是無疆域、無管制的,個人或群體可以從事任何類型的活
動而不受什麼監管。這是另個玩笑。網際「空間」(cyberspace)的譬喻,令我們警覺任何空間都是構築的,有其「界限」。網路的操作性構築重劃了空間的界限:
重新界定誰在局內誰在局外(inside/outside)、許可進用/拒絕進用(access-granted/access-denied)、平台相容/平台不相容(platform compatible/platform incompatible)、可操作/不可操作(operational/inoperable)等等(Luke 1995)。因此網路連線本身就成為新的社會衝突點。網路掮客、網線詐欺、駭客、電子竊盜等是(違)
規(犯)禁(逾)限(越)界的形式,而規則與區隔制訂、執行、詮釋的權威與
權力都在重新形構,且經常逸脫於傳統的政治與司法形式。因此在期許真實生活
(real life)的民主參與之前,虛擬生活(virtual life)的民主參與本身就是個問題。網際空間的運作有賴巨大的物質基礎以及複雜的技術支撐,數百萬個人電腦透過諸
如微波塔台、通訊衛星、光纖網路與線上服務等有線或無線系統而連結,所有部
份的互動結合而成網際空間與虛擬實境得以運作的電子通訊領域。由誰設計、擁
有、經營、操作就成了關鍵問題,因為牽涉了顯著的權力與利潤潛力。Wired 執行編輯 John Battelle 說:「人們終究必須瞭解,網路不過是另個媒介,必須受到商業的贊助,也必須按照市場規則來玩」(引自 Kroker 1996:167)。而市場導向的網路經營者不僅有促銷與流通商品化資訊的興趣、構築與設計的技術,也握有關
閉與排除的權力。 社會學家已普遍認識到在從工業社會轉型到以服務業為主的後工業社會過
程中,社會階級逐漸出現兩極的分化,一方面是遭舊產業尤其是製造業淘汰的失
業人口與轉業到低收入次級勞力市場的人口,另一方面顯著成長的新富則集中在
所謂「先進服務業」(advanced services)——軟體、金融、教育、醫療、商務、觀光、物流、文化工業——裡的上層專業人口。這個兩極分化表現於所得差距的顯著擴大。先進服務業的上層專業人口的特徵是:擁有高水準的文化資本、享有優
渥的資訊環境、具有符號技能、他們製作/生產符號——包括知識的、道德的、情感的、美學的、敘事的與意義的面向,他們的符號產品以影像、錄音、或電視
等各種媒介發表,創新率高且受到智慧產權的法律保護,他們活躍於媒體,也在
市民生活的各方面具有意見能力。若以 “mode of information”取代馬克思的「生產方式」(mode of production)來說,他們是新資訊結構的贏家。相反的,貧窮化
18
-
的下層階級,不僅所得惡化,往日工業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例如工業勞動市場、
教會、家庭、工會乃至福利機構,都日漸解組或撤出,在取而代之的資訊結構裡,
他們的位置更為邊緣、在新興的網際社會裡他們仍不具公民身份,而急速擴張的
網際空間,也非他們所屬的空間。
阿多諾(Adorno 1991:170)在一篇文章的結語中暗示,或許唯有當我們的社會登於成熟(Mündigkeit)之境,也就是脫離文化工業宰制奴役的時候,我們才獲得真正的自由。我卻始終甩脫不了一個顛倒的視域:文化工業隨著我們社會的成熟
而日趨繁榮,幾乎遍在。離開了具體情境,我們越來越難以抽象的指認什麼是宰
制奴役什麼是自由解放。確定的是,在文化工業之外的餘數,未開發的或被遺棄
的,是我們眼中的——荒原或廢墟。
參考文獻
阿英,1973,晚清小說史,香港:中華書局。 程季華,1963,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冊),北京。 張靜盧,1957,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第三冊),上海:中華書局。
Adorno, Theodor W. 1954. “How to Look at Television”, The Quarterly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7 (Spring).
Adorno, Theodor W. 1991.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Edited by J.M. Bernstein. London: Routledge.
Althusser, Louis. 1970.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Barnett, Doak A. 1963. 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New York: Praeger. Baudrillard, Jean. 1975.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Translated by Mark Poster, St.
Louis: Telos Press. ——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Trans. by C. Levin.
Mo. St.Louis: Telos. —— 1983a.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Translated by P. Foss, J. Johnston
and P. Patton, New York: Semiotext(e). —— 1983b. Simulations. Translated by P. Foss, P. Patton and P. Beitchman. New York:
Semiotext(e). —— 1996. The System of Objects. Translated by J. Benedict. London: Verso. —— 1998. The Consumer Society. London: Sage. Bauman, Zygmunt. 1990.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9
-
5(2-3). ——. 1992. 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 1993. Postmodern Ethics. Oxford: Blackwell. Benjamin, Walter. 1969.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Illuninations. New York: Schochen Books.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 N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 1987.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8. On television. Translated by Priscilla Pankhurst Ferguson, New York: New
Press. Brants, Kees, M. Huizenga and R. van Meerten (1996) “The new canals of Amsterdam:
an exercise in local electronic democrac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8 (April): 233-247.
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Chu, Chia-hua. 1937. China’s Postal and Other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London:
Kegan Paul. Chu, Yuan-horng. 1990. Dialectics of Liberation: A Genealogy of Revolutionary
Reason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Clark, Danae. 1993. “Commodity Lesbianism,” in Abelove, H. et. al. (eds)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Clunas, Craig. 1991.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Darnton, Robert. 1982.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avis, Natalie Zemon. 1975.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Emilio, John. 1993. “Capitalism and Gay Identity,” in Abelove, H. et. al. (eds)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Douglas, Mary. 1982. “The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Religious Change,” Daedalus, 111(1).
Eisenstein, Elizabeth L. 1968. “Some Conjectures About the Impact of Printing on Western Society and Thought: A Preliminary Report,”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0:1-56.
——. 1969. “The Advent of Printing and the Problem of the Renaissance,” Past and
20
-
Present 45:19-89. Elias, Norbert. 1978. The History of Manners. Translated by E. Jephcott. New York:
Pantheon. ——. 1983. The Court Society. Translated by E. Jephcott. New York: Pantheon. Elmer-Dewitt, Philip. 1993. “Take a Trip into the Future on the Electronic
Superhighway,” Time (April 12).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1982. “Constituents of a Theory of Media,” in Critical
Essay. New York: Continuum. Hebdige, Dick.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m. Featherstone, Mike. 1991.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 1996. “Localism, Globalism,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R.Wilson and W.
Dissanayake (eds.) Global/Local: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Fiske, John. 1987. Television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Fromm, Eric. 1941.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Gilder, George. 1993. “Telecosm: the New Rule of Wireless,” Forbes (March 29). Habermas, Jürgen.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Hacker, Kenneth L.. 1996. “Missing links in the evolution of electronic
democratiza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8 (April).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W. Adorno. 1969.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Continuum. Jameson, Fredric. 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 Jay, Martin. 1993. “Mass Culture and Aesthetic Redemption: The Debate between Max
Horkheimer and Siegfied Kracauer,” in J. McCole, S. Benhabib and W. Bonß (eds.) On Max Horkheimer: New Perspectives. The MIT Press.
Kapor, Mitchell. 1993. “Where Is the Digital Highway Really Heading? The Case for a Jeffersonian Information Policy,” Wired 1:3.
Kellner, Douglas. 1989. Critical Theory, Marxism and Modernity,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Kracauer, Siegried. 1947. From Caligari to Hitler: 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roker, Arthur. 1996. “Virtual Capitalism”, in S. Aronowitz, B. Martinsons and M. Menser (eds) Technoscience and Cyber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Lee, Leo Ou-fan and Andrew J. Nathan. 1985. “The Beginnings of Mass Culture: Journalism and Fiction in the Late Ch'ing and Beyond,” in D. Johnson, A. J.Nathan and E.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1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öwenthal, Rudolf. 1938. “Public Communications in China Before July 1937,”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2-1. Luke, Timothy W. 1995. “Simulated Sovereignty, Telematic Territorialit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yberspa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Conference, “Culture and Identity: City, Nation, World”, August, Berlin, Germany.
Marcuse, Herbert. 1955.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McKendrick, N., Brewer, J. and Plumb, J.H. 1982. The Birth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London: Europa. McLuhan, Marshall.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Mills, C. Wright. 1951. White Collar, Boston: Beacon Press. ——. 1956. The Power Elite, Boston: Beacon Press. Nathan, Andrew J. 1985. Chinese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orter, Roy. 1990. 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nd edn, Harmondsworth,
Penguin. Poster, Mark. 1995. The Second Media Age,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Simmel, Georg. 1997. “The Philosophy of Fashion,” in D. Frisby and M. Featherstone
(eds) Simmel on Culture. London: Sage.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ng, Lee-hsia Hsu. 1974. 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 Press in Modern China
1900-194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0.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2
文化工業與國族國家Cyberia.com ——網際文化工業及其餘數:代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