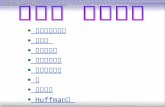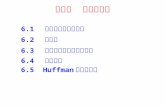家住军垦新都 - epaper.bingtuannet.comepaper.bingtuannet.com/pc/att/201904/19/c9eb693b... ·...
Transcript of 家住军垦新都 - epaper.bingtuannet.comepaper.bingtuannet.com/pc/att/201904/19/c9eb693b... ·...

与春天有约 栗卫平 摄
2019年4月19日 星期五电话:0991-5509362 第1699期 责任编辑:陆小龙 版式设计:任延雪
绿洲副刊 胡杨 7版绿洲副刊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左公柳也是援疆来的。当年阿古柏占领新疆,自立王国。左宗棠便带领部队,卖了家产作
为军饷,抬棺入疆,赶走了侵略者。而左公柳就是跟着左宗棠,沿着河西走廊,从陕西出发,一路上援甘肃、援新疆。
西北由于干旱少雨,从河西走廊一路往西,按照左大将军的记载,那是赤地千里、秃山如剥,黄风过时,沙土飞扬。当年在陕甘总督任上的左大将军,见到西北这种状况,于是带领将士,东起潼关,西至新疆,一路种植杨柳而来。
杨柳这植物的生命力也真是让人奇怪,无论南北,它都能够适应生存。在那些苦寒之地,甚至长得比在江南还要“健硕”,不腐不蛀不空心。以前冬天去北方,在一些湖边见到它,湖面都结冰了,可以走人走车,杨柳却还有些黄绿的叶子挂在枝上,敲一敲会掉下些冰碴子,来年一开春,那冻成冰棍的柳条上会立马发出新芽,瞬间吐绿。后来在西藏,也见到了许多杨柳,藏民说那是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和亲,嫁到西藏时带来的,种下后,杨柳竟然成了西藏地区的主要木材来源,布达拉宫高耸的门楼,就是用这些杨柳所建。
在阿拉尔市政广场的东边,有一排可以称之为“左公柳”的老杨柳。那些杨柳树干不高,扭曲而挣扎。粗壮的“腰身”要几人才能合抱。经历多年风霜的树皮长得厚实,如铁板敲打成的,被一片片、一条条地“焊接”在树干上。丝丝缕缕的纹理好像錾子凿刻过,又像一些老农布满皱纹的脸庞。老柳树的树冠很大,一根根枝条直直地撑
着,有些不愿意妥协的模样,甚至枝梢都硬生生地翘着。以前曾听老先生说过,杨柳是两个品种,垂下的是柳树,扬起的是杨树,按照这个观点,这一排老树就应该姓“杨”。“左公柳”似乎也就可以被称为“左公杨”了。
在阿拉尔,垂柳还是有的。我们住的小区西边的大马路两侧都有一行,树冠高大,比南方的大柳树要高上一半不止,直直地耸向天上,然后数米长的柳枝一层层地垂挂下来,浓浓密密的,像绿色瀑布。如果有风吹过,成排地摆动着,更加壮观。
在我的认知里,“左公柳”只是笼统的称呼,不仅包括柳树、杨树,还包括了耐碱易种的沙枣树等一些树种。
在广场的北面,还就保留了一片沙枣树的林带。沙枣树长得自由,在林带中,常见着一些倒着横着扭着的沙枣树,枝干错杂着,好像图画一样,有着不加修饰的天然之美。树冠上的枝叶连着,带着些青绿,浓密得发黑,连成一片。夏日无论多热的天,到了林带边上,就会感到阵阵清凉。沙枣花开,整个城市一片甜香。夏秋之后沙枣成串地黄了、红了,点缀在枝叶间,玛瑙珠子般透亮美丽。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因了这早早过来援疆的“左公柳”,所以这万里边疆,那些在戈壁荒滩中开出的城市和道路才有了更多的绿色。这些绿色,带着生机、引得春风,把这“赤地千里、秃山如剥”的亘古荒原改造为一个个绿洲,并串联为镶嵌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翠珠碧瑗。
左公柳●陈引奭
胡杨专刊
由树下工作室推出
诗丛
挂职日记(组诗)
●秦安江
农场
在这个尘土飞扬的地方我意外地邂逅了诗歌
过去我长期在那些没有尘土的地方寻找诗歌自从我踏入这个农场诗歌揪着我的衣襟抱着我的腿不让我离去
麦地里听《二泉映月》
瞎子阿炳在麦地行走麦子的对象千年不变音乐的对象千年不变美丽的忧伤追不上麦子
一垄垄麦苗在我的岁月里行走
下地
碱在地里的表现之一是虚土
一个上午我和赵政委、冯副团长就在这碱的丑陋的表现中艰难走着
鞋里全是土裤子沾满土头上落满碱的雪花
他们两个笑我:你知道甜菜是怎么长出来的吗
望着满眼碱地我像一颗陌生的种子开始了艰难成长
说到地窝子,人们就联想到兵团人。其实,现在的兵团人工作在广阔的田野里,生活在现代化的城镇中。电梯高楼、智能家居,已经来到昔日的戈壁荒滩。兵团大院、军垦新都、碧水戎城、青湖映象、青湖铭城、金碧天下、贝鸟语城、君豪绿园、北新佳境、阳光康居、国际蓝湾……五家渠市这些住宅小区的名字,令人耳目一新,甚至还产生一些栖居的诗意。
我家住军垦新都。当然,我也和这个小区的大多数住户一样,住过地窝子、窑洞房、干打垒、土坯房、砖平房,2013年才搬到这里的,要不然,为啥叫军垦新都呢。
我喜欢这个小区,因为它名字取得好:让人想起垦荒造田的艰苦岁月,让人珍惜今天生活的美好;因为小区规划好:楼房高低错落、布局有致,道路绿荫掩映、曲径通幽;因为它户型设计得好:方方正正,每间都有窗户,通风透光;因为它有运动场、业主文体活动中心而且背靠滨河公园方便散步;因为它的园林绿化:春天榆叶梅姹紫嫣红、丁香花浓香四溢,秋天山楂树挂满红红的小果……
虽说在平房里住了几十年,但人们很快适应了新居,爱上了新居。除了少数老年人抱怨电视遥控器上按键太多,有谁说楼层太高、电梯太快、地暖上不能烤馒头片吗?有谁说院子空地太少没法堆放柴火、没地方养鸡鸭吗?没有。倒是我,常常怀念团场那些树。榆树、白杨、沙枣树,给我的印象太深,记忆太深。这些本地树种,是团场防护林的标配,在城里却很少见到了。但是在军垦新都最显眼的地方,种植了一圈榆树。
那是建设单位在整体工程尚未竣工前,栽种的一道周长约1000米的护院林,而且是那种未经嫁接的本地原生树种。等业主入住时,榆树已有五六米高,且枝叶繁茂,俨然是看家护院的卫士。以它那经酷暑、抗风寒的雄姿,护卫着院内新种的草坪、新栽的小树;也让那伟岸挺拔的建筑物置身在绿荫之中,避免了新建小区楼高不见树的尴尬。
这护院榆树的生存能力,我敬佩。我们入住的头两年,还正常灌水,近两年,可能缺水吧,园林工人把有限的水量,都给了草坪和幼树,这榆树只好用它那深深的根,去吸取地下水。就这样,榆树依然枝叶繁茂,只不过那绿叶显得更加苍老,但这并不妨碍它榆钱挂满枝头,供人们采摘。春末夏初的时候,榆荚变黄了,成熟了,纷纷扬扬地随风飘落。只要遇到水,哪怕是一场阵雨,它都会吸饱水分,把根伸进地下,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幼苗。我见过园林工人费力地拔出那些长在砖缝中、草坪里的榆树苗,看地上不过二三十厘米高,拔出的根竟有四五十厘米长!偶尔留下的小榆树苗,三两年工夫竟然赶上了新栽的幼树。这种生存状态,不正是我们老军垦的品格吗?
这看家护院的榆树啊,又让人联想到我们的军垦老前辈、边塞诗人岺参——请不要质疑我对岺参的称谓,称诗人为军垦老前辈是有根据的。公元744年,岺参作为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僚属,分工就是负责屯田,包括军屯和民屯,而且常常坐镇轮台直接指挥。尽管当时的轮台是现在的乌拉泊还是昌吉破城子、六运古城尚无定论,但唐轮台在唐朝路上是肯定的,唐朝路上的五家渠属轮台的屯田范围是确定的,岺参作为
军垦老前辈也就是当之无愧的了。好,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这位军垦老前辈诗句中的榆树。岺参留
传至今的边塞诗有关榆树的至少有三首。其一是:“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三月无青草,千家尽白榆。”你看,“千家尽白榆”,榆树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榆树根深耐
旱,南北疆多有分布,是干旱地区生存能力最强的树种之一;而且抗寒,青草尚未发芽的时节,白榆已经开花了。历史上的灾年,树皮树叶皆能充饥。在新疆没有吃过榆钱的人可能不多吧,榆钱至今仍然是每年开春的第一道美味。那孩子们在榆树下的翘首以盼,妈妈们揭开锅盖时蒸榆钱飘出的满屋清香,也成了今天兵团人的乡愁。榆树这些优点深得人心,而且永不过时。老前辈岺参比我们高明的是,他既看到榆树的实用价值,还用诗人的眼光发现了榆树的审美价值: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千树万树的“梨花”正是榆树上的雾挂。诗人说,没想到啊没
想到,入秋季节忽然春风浩荡,一夜之间就吹开了千树万树的梨花。用春花比喻冬雪,把寒冷的冬天写出了春天般温暖的感觉。那么,这开满“梨花”的“千树万树”究竟是什么树?白杨,胡杨,柳树还是榆树?如果你仔细观察,白杨的枝条挺拔、树冠较小,更像风雪中英俊的哨兵;胡杨则树枝稀少、枝干沧桑,像是饱经风霜的老人;柳树呢,过于婀娜多姿,像个不畏严寒的舞者;只有榆树上的雾挂最美,更像梨花那一串串的花絮,更能给诗人如此美妙的意象。因为榆树的树枝茂密,有弯有直,且每个枝桠上都孕育着来年的花蕾,这些都是形成雾凇雾挂的有利条件。如果在春天,那挂满枝头的榆荚,就是一个淡绿色版本的“梨花开”。
军垦老前辈岺参看到了榆树的实用价值、审美价值,还由榆钱的形状联想到是否还具有“交换价值”呢:
“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道旁榆荚巧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岑参虽然是诗人又是官员,但他平易近人。他指着满树的榆钱问卖
酒的老汉:“我摘串榆钱来买酒行不?”你看这榆钱,让诗人多么风趣愉悦啊,多么畅快惬意啊。也由此让
我们想到,把榆荚称榆钱,至少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吧。不过,小区园林,除了它的生态价值,主要还是观赏,没有更多人会
关注树的历史和体现什么精神。我家楼前的那行榆树,虽说作为风景树,已经过嫁接改良,树叶变大了,树冠有了新的造型,但看久了仍觉单调,主要是它的颜色,从春到秋,一律带褐色的老绿,缺少生机,显然说不上亮丽。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榆树会因为颜值的沧桑而淡出江湖吗?美不仅需要发现,更需要创造。在榆树林中增加一抹嫩绿,会怎样?
入住后,我和邻居在那排榆树的旁边,掏出表层土下未清理干净的建筑垃圾,种植了一些槐树,最早种的已和我住的二楼窗户一样高。槐树也很有意思,每棵树的四周又长出许多小树苗,像个苗圃。出于对槐树的喜爱,大家纷纷把它移植到缺树的地方。
千家尽白榆的军垦新都、唐朝路上的军垦新都、我的家园军垦新都,老绿和新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交相辉映,构成了和谐的风景。那榆树林中飘动的绿云,是槐树青翠的树梢;那绿云里闪烁的火苗,是槐树红色的花絮。而这些,都离不开榆树的辅佐与映衬啊。
深陷在四月的门槛●王永健
天气预报说四月,醒来的花海会乘坐着风,蒙上你的眼会拖着长长的裙裾和红衣掠过,且撩起了下摆
这天上午,便爆出消息她改道来了你的庭院挟持着春意,拎着蓓蕾
“一个身份不明的客人,”有人暗中念起咒语。鸟鸣轰然响起朗诵新诗的声音落在了衣襟。细薄的白色、粉色掩盖不住地乍现陈年的杂草、古树递来热腾腾的嫩绿
我跨入四月的门槛,恰似云影恰似亿万年前大地、蓝天和水的冰清玉洁只能戴上眼镜,积攒香气与汝手挽手,步入良田
杞娜尔,杞娜尔一脸笑意在这个晴朗的日子,两盏砖茶两碟萝卜小菜,两个馕两碗粉汤,两盘抓饭生活的滋味仿佛一瞬间品味这一蔬一饭藏尽了岁月的安然
我深陷在四月的门槛怀揣隐约的醉意,在那一溜石墙下让花海次第扑面,先是零星几点接着大片汹涌一经活转,迅速充盈直至远方每片云朵都翠色阑珊
四月,我深陷在你的门槛女儿那淡淡的,缓缓的深沉温婉的英文朗读讲述着一个依稀的故事林徽因,撑着下颚坐在窗前,写下你是人间四月天
泡桐花开满枝条的时节,我回到了山西老家。踏着久违了的洒满一地泡桐花瓣的青石巷,黄昏时分,我被站在巷口已经望了几个小时的母亲和家人簇拥着进了家门。简单洗漱后,坐在母亲的土炕上,嚼着母亲端上的家常美味,不时品几口清醇的家酿米酒,酒酣耳热之际,几个孩子围在母亲膝前吵闹嬉戏。此情此景,直令难得偷闲的我置身亲情弥漫的快乐逍遥中,浮躁的心绪逐渐宁静而平和。
灯光下依稀看到母亲额前新生的几绺白发,禁不住眼眶里一阵酸涩。母亲在不知不觉中已显现出垂垂老态。感慨良久,心头忽然涌出一个问题:这些年,自己真正为母亲都做过些什么?于是,脑海里苦苦寻觅答案的同时,更多的是愧疚和感伤。
小时候,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母亲不爱我,关于母亲点点滴滴的记忆,似乎都是不爱的证据。我们姐弟五人,相继出生在那个清贫的家里。我来到这个世上时,我的上面已经有三个姐姐了。听亲戚说,在那个盼儿子顶门立户的年代里,母亲一看,又是一个头发稀黄、可怜兮兮的女孩,当时就想把我送人。我不知道这件事的真伪,也从未去问过母亲,然而这件事在无形中给我留下了阴影,我懂事后总感觉母亲不爱我。后来,我像一棵野草,哪怕只有一丝阳光雨露,也努力生长。尽管个头比同龄人小些,但自从我有了记忆,我很敏感也很自尊、自立。那时家里人口多,房屋少,尤其到了冬天,全家人挤在一个大炕上,抵御那寒冷的冬天。由于人多炕小,母亲便把我安排在她的脚边,也就是说她的落脚点就是我的
“起点”。每天早晨唤我醒来的,当然不是母亲温柔的呼唤,而是母亲给予我的动作语言——只要她一伸腿,就能很准确地踢到我的屁股。小学六年,母亲近乎苛刻地每天早晨把我踢醒,又要求我必须每次每门课拿满分,所以我偶尔粗心没考满分,小脸上便挂着泪水,久久徘徊不敢回家面对母亲。最后的结果便是母亲满镇上喊我,找到我后她的骂声招来的是我更响亮的哭声,愤怒至极的母亲便会顺手给我几下。于是我发奋学习,心想念书有成以后,拥有一张大床,再不用睡在母亲的脚边,自己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离不爱我的母亲远远的,越远越好。
打我记事起,耳聋的大妈和偏瘫的大爸就和我们吃住在一起,直到 1995 年他们去世。我们姐妹们每次放学回来,总看到母亲在给大妈梳头或是洗衣服、剪指甲什么的,她还常常让我们姐妹大点声陪耳聋的大妈说话。我常常小声对姐姐们嘀咕,说母亲如何对自己的女儿不好,对外人好。母亲听到后总淡淡地说:“老嫂比母啊。”偶尔收破烂的、修补锅的声音在胡同里响起时,母亲也会放下手中的活,急急地走出去,给人家找几件旧衣服,塞个馍,端碗水。通常端水的任务都会叫我去。有时我嘴里嘟囔甚至故意磨蹭时,母亲便会拍拍我的头,训我几句。在母亲的
“冷落”、斥责声中,我在镇上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无一例外地年年捧回各类奖状,甚至地区的学生作文大赛、书法大赛奖状。但母亲却从来没当面夸过我一句。
后来,我出去上大学,从山西跑到新疆工作、成家。还记得我初到新疆的日子里,只读过三年小学的母亲竟写了平生的第一封信给我,上面只有几个核桃般大小、歪歪扭扭的字:要听话,把活干好,不许给家丢脸。当时,漂泊失意的我,对家、对母亲虽有淡淡的牵挂,但还是埋怨母亲在我决定去新疆时没有阻止我,心想母亲就是不爱我,想让我离她远些。后来,直到我临产前一个月,从来没出过镇子、上车就晕车的母亲,竟然从家里坐了一夜的汽车到西安,先在西安买站票上火车、到兰州补上硬座,辗转几千公里来到新疆伊犁。我在四师六十六团的界梁子路口等了几个小时,看到母亲从晚点的夜班车上大包小包提着亲手缝制的小被子、小衣服、家乡的小米、芝麻走下来时,我忽然发现母亲老了,真的老了,母亲的皱纹一览无余地堆在眼角,白发肆无忌惮地在鬓角跳跃。我拉着母亲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刹那间泪流满面。那一刻,我似乎才深深地感受到,母亲的爱,其实一直离我不远,就那么一指之隔。
婚后的日子,我私下总觉得婆婆的厨艺难与母亲相比,便喜欢自己下厨。有一个年三十的下午,我在厨房忙活时,母亲打来电话,得知我在厨房做菜,又听着客厅里的喧闹,母亲良久未说话,喃喃自言自语:“静儿,就该这样,回家帮老人多做点事,我女儿懂事,妈高兴啊。”说完就挂了电话。后来我才慢慢感受到,母亲当时是心疼女儿。姐姐后来告诉我说,母亲当时放下电话就落泪了。
多年后的今天,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自己人生的每一步,无不受益于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母亲的坚强、勤劳、朴实、善良、大度,让我受用至今。出身贫寒家庭,“严母”让我知道生活的不易,知道前路需要自己去闯荡。
走笔至此,时已夜半。窗外风声不知何时已悄然停歇。木桌之侧,母亲盘膝坐着,检查着我行李箱中每件衣服上松散的扣子,然后一粒粒缝牢。静坐于这个温馨而宁静的夜晚,在这个和母亲只有短短一天团聚的日子里,沐浴着母亲无言的爱,我又一次泪流满面。
家住军垦新都●文定讴
有一种爱,让我泪流满面
●赵丽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