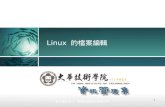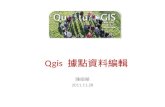走上音樂使者之路 -...
Transcript of 走上音樂使者之路 -...

二〇一二年三月四日 星期日14香港人家1051673責任編輯梁曉斌美術編輯譚志賢
蕭樹勝做事喜歡有計劃若某條路走到尾不見了光就轉身樂意嘗新卻不拖泥帶水不然他不會到了十七歲還敢從頭學小提琴不會在浸會大學學了兩年琴覺得不妥轉去聲樂不會去澳洲學聲樂學了幾個月覺得自己聲音條件不夠好又轉去作曲也不會放着好好一個研究馬勒的博士學位不讀轉身回港繼續做起忙前忙後的樂團行政來
不過他去年十月和太太一起去北京捧馬勒《第八交響曲》的場則純是 「計劃外」的偶然 「可能是我太 『發燒』了吧」
於是音樂 「發燒友」蕭樹勝和同樣愛樂的太太去了北京聽中國愛樂樂團的 「馬勒八」在國家大劇院看一眾婆婆公公組成的 「童心合唱團」唱《閃閃的紅星》又抽空去嘗了地道的老北京炸醬麵最後順着胡同彎彎扭扭地逛竟逛到中央音樂學院門前他一面翻看手機裡北京小遊的相片一面講那間炸醬麵館的好勸我下次路過北京時也去一嘗那個愛分享的蕭樹勝又來了 「這叫本性難改」他笑道
我趁機勸他分享自己心水的作曲家他說少時愛 「為賦新詞強說愁」喜歡悲傷的調譬如柴可夫斯基曾經有段時間又突然愛上蕭斯塔科維奇 「不過從小喜歡到大的是馬勒」
旋律太重 生病不聽蕭樹勝前段時間生了場不大不小
的病手術前後折騰了半年多生病的那些日子他不敢聽馬勒了說那些旋律 「太重」太嚴肅太糾結一講就講到宇宙萬物洪荒的大命題手術後傷口痛得厲害時他翻出莫扎特和孟德爾頌那些明亮悅人的曲子翻出床底下櫃桶裡藏着的五百多張黑膠唱片也翻出當年在巴黎歌劇院聽一百多人合唱《假面舞會》時的興奮記憶想一想痛就減輕了
蕭樹勝說等下半年身體康復了他會再去游泳去沙灘上曬太陽再去打網球玩橋牌再跟太太去北京吃炸醬麵最重要的是要買台黑膠唱機將太太送的小提琴練熟了再聽回馬勒聽回普羅科菲耶夫繼續做個「百分百的愛樂人」
蕭樹勝讀大學時暗戀同級一個唱女高音
的女生為愛情他隨她去學聲樂後來兩人結了婚婚後二十多年裡但凡外出度假必去當地歌劇院或音樂廳看演出散場後在外面廣場長椅上坐着看整齊穿軍裝的男孩子步操看日落時鴿群在空中劃過一道弧
在太太的影響下蕭樹勝喜歡上歌劇喜歡那些旋律以及歌者聲音中蘊藉的力量不過自稱歌劇 「發燒友」的他卻直言歌劇看得多了不免常覺失望因為左右一齣歌劇演出成功的因素太多 「合唱要好獨唱要好樂隊要好燈光和布景也要好」所以蕭樹勝看歌劇看了二十多年遇到真正心水的演出不多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次去巴黎開會會議間隙獨自散步去巴黎歌劇院正巧趕上瓦格納的《羅恩格林》
歐洲觀眾 相對成熟他說如今在香港演《茶花女》或
《卡門》不難賣票可若要嘗試現代一點怪一點的作品則 「不容易找觀眾」相比歐洲的歌劇製作和受眾群則相對成熟 「他們的歌劇院一個星期內可以有三場演出」蕭樹勝說歐洲的主要城市如巴黎或柏林通常有兩個較大規模的歌劇院歌劇舞台上常見 「很新很新的作品」卻依舊有觀眾樂此不疲去捧場 「大概是他們的文化比較開放吧」
香港的文化並非封固可是在 「音樂推廣者」蕭樹勝看來最關鍵的是要「給孩子們機會」因此港台在過去二
十多年裡一直堅持遴選 「樂壇新秀」不單純為比賽想評出冠亞軍而是希望這些愛音樂的孩子們明白自己所學自己所愛的究竟是什麼
走上音樂使者之路走上音樂使者之路
戀上太太 愛上歌劇
蕭蕭樹樹勝勝
馬勒情懷
始終如一
蕭樹勝說自己不是出色的作曲家或演奏者卻是合格的音樂推廣者(facilitator)
蕭樹勝在北京音樂廳與李德倫和蕭友梅的銅像合影兩位音樂家在他眼中都是出色的音樂推廣者
蕭樹勝在巴黎歌劇院欣賞威爾第的《假面舞會》和瓦格納的《羅恩格林》
蕭樹勝和太太陳少君同遊海南在天涯海角邊留影
蕭樹勝已在港台第四台工作十七年圖為他在港台錄音
室內
蕭樹勝練習新買的小提琴希望身體完全康復後可以
做回 「百分百的音樂人」
香港電台第四台節目總監蕭樹勝自小樂意跟音樂打交道彈鋼琴練小提琴學男高音興致來了也寫曲子自娛不過他一直覺得不論演奏歌唱抑或作曲自己都「差那麼一點點」 去英國讀音樂碩士那會兒他常問自己 「我究竟想走哪條路」
本報記者 李夢(圖文)(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彼邦求學 伴 「音」同行上世紀八十年代蕭樹勝從浸會大學音樂系畢業去英國謝菲爾德
大學深造只用一年時間便拿到作曲和演奏兩個碩士學位回想起來他直說那一年頗具挑戰開一場獨唱會擔任校樂團第二小提琴首席交一百五十頁的畢業作品閒時寫的器樂小品也常被校內敲擊樂隊叮噹叮噹地演奏
累是累但他喜歡喜歡那裡學音樂的氛圍 「四圍永遠是安靜的沒人喊你吃飯喊你睡覺你可以整晚整晚地作曲直到天明」這樣的自由安靜是蕭樹勝從未敢想也未經歷過的年少時家境不算優渥的他十七歲才開始學小提琴又因住屋逼仄不得已常拎把琴站在樓梯間苦練
因了這樣的好環境碩士畢業後的他想過留下讀博士 「當時有個研究馬勒的項目要四年時間」自知不擅長搞學術一番利弊權衡後蕭樹勝選擇回來 「把好好的青春放在研究馬勒上不是那時的我想要的生活」
那一年他二十五歲
第一份工 「音」不離手回到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 「翻開報紙找工作」第一份工得來並
不難全因他有備而來大四時在泛亞交響樂團做行政助理的六個月裡蕭樹勝練成了 「多面手」不單搬琴櫈抄琴譜的體力活做得來新聞稿寫得好聯絡樂手與組織排練也不在話下 「拿過香港管弦樂團的筆試題我就樂了」他回憶 「寫新聞稿不就是我天天幹的活嗎」
香港管弦樂團聽眾拓展經理這份工蕭樹勝做了整整六年其間參與創辦 「港樂」俱樂部 「樂友社」做過不下二百次音樂會司儀帶樂團去社區去學校巡演 「全香港都跑遍了」直至一九九五年加入港台第四台
在港台的十七年他籌辦香港亞洲青年音樂家比賽幫本地年輕演奏家灌錄CD還在沙士那年「不好受的春天」過去後參與組織香港公園內舉行的「為生命喝采」音樂會
加入港台 以 「音」會友在港台的十七年他不單做好分內事還一直主持康文署主辦的音
樂講座從巴洛克音樂一路談到肖斯塔科維奇再談到現代音樂透過類似的音樂普及活動他結識了若干好友拎過小提琴在李傳韻面前炫技的是他從何占豪那裡 「套」出作曲家最欣賞的《梁祝》演奏者的是他講座後和聽眾聚餐飯桌上推心置腹聊人生的也是他
蕭樹勝說做這些 「分外事」他從不覺得累只覺得享受 「可能因為我樂意分享吧」
分享與溝通是蕭樹勝從小養成的習慣若嘗到哪間餐廳的飯食靚回家後定會說服家人一起去光顧同樣長大後從事音樂這一行聽到哪個男高音的聲音靚又或哪個樂團的銅管聲部有力量也會說服身邊人一起去聽去享受
如今回頭看蕭樹勝終於清楚見到自己一直走的路不論抄樂譜辦講座為 「樂壇新秀」活動當評委抑或做台長他做的關乎音樂的一切無關愛樂人最常扮演的三個角色不是 composer不是 performer也不是audience而是facilitator一個貨真價實的音樂推廣者
有人說港台第四台現在的節目 「講話太多」最好少講多放音樂聽蕭樹勝卻不以為然 「我覺得教育和推介是公共廣播電台的使命之一」他正考慮增設一個 「不停講話」的清談類節目每周一期約本地樂迷和文化人來第四台演播室談猶太裔音樂家談俄羅斯鋼琴學派也可小聊幾段貝多芬和斯克里亞賓的情史
蕭樹勝一直記得自己某次在澳洲乘公車跟鄰座一藍領工人聊馬勒聊了一路的情形他期待有一天在香港的巴士上地鐵裡也能見到這樣一位講《大地之歌》講得頭頭是道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