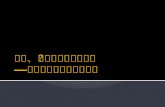责任编辑:王 昉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
Transcript of 责任编辑:王 昉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

36
“百年新文学视野中的新世纪文学”,
这个主题的两个关键词都让我感到难以
把握:“新文学”经过百年发展,纷纭复杂,
其内部充满此消彼长的相互作用与争夺,
以此为“视野”,究竟是怎样的视野?而
“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尽管已经被讨论
很久,但似乎除了时间定位的意义,始终
难以从内在特征加以概括和梳理,因此我
们所说的新世纪文学又是怎样的文学?
当然在此时谈论这一话题有着特别的意
义,那些如今已成巨人的文人学者们,就
在恰好100年前将中国文学带入现代,逐
渐形成新文学的灿烂图景;而由于某种关
于时间阶段的莫名轮回信念,我们难免期
待100年后的今天,文学与文化都会有一
次再出发。所以在这一主题下,我宁可暂
且不去考虑新文学百年来的复杂性,而回
到100年前的原点,思考那时候巨人们的
探索,对于今天会有怎样的启发。
大略而言,我以为在上个百年之初,
那时的知识分子至少在三个层面深入地
思考了“新”与“旧”的时代命题:其一是基
于家国情怀的思考,20世纪初叶的中国,
所有文学与文化的命题,无不在民族国家
的大命题之内;其二是对于知识分子自身
的思考,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知识分子这
一群体必须重新寻找自己的作用与位置;
其三是关于文学的思考,那当然涉及书面
语言的更替、文体的变化与创生,以及文
学之于外在世界的意义等等。
就第一个层面,新世纪文学至少面临
着两重困难。第一重困难是,我们经历过
文学与政治过度亲密的时代,那时候文学
活力的衰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
那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地向事情的另外一
端努力,不再愿意触碰宏大主题。更何
况,一个日益碎片化的“小时代”很快就来
临了,宏大之物似乎愈发被琐碎之阵淹
没,变得难以把握。因此随着越来越年轻
的写作者成为创作主力,新文学之初那种
立足于文学之外的伟大理想,在文学当中
越来越萎缩。当然,20世纪80年代去政
治化的文学立法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创作
者,这一方面使他们可以放心地回避崇
高,沉湎琐碎,退回个体;另一方面也在某
种程度上鼓励他们沾沾自喜于所谓文本
内部的历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至今还能
看到那么多“伪先锋派”的原因。但是在
经历过那样一轮极端的形式创新之后,纯
粹的形式层面还有多大的潜力与空间?
而那曾经将文学从禁锢下解放出来的呼
吁,换了一个时代是否同样也会构成压抑
它的力量?今天文学的自说自话,其社会
效应的整体退败,是否应该回到这个层面
加以反思?第二重困难是,其实当然很多
作家,仍在关切着宏大的命题,但是这种
关切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是能动的,
还是惯性的?是富于创造力的,还是机械
重复的?新文学之初的那些知识分子们,
是带着真实的社会问题投入到对宏大命
题的思考,他们真的探索症结所在,他们
不断地创造世界观和解决方案,而今天我
们往往看到的却是陈旧观念的一再重复:
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巨变,社会结构如何
重构,对于历史的态度都仍立足于简单的
立场与逻辑。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写作
者的勤奋问题:所谓勤奋不仅意味着不断
写作,关键在于是否写出了有效的作品;
作家的勤奋不应该是在敲打键盘的体力
劳动层面,而更应是在精神层面,在思考
能力的层面和世界观的层面。不能不断
思考真问题,而重复老调子,我以为算不
上创作。这实际上已经涉及第二个层面,
即新世纪的作家们,如何体认自己的身份
与位置?
关于第二个层面,我想从创作的初衷
谈起。今天仍然可以读到不少前辈作家
的回忆,在溯及自己为什么踏上文学道路
时,他们会说是为了脱离农村劳动,为了
到文化馆工作,为了吃上国库粮……他们
还会强调文学是个手艺活儿,而自己是个
手艺人……这当然也是20世纪80年代文
学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个历史时期
是有重要意义的;而且我相信,也确实有
相当的真实性。但时至今日,依然不断重
复这样的“忆苦思甜”,就或多或少构成了
前辈们有意无意的“欺骗”,让不明就里的
年轻人上了当:也许最初开始创作,真的
是因为这样那样形而下的原因,但一个人
如果只是为了吃上白面馍馍而干文学这
个行当,何以能够坚持到现在?在今天物
欲横流的时代,这点动力完全不足以支撑
工作热情,这个事情说不通。因此前辈们
的这类自诉,其实更像是在一个侈谈理想
的时代羞涩地隐藏起了自己对于文学、对
于文化以及对于这个时代的激情,与胸中
“莫名的大志”,这是更年轻一辈从业者不
可不察的。回溯新文学之初,那时候所谓
职业文人的观念,还没有那么根深蒂固。
尽管如今已经有太多研究,探讨新旧交替
时代的现代报刊新闻业与职业知识分子
的生成,以及他们与新文学的发生之关
系。但那时的写作者职业化程度较之今
天是差得多了。我们也总是会提起鲁迅
对自己职业的不断选择,选择何种职业取
决于他内在的精神诉求与宏大理想。而
今天有多少从业者仅仅是将文学作为一
份职业呢?如今我们常常感慨难于看到
挑战阅读经验的作品与作者,这在某种程
度上是否也可以在从业者自身身份认定
的层面找到病因呢?正因为我们将自己
的工作视为专业分工下的某一职业,因此
我们很容易变得机械、僵硬、保守,不求有
功但求无过,追求既定规范内的精致完满
而不愿越雷池一步。最初我们或许是出
于得失考量而拒绝新鲜事物,但久而久之
那将成为一种下意识的审美趣味,一种难
以看到创新激情的审美趣味。
在前文对当下继续探索文本形式实
验的做法表达质疑之后,再来讨论第三
个层面的问题似乎有点矛盾。因此似乎
有必要再次强调,我所质疑的只是那些
缺乏难度拾人牙慧的实验,是那种无法
将文本的创新与内涵的深掘有机结合起
来的实验。而在诸多方面,对于文学新
的可能性的探索,当然始终是我们应该
予以不断关注的。这诸多方面,当然不
仅仅在于扭曲小说的机构,颠倒小说的
时空,复杂小说的叙述,而还应该包括
对文学组织机制、生产机制、流通机制
等方面的创新探索,包括在新技术条件
下新文体的生成与有效发展等问题。就
此而言,网络文学当然是应该放在这一
层面讨论的话题。这一借助新的传媒手
段而产生并在各个相关领域(或者说尤
其在相关领域)充满蓬勃活力的文学奇
观,看似新鲜;但是考虑到新文学的发
生与现代新闻出版之间的关系,我们会
发现这也不过是百年新文学系统之中的
老问题:无论我们从通俗文学的角度来
考量其文学特征,还是在文化研究的框
架下探讨其之于文学制度、社会组织的
有机作用,都不必大惊小怪。有趣的或
许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将这样一个似
新还旧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我们的认知
系统中,并找到一个办法,有效、健康和
更加富有活力地将之纳入到文学版图
中。今天我们已经过多地关注了网络文
学,但是似乎除了为资本提供 IP,还没
有其他可以看到的成效。尽管在资本运
作的层面,网络文学内部已经形成了新
的阶级差异、新的不公正与新的压抑,
但是在文学层面却依然混乱,依然莫衷
一是。将网络文学理解为某种超级通俗
文学大概是传统文学界最能接受的论述
方式——这在新文学之初,甚至之前都
同样曾经流行过。如今众所周知的是,
我们认作巨人的那些新文学主将,论当
时实际的读者数量,可能远不如同代的
通俗文学作家们。但即便像张恨水这样
销量巨大的所谓“鸳鸯蝴蝶派”作者,其
作品同样也展现民间疾苦,也涉及抗战
等严肃话题。但是今天的网络文学呢?
在纯粹的娱乐性之外,提供了多少坚实
的东西?“发迹变泰”是通俗文学的永恒
主题,自古就是通俗文学提供“爽度”的
无上法宝,在网络文学中亦复如是,只是
更像是电脑游戏中的“打怪升级”。但是
如何发迹变泰,为了什么要打怪升级,而
发迹变泰或打怪升级之后又做些什么?
这之间是有差别的。卖油郎独占花魁,
张扬的是小生产者的勤劳和对爱情的忠
贞专一,而如果缺乏这样的价值导向,只
剩下对于力量、权力、金钱的纯粹崇拜,
其中还会有基本的文化自觉吗?就此层
面而言,网络文学这个新世纪以来最大
的文学奇观,实在又很难放在百年新文
学视野中加以考量。而从评介、研究、引
导与组织的角度,是否也有可反思处?
是不加分辨地单纯按照粉丝、收入的排
行榜去团结网络作家,还是另立我们的
标准?我们有没有责任肯定某些网络文
学,而否定另外一些?大 IP就一定是好
的吗?在资本与掌声之外,我们有必要
盲目地跟风给他们再加冕一顶文学的桂
冠吗?这可能都是在新世纪的语境中,面
对新的文体变迁,文学从业者需要在百年
前巨人们的经验下去考量的问题。
前面谈过,新文学之初的知识分子们
至少在以上三个层面思考问题,但思考的
都是关于“新”与“旧”的问题。这是现代
性笼罩下不能逃脱的命题与思维方式,因
此百年新文学的视野,本质而言是现代性
的视野,是时间的视野。因而之所以回到
新文学之初去寻求资源来返观新世纪文
学,当然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将当前
的文学继续向前推进。不难发现,前此提
及的新世纪文学诸多问题,其实恰恰是百
年新文学发展过程当中所积存的。百年
新文学本身或许也已构成某种“旧”了。
所以关于“百年新文学视野中的新世纪文
学”这一主题,或许最好的结论是:对新世
纪文学而言,最好的情况就是不断走出百
年新文学的视野。
从新文学的起点返观新世纪文学
从新文学的起点返观新世纪文学
□□丛治辰
丛治辰
回望传统的文学实践回望传统的文学实践——对新世纪文学的一种观察 □郭冰茹
责任编辑:王 昉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2017年3月20日 星期一青年批评家
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辞:
郭冰茹的《赵树理的话本实践与“民族形式”探索》,讨论了现代小说文体变革与叙事传统
的关系,指出了赵树理创作中存在的主观动机上的积极性与话本文体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在
文学史脉落中探讨了“民族形式”的传承与转化问题。作者学风严谨,学术功底深厚,文章论述
恰切。有鉴于此,评委会决定授予其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辞:
丛治辰的《上海作为一种方法——论〈繁花〉》,论述
了长篇小说《繁花》构筑“纸上的上海”所具有的方法论
意义,分析了它作为一种方法,蕴含着如何理解记忆和
历史的多重可能性,其意义超越了一般的“作家论”。论
文见解独到,论述合理,才识俱佳。有鉴于此,评委会决
定授予其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大约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面对纷至
沓来的各种文学现象,文学研究显得有些手足无
措,批评家们一方面忙于给这些现象命名,或者
在一个已然熟悉的概念前冠以“新”字,比如“新
都市小说”、“新心理小说”,或者按照作家的年龄
来归类,比如“60年代出生作家群”、“文学新人
类”;一方面却也深深地怀疑这些命名的有效
性。的确,现在回头看那个热闹喧嚣的时代,那
些层出不穷的名称似乎并没有多少留存下来,而
对那个时代较为中肯的描述是“多元化”或者“无
名”。文学史的研究者不难发现,当代文学史,尤
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很难再像此前那
样,去除枝蔓,清理出一条清晰明朗的依照时代
主题或由重要文学现象串联起来的历史线索。
事实上,追踪新世纪,包括1990年代以来当代文
学的思想潮流和主题流变,越来越成为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那么我们该如何在文学史的框架中定
位这些文本,又该如何在文学史的视野中审视这
些文本呢?
现在比较通行的文学史写作往往关注文本
的反映对象(内容和形式),而忽略文本的反映方
式(文体),往往关注文本的主题流变,思潮更迭,
而忽略文体的发展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
我们将“新世纪”视为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非
对一个时期文学现象的总体概括,从文体层面进
入文学史,考察新世纪文学,尤其是小说,在文体
实验和文体革新方面做出的努力,那么我们便不
难将许多看似无关的文本联系起来,从而清理出
一条关于新世纪小说文体发展的线索,这条线索
与叙事传统,与本土叙事资源有关。
中国本土的叙事传统源远流长,它们广泛地
存在于史传、文赋、古典小说、民间曲艺等文艺形
态中,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同
时也彼此渗透融合。诚然,传统并非一成不变,
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继承,而过分强调“民族传统”
也很可能导致作家视野的僵化和封闭,正如早有
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
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有
可能变成“假命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也可
能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
陷阱。但是,我们同样不应忽略谈论“中国性”和
“中国文学传统”的前提,因为“中国”、“传统”这
些范畴正是在“西方”、“现代”的参照下提出的。
陈国球在论及中国文学传统时说:“当然,中国的
诗词歌赋或者骈体散行诸种篇什,以至志怪演
义、杂剧传奇等作品,本就纷陈于时间轨道之上;
集部之学,亦古已有之。然而,以诗歌、小说、戏
剧等崭新的门类重新组合排序,以‘文学’作为新
组合的统称,可说是现代的概念。亦只有在这个
‘现代’的视野下,与‘西方’并置相对的此一‘中
国’之意义才能生成。于是‘中国’的‘文学传统’
就在‘西方文学传统’的映照下得到体认,或者说
‘传统’才成为传统”。也就是说,正是在传统/现
代、新/旧、中国/西方这样的二元模式中,“传统”
才成为传统。具体到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则是
在与西方现代小说的对照中,借助叙事学理论,
从众多的传奇话本、章回说部中总结出的叙事特
征或叙事规律,比如:白描写实、外视点、全知叙
述、轮回的环形结构等等。当然这些叙事特征并
非中国古典小说所独有,但却是其最鲜明的表现
形式。
当代文学走到新世纪,一方面凸显出彼时文
学创作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当代作家的
文化和文体自觉。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被
西方汉学界视为“过时的西方模式衍生物”,当
代文学也不例外。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大多
是通过阅读和学习欧美文学成长起来的,对他
们来说,起作用,有意义的传统可能是卡夫卡、
乔伊斯、博尔赫斯、福克纳,他们所感受到的传
统压力可能来自19世纪现实主义,而中国古典
文学则是一个悬置着的、几乎感觉不到的存
在。当他们逐渐从对“西方”的模仿和依赖中走
出来,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言说方式时,认同危
机便不可避免。一个中国作家如何确定他们的
文学书写在世界文学中的身份?他们在北京写
作和在纽约写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与此相关的
是,实验性的文本写作在形式探索方面的路越
走越窄,意义的迷宫、叙事的圈套、语言的狂欢
不仅抛弃了读者,同时,这种总体上以形式和叙
事技巧为主要目标的倾向,在后来其局限性日
渐显露,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形式的疲惫。面对
此种困境,从中国传统文学中汲取滋养成为一条
退路/出路,或是一种选择。
格非是较早意识到应该从古典小说叙事传
统中汲取资源的先锋作家,虽然他的《人面桃花》
在2004年出版,但他注意到先锋文学、现代主义
所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清醒的反思却是从
1990年代开始的。在《小说的十字路口》中,他
这样描述20世纪小说创作中传统现实主义和现
代主义创作原则的消长与融合。他说:“传统现
实主义小说在经历了它空前繁荣的全盛期以后,
今天正面临新的蜕变的可能,一方面,由于它古
老的美学理想在读者心中积淀的审美情趣的永
久魅力,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在当今的文坛上仍保
持相当的活力;另一方面,它的某些创作原则(如
流水时序,全知角度的叙述、戏剧化的情节结构
等)已被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读者扬弃。本世纪初
崛起的以新小说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小说,在某种
程度上革新了小说的叙事方式,但时至今日,现
代主义小说所暴露的弊端(如晦涩艰深,难以卒
读,对小说传统的破坏导致的读者的陌生感等
等)也已日益明显”,而“当代小说极为重要的文
学现象之一”便是两者的融合。格非对这种文学
现象的概括针对的虽然是西方小说,但在某种程
度上也契合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状态。面对先
锋的文学实验越来越疏离读者,作为一位清醒的
理论家和自觉的文体革新者,格非从古典小说中
汲取资源,并将其与此前的先锋写作经验相结
合,从而尝试融合两者的写作实践。《人面桃花》
以及后续的《山河入梦》《春尽江南》都显现出对
这种融合的尝试。
《人面桃花》中有许多可以被视为古典小说
叙事特征的形式符号,比如白描式的写实手法、
诗词典故的化用、草蛇灰线的布局、文白杂糅的
语言风格等等,但同时《人面桃花》在叙事时间
上的中断、跳跃和拼接让这部小说又充满了现
代感。《山河入梦》则将白描手法与内心独白相
互穿插,外视点与内视点相互并置。《春尽江南》
不再拘泥古典小说的具体形式,而是将中国古
代轮回的时间观运用在叙事结构上,将古典小
说特别重视的“内在超越”作为“江南三部曲”的
精神追求,从而使小说文本在精神气韵上接近
古典小说传统。
格非认为中国古典小说是所谓“不离世间而
超越世间”,“世情”、“世事”和“人情”既是描述的
对象,也是超越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
忆的文学书写一直“不离世间”,也一直在努力
“超越世间”。在《启蒙时代》中,王安忆一方面巧
妙地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嵌入文本,
通过高中生们的阅读、清谈和辩论来肯定市民精
神;另一方面通过弄堂、操场、客厅来肯定市民生
活的恒常性。抽象的讨论与具象的写实互为表
里,相互映衬,使琐碎细腻的世俗书写有了理性
思辨的色彩。《天香》则是一部正面演绎市井活力
的作品。故事发生的“天香园”虽是一处江南贵
族的私家园林,内里却透着一股市井的蓬勃生
气。生活在里面的人们,不论怎样的事由,最终
都是热火朝天,赶集似的,总有着兴致勃勃的做
人的劲头,造园、设宴、裱画、唱曲、种花、养蚕、制
酱、刺绣、制墨,甚至在院子里模仿市井中人摆小
摊做买卖,仿佛什么都挡不住天香园里的好兴致
和一系列的异想天开。而在天香园里,物性人情
同时也是超越的对象,王安忆想要说明的是,市
井作为一方地理,既在野又在朝,它沟通了庙堂
和江湖,兼备了“王气”和“奇气”,这是“市井”之
于个体入世抑或出世的“上通下达”。因此,市井
的创造力不仅被表述为蓬勃的生机,更体现为贯
通连接生活和艺术、实用技艺与传统文化的理想
之链。
谈及“不离世间”,谈及文学书写的“世俗
性”,有一部小说便不得不提,就是金宇澄的《繁
花》。《繁花》通过各色物象的并置和罗列,拼接出
一个崇尚物质、多姿多彩的市民生活图景。与此
同时,与物象相伴的人情也透出种种物质性,人
与人之间的体恤互助与拆台使绊、义气温情与偷
窥乱伦、肝胆相照与隐瞒欺诈构成了《繁花》的
“世间”万象。与王安忆非常理性地把控人物、情
节、叙事节奏不同的是,《繁花》中的故事接故事,
故事套故事,牵牵连连、吵吵闹闹着涌向读者。
不同音高、音色、音质构成的各种“声音”从一个
瞬间到另一个瞬间,从一个平面到另一个平面,
流动在日常交往的各个场景中。在看似絮絮叨
叨、漫无目的的叙述中,作者记录了琐碎的生活
世相。此外,除了“不离世间”,《繁花》在叙事技
巧上也借鉴了苏州说书的方式,将传统话本“讲
故事”的绝活发挥到了极致。
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对中国古典小说叙
事传统的借鉴并不止于以上几个文本,苏童自
《妻妾成群》开始的“旧瓶装新酒”式的艺术探索,
贾平凹《废都》对明清世情小说的模仿,莫言的
《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对中国经验的
忠实,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对传奇小说的借
鉴,等等,都说明这种回溯传统的创作路径。当
然,如何创造性地转化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如
何扬古典小说写实之长,融现代小说之理性思辨
以描摹现实生活,并以此展现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仍然是当下的文学书写必须面对的问题。
丛治辰丛治辰
郭冰茹郭冰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