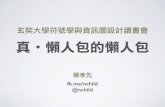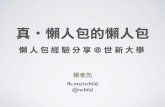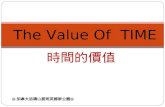落单的鸟儿孤身飞 但看到了归宿方向 -...
Transcript of 落单的鸟儿孤身飞 但看到了归宿方向 -...

2020年1月17日 星期五C4青影院
在去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以及今年的金球奖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的《别告诉她》,尽管没有获得新一届奥斯卡奖的任何提名,但比起其他探讨中美文化差异的电影,仍然具有一定的革新意义。
以往讲述中美文化冲突与华人身份认同的影片,李安的《推手》《喜宴》、许鞍华的《人在纽约》、王颖的《喜福会》等等,都是把纽约当作剧情衍变的舞台,华人在异乡的境遇变化与心态调整,一代或者二代移民的身份困惑与寻找,是以美国主流文化作为参照。可是华裔导演王子逸导演、编剧的《别告诉她》,却把故事放置在中国讲述,并且不是西方观众认知度较高的北京、上海,而是对他们宛如新大陆的长春。
地理坐标的变化,带出王子逸迥异于前辈导演的创作视角。《别告诉她》里,文化之间的冲撞与融合不再是重点,以回归目光看向人类赖以存在的情感基础成为核心。女主角碧莉一家,以及她的大伯一家分别从美国和日本飞回长春,假借参加碧莉堂弟浩浩婚礼的名义,与身患癌症晚期的奶奶见最后一面,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回家过年”。两种返乡之旅承载的心情虽然大相径庭,但为的都是在大家庭的氛围下重温亲情。
中国文化并不看重个人价值,个体需要按照集体或者团队的规则找寻人生路径。许多大龄单身人士“每逢春节被催婚”时,总会从父母亲戚口中听到“为了你好”,背后的潜台词往往是“你不能逾越常规”“你好,我才能好,才能让大家好”。但“大家”是个虚无的概念,指向集体无意识盲从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看似正被多元的网络文化消解,其实根深蒂固,原本与个体相关的大事小事,经常性地会以线上线下的方式,被迫与家庭、家族、邻里、社区等“攀上”关系。《别告诉她》中的奶奶便对回来结婚的孙子浩浩与日本女朋友只认识三个月耿耿于怀,担心邻居会指指点点而要求家人默认他们已经认识半年,其后又在家人的建议下,将半年延长至一年。
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虽然形式上接近消失,却仍在变相参与改造着我们的日常。个体即使来到推崇个性解放的国度,比如美国定居,也不意味着成功从环境的包围圈中突围,可以就此高枕无忧。《喜宴》中的纽约成功人士伟同,依旧要在父母,以及旧时长辈、同窗的监督之下,成为
“五千年性压抑”引发的形婚闹剧的主角。甚至,个体在灵魂焕然一新之后,以为已经扔掉的思维也会跟着在体内复苏。《喜福会》里的几位中国女性,人到美国后逐渐走出各自的苦难获得身心独立,可是在她们的女儿面前,又不自觉板起面孔扮成爱攀比、好面子的中国家长。
《别告诉她》中碧莉6岁便随父母去了美国,一家三口已在纽约生活25年,拿到美国国籍。在故乡长春的饭桌上,父亲海燕与亲戚争辩中美生活理念的差别,谈到他们一家已经算是美国人,带出他和妻子不会干预碧莉人生的言外之意,可是面对母亲的癌症晚期问题,他像个传统的中国人一样,顺从了小姨、大哥等合计的“不告诉她”,确保老人相信一大家人能在并非逢年过节的时间点团聚,的确是为了浩浩的婚礼。作为华裔二代的碧莉穿着鼻环,外在形象比她的众多美国朋友还要特别,充分彰显她的独立个性。可是对于父亲等人的举动,她经过无法理解的阶段后予以认同,甚至主动承担起隐瞒的重担。她习以为常的美国式知情权,终究败给了较为陌生的中国式家庭观。
不过这种“落败”,并不代表构成冲突的文化分出了高低。同样是在饭桌上,碧莉见母亲夸赞美国,忍不住反驳美国也有许多社会问题,然而对于中国,小到“美女”一词的含义,大到城市的拆建,她同样有许多疑惑。于是面对热情的宾馆服务生抛来的更爱中国还是美国的问题,她只能用“不一样”来回答。这个“不一样”,亦是王子逸对于两国文化的态度。《推手》《喜宴》中接连因为文化冲突导致的个体摩擦、家庭矛盾,在《别告诉她》里只是蜻蜓点水般的存在,一切都在为“善意的谎言”服务,带出的是国人从家庭内部向外层层扩展的情感。除了母子情、祖孙情,影片中还有姐妹情、老伴儿情,以及多年不变的友情。
碧莉的奶奶在两个儿子均不在身边、丈夫又去世的这些年,除了受到保姆的照顾,也一直被她的妹妹、后夫、侄女等人温情相待,并与他们感情深厚。后夫虽然耳朵不好使,总是遭她埋怨,但无论是她提醒他小心地滑,还是他为她端来洗脚水的笔触,都颇令人动容。妹妹出于照顾的方便,把家安在她家楼上,更是让人心头一暖。因此,她带着一大家人拜祭
亡夫时,请求丈夫的在天之灵保佑这个、庇护那个,并非情感的夸张外化而是自然流露。
只是,影片中的情感浓度,更像是王子逸对于中国社会昔日人情结构的回溯,接近《平原上的夏洛克》里几位农民兄弟的肝胆相照,却与当下的社会土壤并不匹配。浩浩婚礼上,奶奶与昔日战友的重逢叙旧,才是情义无价。如今飘荡在我们周边的,不过是人情社会的幽灵。正如《喜宴》中的父亲与部下在纽约的华人餐馆再见面,两人都是满脸兴奋,可是伟同在街上与老同学不期而遇后,只有一脸厌恶。
不过有意思的是,由这种沾染一定理想主义色彩的质朴人情,映出的中国社会面貌却具备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特征,既不是《喜福会》里有着秀美风光又充满磨难的过去时的古国,也与《摘金奇缘》中浮光掠影呈现的现代大都市景观相距甚远,更不同于国产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纪录扫描的城乡。碧莉奶奶居住的老小区、拔地而起的新高楼、让碧莉等人迷失方向的道路、与碧莉目光对视的风尘女子,以及婚宴间隙喘口气的服务人员等,共同塑就长春以及发展中的国家的模样。
中美文化差异让步于家族情感之外,《别告诉她》中与日本有关的设置更是紧紧围绕主题。回到前面提及的饭桌戏份,碧莉的大伯海滨谈到自己的身份,称无论在日本还是其他国家生活多久,他都是中国人。他的话看似是在嘲讽自称已是美国人的海燕,其实与婚宴上他流着眼泪对母亲“深情告白”一样,满满都是对母亲的愧疚与安抚。他没有办法做到“父母在不远游”,更加明白这次团聚的意味,只能用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而言,都显得有些激烈、与含蓄毫不沾边的言辞,让母亲接收到他的心意。而浩浩的女朋友能够始终面带微笑配合完成婚礼的表演,集体主义观念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加深入人心。
令人欣慰在于,根据王子逸的真实故事改编的《别告诉她》,片尾通过彩蛋告知观众,在她和家人精心包装的谎言之下,奶奶又多活了几年,侧写出电影中碧莉奶奶的命运。而碧莉与家人一道在长春与奶奶的短暂相处,也让她对自己的未来更加坚定。影片结尾碧莉在纽约清晨的街头,按照奶奶教给她的强身健体的方式发出两声吼叫,“震得”奶奶小区楼下一棵树上的鸟儿纷纷飞向天空,之前在纽约和长春莫名其妙飞进碧莉房间的那两只小鸟,也许还会继续孤单飞行,但至少像她一样,看见了归宿的方向。
编辑/史祎 美编/黎倩 责校/房霞
下载北京头条App让现在告诉未来
新近上映的《蕃薯浇米》是一部闽南色彩浓重,关系闽南文化的电影。年轻的导演叶谦是土生土长的福建人,作为服装设计师正当红,在设计方面也时常吸收故乡独特的文化元素与思路。创作首部剧情长片时,叶谦自然直接将镜头对准了故乡的风景与人情。
影片取景福建,讲述了两位乡间老人的“闺蜜”情谊与生死相隔后的个人价值追寻。主演颇压得住阵,分别是台湾的两位影后归亚蕾与杨贵媚。二人扭转口音重学当地方言,另外又费了不少功夫体验生活,才算接近了农妇的角色设定。归亚蕾所饰的寡妇林秀妹年过七旬,丈夫早逝,两个儿子也都成家立业在外拼闯。与儿媳妇带有距离的日常生活、无事操心也不被需要的孤单状态,便是故事的起点。而杨贵媚所饰的卖菜姐青娥的离去,则让林秀妹有了直面余下人生、探索更多可能性的想法。
片名“蕃薯浇米”对于同乡人来说定然是亲切异常的,稍作翻译,这便是最普通、清淡的家常饭食——红薯稀饭。“蕃薯浇米”是林秀妹性格与情感的标志,更是这部电影提供给目标观众的心灵把手,直接引向了对故土的思忆。但影片的总体风格与创作特征,却与稀饭恬淡中的细微滋味不大相配,反而是将乡野的朴实生活和民间的文化奇景进行了“乱炖”。观众爱不爱吃这口儿,就全赖于对食材本身是否眷恋了。
“内地首部闽南语对白院线电影”,这组锱铢必较的描述或首现于片方的通稿中,媒体又常将之压缩为“首部闽南语电影”,看似无差,却漏掉了必要条件。以闽南语为语言载体的方言电影,被概括为“厦语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可谓源远流长,依学者统计,至少有两百多部。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显踪”于大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更由香港、台湾传播、发扬光大于东南亚华人的视野中。
诞生于闽南文化中的《蕃薯浇米》,间隔大半个世纪,脉络仍可接续当年的前辈。最突出的几点可罗列于下:一是“妇女悲情”的题材情调;二是本地文化风俗的元素嫁接;三是传统乡村的原乡意识。片中,秀妹与追求者阿水师共赏的戏曲《陈三五娘》,便是早期“厦语片”多次改编的女性题材民俗经典。
“妇女悲情”之所以成为厦语片的重要特征,当地现实生活的男女差异情况当然是最大的原因。《蕃薯浇米》虽然聚焦闽南当下,但家庭框架的约束和封建观念的掣肘,仍然是剧中二位女性的苦恼来源。导演叶谦以当代视角改写了悲情人物的设定与处境,将传统的少女与新妇形象换为年逾七十的老年寡妇。林秀妹在家庭中的边缘之姿、老年恋遭遇的抵触,以及她仍需不断劳作于盐田、菜地之间的生活情境,与福建千百年来的女性形象异曲同工,不过又增添了老年关怀的次命题。而好友青娥的子女压力、婚内暴力,乃至秀妹儿媳妇所面对的六合彩风波和与丈夫的疏离,
都为这一题材主旨做了补充说明。《蕃薯浇米》试图以细节梳理这诸多的头绪,在窠臼中完成深度,却极难成功。悲情之悲不到,细节本身只构成了影片对地方上保守人际关系的照搬全收。
相比人物情感,《蕃薯浇米》编剧、导演思路上的核心考虑,更像是如何通过文化风俗元素的组合完成对原乡精神的重召。说得更直白些,就是怎样将那些具有闽南风味的关键元素拼盘,召唤观众的乡愁和对闽南文化的欣赏。影片场景方面展示了村舍、田野、盐场、海角的风光,在情节里串连起了各种民间信仰的元素,如舍公、妈祖、阿土师,还有民俗仪式如丧葬、敬神;大至曲艺表演、小至花色头巾,都在强调这锅“闽南乱炖”的特色风味。
这种风味显然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夸张的,正如秀妹与阿水师在三角梅边踩水车一场戏,带着鲜明的架空感和舞台感,人物间或唱起的民
谣,也同样带出一种半抽离的表演特征。从头到尾,影片面面俱到地拼凑着不同风味,也不忘引入一些与风味有违的元素。例如被台湾人承包的集中生产蔬菜的大棚,对秀妹态度冷淡、埋头电子游戏的大孙子,沉迷于六合彩的儿媳妇,以及夜间收看的天线宝宝节目等,就都作为“异化”的代表,被加入进来反衬秀妹温柔生活里的原乡含义。
当然,创作思路不宜作为孰优孰劣的衡量对象。对闽南的关注、对原乡的回望本身,已经是《蕃薯浇米》的特异所在。尽管其中包含的不是一种更具分量的回忆式的乡愁,而是一种概念化的想象的乡愁。但这种别样的乡愁,同样诞生于一些人的目光,也将真实共鸣于另一些人的心灵。所以,这部电影跻身于文化背景相对单调的流水线制作里,还是值得被它的目标观众所看到的。
可令人不吐不快的是,影片即使作为青年导演的初创之作,仍显得过于混乱和业余,视听设计放纵而毫无体系可言。《蕃薯浇米》作为电影艺术的创作,可以被直接判定为不合格。这并非是一部纯朴、笨拙的以“看”来关切拍摄对象的电影,而是有着鲜明的“做”的痕迹的,但导演的介入、制作的融合又显然是失败的。
在影片中,部分场景的调度或框取有着对艺术经典的模仿参照,但拍摄效果的控制、内在意义的填充则未能实现。以青娥偷菜的几段戏为例,杨贵媚仿佛回到蔡明亮的片场,独身一人在颇具形式感的灯火通明的大棚中,没有叙事信息量、未能引发凝视、也不曾提出造型意涵,只是对情节的“摆拍”。更不要提其他段落对阿彼察邦的致敬了,当真差之千里。
许多人也提出了职业演员与素人演员在本片中的兼容问题。归亚蕾与杨贵媚的勉力表演却无功而返确实是本片的最大遗憾。但遗憾之外,这点错漏实际上指向了一个更大更难却往往被低估的问题:什么是电影?什么是电影艺术?本片的未全之处提醒我们,艺术电影不是一种学科经验,更不是一种阶层资源。今天的艺术电影可能存在文化窠臼,但没有任何电影可以从文化窠臼里生发出来。也就是说,当你想把一个人、一个故事、一个地方拍成电影时,你应该先试着想想清楚,什么是电影。
落单的鸟儿孤身飞 但看到了归宿方向◎梅生
红薯稀饭怎么做成了“闽南乱炖”?◎浇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