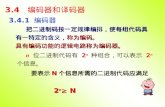编辑/于静 美编/周桂兰 责校/罗晶 -...
Transcript of 编辑/于静 美编/周桂兰 责校/罗晶 -...

2019年8月23日 星期五C4青舞台
继前年傅抱石、去年徐悲鸿之后,三峡博物馆今夏推出的著名画家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轮到了张大千。
看展前有两大疑问。与傅抱石“壬午个展”一战成名、“抱石皴”惊艳陪都,以及徐悲鸿长期任教中央大学艺术系并随迁重庆不同,张大千抗战时在重庆更少停留,长年隐居青城山,后期又赴敦煌临摹,要如何勾连起这位“五百年来第一人”与这座城市本身?今年是张大千百廿诞辰,这几年陆续有各种纪念展奉上,去年国博张大千艺术展有荣宝斋所藏巨幅金碧山水《华山云海图》压阵,今年保利春拍预展又是张大千泼彩名作《云山图》领衔,三峡博物馆这次展览又拿什么来招揽观众呢?
展览第二单元“东西南北之人:大千朋友圈”让人眼前一亮。张大千不到二十就出川东渡,学书、成名均是在沪上,辗转大江南北,晚年又远渡重洋,可谓朋友遍天下,这部分就是与人合作作品的集合。张大千与其兄“虎痴”张善子的《猛虎贯日》《红叶白猿》,“南张北溥”还有于非闇合作的《秋林高士》《芭蕉仕女》,都值得细品。比较稀罕的是一幅三峡博物馆自藏、张大千与谢玉岑合作的《山水人物图卷》。张大千评价“当代文人画家”唯有两个半,溥心畬、吴湖帆各算一个,半个是谢稚柳,这“两个半”的作品都是书画拍卖的常客,而剩下的半个就是谢稚柳早逝的胞兄谢玉岑。谢玉岑是张大千亲密知己,并称“谢诗张画”,可惜未及四十即病故,画名又为诗名、弟名所掩,作品比较少见,近年来偶有上拍。这幅图中秋树为谢所写,枯笔干墨,有倪云林之风,张大千配合所画高士也是瘦削笔法,正如题词所言,乃
“如一家眷属”。第三单元的“汲古为我:大千山水”,着
意在展示张大千的山水画成就,“师古人”的仿石涛、仿王蒙、仿弘仁,“师造化”的青城山写真、黄山写真都囊括其中,也可见张大千的“三千大千”,多面圣手。四川博物馆借展的《巫峡清秋图轴》,是本次展览中 编辑/于静 美编/周桂兰 责校/罗晶
下载北京头条App让现在告诉未来
◎水晶
两个小镇的﹃大﹄艺术节
在今年七月阿维尼翁艺术节和八月爱丁堡艺术节的间隙,我们没有像往常那样回
国,而是继续在欧洲游荡,先后去了法国的夏隆街头艺术节(C
halondans
larue
)和
英国的斯托克顿国际河岸艺术节(S
tocktonInte
rnationalR
iversid
eFestiva
l
),虽
然是两个小镇级城市,但艺术节的量级却很高,分别是法国和英国最大的户外艺术
节。两个城市迥然相异的气质,加上艺术节不同的运作方式,给人很多启发与思考。
◎解三酲
展览:三千大千——张大千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时间:2019.7.13-10.13地点: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张大千的龙门阵
《簪花图》
唯一一幅金碧山水,也曾在去年国博的主题展览上展出。在一片水墨、浅绛、青绿之中,泥金勾染的秋日巫峡分外夺目,瑰丽尽显无余,也是对本地盛景的描绘。
在第三单元展区中,还有几个展柜盛放着川博借展的印章,其中“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是张大千的一枚收藏章,曾经盖在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国宝《韩熙载夜宴图》上。抗战胜利之后张大千和张伯驹同为故宫博物院的鉴定委员,南京政府对于收购当时从伪满宫中散出的古画无心无力,二人变卖家产入藏了部分珍品,其中有这幅,也有张伯驹用李莲英的私邸换来的展子虔《游春图》。五十年代《游春图》等张伯驹收购的珍贵字画被他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差不多同时,《韩熙载夜宴图》也因张大千为迁居南美筹措川资托中人卖给了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再次聚首,这枚收藏章的美好愿景却成了虚话。十分凑巧,唐寅临的《韩熙载夜宴图》正是三峡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算上去年《千人千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古代人物画展》在内,一共就展出过三次,上一次展出还是十余年前,这次自然也是看不到的。
第四单元“清华旖旎:大千人物”是本次展览比较特殊的一个单元,其中展品当与第三单元山水画及第六单元“向古而生:敦煌朝圣”之后的人物画参看,可以看到张大千人物画从山水画中点景人物的高古出尘演变到敦煌临摹之后的雍容华美,将更偏重夫子自道的文人画法糅合到用色浓重、兼顾造型艺术的职业画家画法之中,开辟了人物画的一条新路。因为本次展览的时限为抗战时期,所以张大千晚年患目疾后泼墨泼彩的大写意画少有呈现,而这正是他衰年变法,于山水、花鸟尤其荷花上刻意不为工的精华所在,仅有两幅尚未如晚年一般脱落形骸的写意荷花,颇为遗憾,所以此次展品呈现人物画发展的清晰脉络就更为可贵。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幅水墨人物《为陈书舫写影图轴》,张大千作于1941年。
张大千与梨园行人士多有交好,京剧界的梅兰芳、程砚秋、余叔岩、俞振飞都曾与其过从甚密,作为四川人他也颇为欣赏川剧艺术,与名丑周企何是好友。陈书舫是川剧名旦,这幅小影却是写画其便装像,着墨不多,一个妙龄女郎呼之欲出。1952年底,陈书舫与周企何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合演的川剧折子戏《秋江》轰动一时,二人均获演员一等奖。次年,著名川籍学者、书法家谢无量在画上题词,“画史歌星两擅名,十年甜笔写倾城。收来倩影休论价,一曲秋江动上京”,正是记述这一段因缘。可惜二人合作的《秋江》并无录像存世,“文革”后已过盛年的陈书舫在峨影1979年摄制的《柳荫记·送行》、1984年《花田写扇》演出时况录像中留下了宝贵的演出资料,虽然年届花甲,舞台上仍然是娇憨动人。
此画绘成不久,张大千即奔赴敦煌,开启他两年多的临摹、发现之旅。1944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陪都“中央图书馆”举行,一时轰动、观者云集,第六单元“向古而生:敦煌朝圣”中部分展品当时即有展出。“中央图书馆”旧址距三峡博物馆也就三公里的路程,时隔四分之三世纪这些画作故地重游。
虽然此次展出中三峡博物馆自藏的书画约只占三分之一强,绝大部分展品也不是张大千在重庆创作,但仍然可以“旧友重相见,叙叙旧根由”。此时不由得期待一下明年同期的主题展览,也不知道会是抗战期间任教中央大学的黄君璧、任教国立艺专的潘天寿、寓居南岸的林风眠,还是1932年为四川军阀王瓒绪创作了与《唐临韩熙载夜宴图》同为三峡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四季山水十二条屏》的齐白石?
《猛虎贯日图》
《临五代水月观音图》
法国夏隆街头艺术节——外国艺术家集体“撂地卖艺”
法国夏隆街头艺术节的举办地在索恩河畔夏隆,位于法国中东部著名的红酒产区勃艮第大区,古镇依美丽的索恩河畔而建,有近2000年的历史。这个仅有不到五万人的小镇,在坐拥美丽风光的同时,也被列为法国艺术和历史名镇,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从1987年开始的夏隆街头艺术节。平时只有5万人不到的夏隆小镇,在艺术节期间会迎来欧洲各地近40万观众。他们的到来,令当地的餐饮、住宿和各种商业都受益。
7月24日至28日的艺术节期间,无论是走在古镇的主街,还是对岸的圣罗兰小岛,无处不在的各种演出都会吸引你放慢脚步,然后又被不远处的其他声音所吸引,赶往下一个节目。在这个艺术节,虽然有官方给出的一些演出时间表,但很难跟着时间表走,因为走着走着,就会被“计划外”的演出所吸引,而放弃本来打算要去看的那个演出了。
和阿维尼翁艺术节激烈的路演相比,夏隆街头艺术节的竞争性更强,因为阿维尼翁的“盈利模式”还是靠路演吸引观众买票进剧场看戏,而夏隆街头艺术节则基本上是“撂地”的盈利模式。除了艺术节In单元的邀请剧目外,绝大部分戏都是不请自来,演完之后,演员们就端着盆啊、碗啊什么的,来跟观众收“票钱”,观众自愿扔多少都行,跟北京当年的天桥差不多。
对此我真是感到万分诧异——天啊,那些演员怎么活啊?有些大的戏,加起来得有十多号人。像我们看的《进入平凡世界的旅程》(EKIVOKE),是一个带领观众在城市里行走的大型浸没式戏剧,有很多新马戏和形体表演的成分,以及制造观众参与和互动的悬念感,整个创作和执行,都需要相当的投入。演到最后,也是演员们端着大锅大盆上来收钱,但观众四散,往里扔的并不多。演员们好像也不太在乎,继续开开心心地游走在人群中。
今年艺术节的官方节目册里有161个剧目,几乎全部免费。我们在有限的时
间里,只看了重要的二十多个,既有路边划出块地方就开始演的,也有规模相当大的演出。有一个雨夜,《街道原则上不属于一个人》的10多位演员在贯穿几幢建筑物的房顶上穿梭,用钢丝、现场音乐、投影绘画等多种手段,与瓢泼大雨交相辉映,共同完成了这场难得一见的城市奇观。
在艺术节上也会碰到一些高科技作品,比如用VR增强现实技术呈现的作品《阿尔法循环》(#Alphaloop),就完全打破了我以往对VR作品的体验。这个作品不仅要求观众适应戴着VR眼镜爬梯、在街道上行走,有时还要在炫目的特效作用下旋转和跟随引导者奔跑,在现实与虚拟情境中不断快速切换,非常考验参与者的平衡感与身体控制能力,但也会体验到很特别的在虚拟世界里跳入跳出的感觉。
夏隆街头艺术节的观众也是一道风景,他们当中有许多经验丰富的“常客”,带着各种形态的折叠椅、小马扎,随时随地在演出场地旁边找到一个安逸的座位。夏隆多雨,观众们的雨具和防护措施也很齐全,一般的小雨、中雨,根本拦不住观众围观,更挡不住艺术家的激情,雨中演出是常态。
更有意思的是,在夏隆街头艺术节的观众群里,你会看到非常多的朋克,男女都有,各个年龄的都有,他们的小脏辫儿、纹身、各种奇特的饰物和身上仿佛能搓出泥来的衣服,都给这个城市增添了一种格外的“自由范儿”。
艺术家们放下架子的“撂地卖艺”,并没有减损他们的艺术水准,反而让他们与观众有种亲切感。而观众们自由自在的状态,轻松随意却又相互尊重,加上法国自身特有的松散气息,让整个夏隆街头艺术节有一种独特的波希米亚风。它会让你忘掉表演艺术通常的运行规则,让人们回到最简单的表达与分享、交流与回馈的朴素状态。
与吸引周边城市观众的夏隆街头艺术节相比,另一个在英国举办的历史相当的斯托克顿国际河岸艺术节则风格迥异。如果从地图上按城市标注字体大小来测算,蒂斯河畔斯托克顿(Stocktonon tees)大概得算英国的八线城市,虽然是北约克郡最大的人口聚居镇,但城市规模非常小。
作为“火柴的故乡”和1825年全世界第一个通铁路的小镇(斯托克顿-达林顿),斯托克顿在经历了工业化的衰退之后,现在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小镇。我们在刚刚到达这个城市时,就开始注意到这点,从火车站叫Uber到市区,只要三镑。街道上的人群,普遍有一种不太健康的面色和近乎褴褛的衣着,贫穷几乎写在脸上;在炸鱼和薯条店,很多家庭一家两口或三口,只点一份薯条;大市场里的廉价超市,物价比伦敦要低近一半……
即便是这样,这个小镇仍然骄傲地拥有一个已经有32年历史的英国最大的户外艺术节——斯托克顿国际河岸艺术节。艺术节的规模不算大,今年的剧目有44个,分散在8月1日至4日进行。但是演出相当集中,围绕着高街(High Street)的城市主线,演出此起彼伏,一个接一个。
由于艺术节的剧目全部由政府买单,民众得以在更放松的状态下自由观赏。这个艺术节真的是他们的“大日子”,十里八村的老乡们全来了,在喷泉水柱下嬉戏的男孩女孩和拄着拐杖坐着轮椅的老人,都在观众之列。艺术节有专门的委员会和艺术总监挑选剧目,并不因为这个小镇的贫穷就低看观众,不乏众多艺术性非常高的作品,有一部讲述年长女性与青年男性关系的舞蹈作品《抱住我》(Catch Me),非常雅致而含蓄,就在街头表演,观众们安安静静地看着,身边其他剧目热烈的喧闹声并不影响他们的专注。
来自西班牙的作品《Kamchatka》,8个拎着箱子的陌生人,来到这个语言不通、一切都让他们既惊又喜的地方,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探索、试探,讨要食物、摘取墨镜、共享雨伞、举起照片寻找自己的亲人……这个没有任何语言的作品,几乎全部表演都是即兴的,却激发了整个城市观众最大的热情,他们不依不饶地跟随着这8个异乡人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直到找到一辆愿意把8个人全部载走的小车,目
送他们而去。我看了两遍这个戏,每一次都热泪盈眶,每一次都感受到什么叫“天使在人间”。
艺术节也有一些委约作品,为小镇增添了独特的风景。在跨越两岸的无限大桥(Infinity Bridge)上,一组由舞者与歌者共同完成的作品在桥头呈现,观众们在风声与海鸥的叫声中,静静坐着,看远处的黑色身影由桥的深处缓缓走来,这场景非常电影感,又比电影更真实、更历历在目。
艺术节的闭幕演出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由悬臂大吊车和众多新马戏演员、歌剧演员、乐手共同在河岸边的天上地下表演,雨中的草坪上坐满了大人小孩。这个节目之后便是艺术节闭幕的盛大烟火晚会,我边看边在内心感慨:天呐,人家的小镇……
我问过艺术节的主办方,这个艺术节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吸引游客吗?可是看上去并不像有太多游客的样子啊。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个艺术节的英国户外艺术节平台(XTRAX)工作人员说,这个艺术节就是为当地人办的,正因为他们平时太缺少这方面的艺术活动,才需要提供这样一个艺术节。
之后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我看了英国导演罗伯特·英克(Robert Icke)与荷兰国际剧团合作的《俄狄浦斯》,非常喜欢,它把一个我一直理解不能的狗血剧情合理化、现代化到无以复加。罗伯特·英克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年轻导演,之前他导的《红谷仓》和《玛丽·斯图尔特》都是我的最爱,他年纪轻轻已经拿了奥利弗最佳导演奖、全英戏剧奖等非常多的重要奖项。
我在翻看节目册时,忽然发现一个有趣的巧合,罗伯特·英克的故乡和出生地,居然就是蒂斯河畔斯托克顿!他出生于1986年11月,在他不到一岁时,这个小镇就有了第一届斯托克顿国际河岸艺术节。在作为导演最初的起步阶段,他的作品也都是在斯托克顿的剧场里上演的。想必在罗伯特·英克成长的少年岁月里,他也像今天在喷泉里戏耍的那些孩子们一样,看了很多很多的户外表演,受到了某种启发。
也许,有些血脉和文化基因,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地写入个人命运和国家历史的。 摄影/水晶
斯托克顿国际河岸艺术节——政府送给“八线贫困小镇”的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