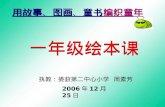儿童美术 - szlh.gov.cn教学特色:引导儿童观察、欣赏古今中外优秀艺术作品,在观察的过程中感知鲜活的 生命,体会色彩的变幻无穷。使儿童通过记忆、联想与想象创意表现出有创想性的作
童年记忆 夏天需要被听见 -...
Transcript of 童年记忆 夏天需要被听见 -...

浮生记慢时光
味蕾
夏天需要被听见□阑 珊
粽子里的流年□李红霞
童年记忆□潘自强
笔记
大师们的童年时光□艾兴君
儿童节的礼物□苗君甫
国画《歌声嘹亮》。 刘原 作
责任编辑:盛祥兰 美编:赵耀中 校对:韦驰 组版:李志芬
2019年6月2日 星期日06 闲情
片断
岁月留痕
老家一带,端午节没什么赛龙舟、喝雄黄酒之类的传统民俗,过得简朴而平淡。唯有包粽子,不知经历了几世春秋传承至今,感觉这端午就是粽子,粽子就是端午了。于是,一入五月,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端午,让每个日趋炎热的初夏时节,随处都飘溢着粽子的清香,将节日的美妙融入了每个人的心里。
儿时,生活水平还很差,根本没钱买苇叶,加上村里缺水,没有芦苇生长。因此,在芦苇发芽的时节,村里人就翻山越岭、起早贪黑地到邻村一处水塘,争抢着摘苇叶,直到整个水塘光秃一片、不再摇曳,才稍事停歇,等下一茬苇叶接上。但不管多累、多紧张,勤劳的农家人都会准备好充足的苇叶,只待端午到来。
当整个山村飘出苇叶的清香,这就是五月初三家家户户都在煮苇叶了。晾晒干枯的苇叶,经过几个小时的蒸煮,慢慢由淡绿变为暗黄,散发出粽子的香味。等整村妇女都端出自家的苇叶,围在老井旁洗整苇叶时,那场面真是既温馨快乐又热闹壮观。一桶桶杂乱的苇叶,在妇女们的
巧手中翻转腾飞,先是一片片洗净,捻出规整的扇面,然后麻利地在水中一抄、一甩、一弯,整齐地码在筐内;反复做着同一个动作,直到洗整完毕。其间,有打水嬉闹的、有斗嘴取乐的、有训斥孩子的、有闲扯唠嗑的,吵翻了整个村子。
五月初四一早,母亲就摆出了包粽子的阵式。苇叶、江米、菜豆、红枣、花生、藤条、筐子、剪刀等原料、工具,呈圆弧状次第摆开,母亲则坐在圆心位置,准备大显身手了。扯出四五片苇叶,折成漏斗状,装入江米、菜豆,埋入红枣、花生,将多余的苇叶折回;再扯三片苇叶,折出三个小漏斗,扣在其余三个角上,握紧;最后扯出剪好的藤条,从中间一缠、一系。一个光滑、可爱的四角小粽子就包好了。我也学着包,可不是漏了米,就是散了架,要么就是样子难看,总被母亲数落一顿,将我这毛愣小子赶到一边。等玩够了回家,只见满满一筐粽子已堆成了小山。
粽子下锅,架起大火,就等美餐了。这粽子可真难熟,足足煮了一下午,直搅得我坐立不安,心神不宁,一
会儿瞅瞅、一会儿看看,恨不得变个戏法,将整锅粽子瞬间催熟。无奈地等呀等呀,等到夕阳落山,鸡鸭归巢,等到整个村子都弥漫在粽子的浓香里。母亲一声吆喝,唤来了早已不耐烦的我。掀起锅盖,用筷子叉起一个,浸过凉水,小心翼翼地剥开。顿时,苇叶香、菜豆香、红枣香、花生香,融为一缕粽子香,沁入肠胃,大咽口水;继而稀溜稀溜地吃个精光。吃了第一个粽子,便跨入又一个端午。
曾经在乡下住校教了几年书,端午节经常回不了家,那粽子的香味便成了遥远的思念。幸好,有可爱的学生、有淳朴的乡亲,总是不忘在端午之前给我送来粽子。虽说吃不上母亲的粽子,可这“百家粽子”,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心中满满的都是幸福。因此,那几年异乡的端午,也便有了独特的值得铭记的浓情味道。
又到端午,又到粽子飘香时。三天假期,一定要回到农村老家,和母亲一起煮苇叶、包粽子、吃粽子,一家人一起品味那醇香的粽子。
出银川北门,东行十多里,便是爷爷家。爷爷的家坐落在一处寨子里,寨子有半
个足球场大。寨墙是用黄土一层一层夯起来的,有七八米高。当年寨子主要是为防范土匪所建,距今已有百年历史,周围的乡亲们管它叫潘家寨。
到爷爷这一辈,寨墙已坍塌,四周只留下三米多宽一人高的土台。
爷爷常穿中式开襟衣褂,戴瓜皮帽,留山羊胡。他会武功,一杆八尺白蜡棍舞起来,虎虎生风。年轻时,常带镖师护卫商贾,北下河套、南上平凉。
爷爷家是四间坐北向南的正房。还有五六间房分别住着二叔三叔及潘氏的其他后人,二十几口人住在一个寨子里还是热闹的。
这是个地脉兴旺的地方,盛产小麦玉米和各类蔬菜。夏天出寨门,抽穗的麦子在风的吹动下摇摆着,恰似海浪,一浪赶一浪,甚是壮观。
寨南一里处,有古庙,俗称高庙,后改为小学校。我在这里读书。学校不上课的时候,我就给生产队放驴。
寨子西边有一渠,名叫高渠,是蓄水用的。再向西行,便是西滩,中间有湖,水清澈得像明镜似的,蓝天尽在倒影中,游鱼在云中游,雄鹰在水里飞,那景象幽静而神秘。
西滩四周是浅滩,长满芦苇,是野鸭和一些不知名鸟类嬉戏的地方。靠边是一溜草滩,杂草繁茂,是驴儿撒欢的地方。
天麻亮,日头冒红,驴要出圈。为了防止驴出圈偷吃庄稼,六七个小伙伴骑上驴,拉开距离站在两边,扯着嗓子喊:“嗷——出圈啦!得球!”
那阵势极威武,像欢送出征将士似的。二十多头驴在呼喊中向西滩奔去。
到西滩,小伙伴们排为一线,把驴与庄稼地隔开,只要驴走向草滩,大家就可以放心地玩了。
我天天趴在黑驴背上,随着驴群奔跑。驴跑快了,有时会被颠下来的。刚开始,最难受的是过高渠。驴低头下渠坝,我会从驴前面滚下去。好不容易爬上驴背,它上渠坝,我又会从驴屁股滑下来,将我整得满头大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有小伙伴说:“告诉你个窍门,下渠坝时,双腿夹紧,身体向后仰,上渠坝时,身体向前靠,就掉不下去了!”按照这个窍门,我掉下去的次数少了。慢慢地熟练了,也会像其他伙伴那样吆喝着,挥舞鞭杆,追逐驴群。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不久,妈妈从银川回来了。她看到我晒黑的脸和满身被蚊子、牛虻和蚂蝗叮咬的疤,说:“你看看,你看看,字没识几个,倒学会当驴倌了?”在妈妈的心目中,读书才是最重要的,“转学吧,俺们进城!”
不久,我坐在老爸自行车的后面,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潘家寨。那年,我八岁。
后来,我又回去几次,每一次,都感受到家乡的变化。如今的潘家寨已完全认不得了,童年的高庙、高渠和西滩只能留在我的记忆里。
这几天,儿子开始追问我们准备送他什么礼物,准备怎样给他庆祝儿童节。
我一时有些无措,儿童节的礼物,我们都送过他变形金刚、一套《十万个为什么》、遥控赛车、漫画书……可是这么多的礼物,并不曾让他真正如获至宝,也不曾让他有我当年过儿童节的欣喜表情。
想起当年我们的儿童节,多么容易满足啊。一大早起床,穿上妈妈给准备好的新衣服,就觉得是天大的礼物了,如果平日里忙着耕种、忙着工作的父母,在儿童节那天表现出比平时稍多一点的细致、关心和疼爱,小小的心里就满满地被幸福和快乐充盈。
当时的儿童节,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最盛大的节日,有吃有喝,有玩有闹,学校里通常会举办联欢会。小小孩童,带着稚气未脱的表情,带着梦想,在舞台上跳舞或者唱歌,把学会的所有本领全在这一天表现出来,期盼得到一张小小的奖状。
那时候,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颁奖了,如果能在儿童节得到一张奖状,会觉得很荣耀,一路呼啸着跑回家,告诉父母这个好消息。至于学校发的瓜子、糖果之类的零食,更像是战利品一样,高高地举到父母的面前,像得胜回朝的将军。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奖状常会换来父母的一个奖赏——那就是可以去买一根冰激凌,还可以出去玩半天。
这已经是我得到的最好的儿童节礼物了,举着冰激凌招摇过市,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或者和伙伴们分享,你一口我一口地吃着属于我的奖品,心里很是满足。
也会和伙伴们满村庄乱窜,把快乐的笑声洒满乡间的每一个角落,那天村里的大人们通常是不会管的,那是属于我们的节日。迎面碰到的叔叔、伯伯、婶婶们都是带着慈爱的表情吩咐我们:
“跑慢点儿,注意安全……”我们头也不回地答应着,心里只想着玩乐,哪还会理会大人们的话呢。
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人近中年的这个儿童节,会回想起自己快乐的童年,会感到无比幸福。
所以,我看着儿子满怀期待的小脸,郑重其事地说:儿子,我希望我能送给你一份最珍贵的儿童节礼物,那就是永葆一颗童真的心。
我不知道儿子能不能听懂,但我希望,这是我们俩的约定。
这个夏天开始得有点累,开始从彻底的无所事事进入紧张的工作节奏,难免有点忙乱。当然也完全没有想要抱怨,早已习惯不管是如浮游生物般坠落到海底,还是细细粘贴修补生活,都随心而为顺其自然。人生这本说明书,总需要不同的修辞方式。
当然难免会有消极的情绪,有时是深夜暗涌的潮水,不挣扎就会被淹没。有时是明亮闹市突然降落的暴雨,不躲避就会被淋湿。有时是清晨厨房里一杯冷牛奶,你仰头喝了就好。喜乐悲伤,爱恨情仇,什么事沉溺太久,都没意思。
通宵写稿,结束时天已大亮,这种时候人会被拉扯成两种节奏,大脑还在活跃身体却已电量不足,无法直接入眠,便把厨房里所有常用的瓷器清洗一遍。那些不知不觉间累积起来的茶垢和污渍,像经年累月积下的疲惫。
然后听见知了的鸣叫与此起彼伏的蛙鸣,一波一波撞击耳膜,原来我与夏天只隔了一扇窗。
突然发现春天是用来看的,各种新绿花开五颜六色如调色盘,而夏天是用来被听见的。
比如蛙叫虫鸣。“这里”咖啡厅窗外有很多树,总有鸟躲在树阴里啼
鸣,是很难形容的悦耳之声。尤其是午后,层层叠叠的绿,一些细碎的阳光从叶间均匀地遗漏下来,落到一半便化作了满地的蝉鸣。绝对是消暑利器。
比如雨落。强风与大雨突如其来时,坐在窗前,听隆隆的雷声,雨滴敲打玻璃窗的声音,密得让你以为每分每秒都有星辰在坠落。这种时候会觉得,全世界最温暖的地方就是书桌旁的那盏灯光,角落暗沉如夜晚,在书页翻动的时间与空间的缝隙中,世界突然安静下来。
还比如海风潮汐。每年夏天都会去海岛,在海边看白种肤色的孩子嬉戏,大人懒洋洋晒太阳。喝酒,随手阅读一本书,看热烈的阳光一点一点变温柔,从树荫的间隙转移到手背上。远处是缓慢移动的船只,身边是很有参与感的海鸟,和潮汐的声音。
屏息一会,能听见思念,来自内心深处神秘低沉的回响。
还比如,在苏州遇见的芭蕉夜雨。住的客栈窗外刚好有一株芭蕉,在一片樱桃红枇杷黄的时候,开始抽出娇嫩的新叶。一开始是小小的卷曲,然后迅速舒展长大。一开始也没有过多留意,知道那晚的一场初夏夜雨,其他树叶都是沙沙沙沙,芭蕉却
是滴滴笃笃,而且会有小小回音。芭蕉似乎注定总得遇雨,光雨打
芭蕉这声音,就被写出了许多的诗句,做了许多文章。比如欧阳修会慨叹“深院锁黄昏,阵阵芭蕉雨”。李清照看到芭蕉树阴满中庭,会“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杨万里却写
“芭蕉得雨便欣然,终夜作声清更妍”,说芭蕉遇到雨,觉得很高兴,整夜的声响,都十分好听。小雨时,轻声细巧如飞蝇触到窗纸,雨大时如山泉跌落铿锵有力。
一丛绿意,有悲有喜。清代的蒋坦在他的《秋灯琐忆》
中说到此事:妻子秋芙所种的芭蕉,已经长大,可以遮蔽成荫。夜里雨水打上去,淅淅沥沥,让人感怀心伤。有一天他在叶子上题写了句子:“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
第二天见着叶面上有了妻子秋芙的续文:“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
其实悲喜都是人间的事,对芭蕉来说,只管张开它的大叶子,点点滴滴,都是惬意。
反正伴着一场芭蕉夜雨入睡,如果此时你问我是否相信幸福,我会肯定地回答你:相信。
□胡 弦
江水像一个苦行者。
而梅树上,一根湿润的枝条,
钟情于你臂弯勾画的阴影。
灰色山峦是更早的时辰。
花朵醒来。石兽的脖子仿佛
变长了,
伸进春天,索要水。
花 事
诗与画
一个朋友说,想吃螺蛳了。春光明媚,阳光能够薄薄地敷在我们的视线里,仿佛一切都是短促的。在清明之前,舌尖上微小的饕餮之火,一旦被提出就会轻轻燃起:它是一种感觉,好像耳鬓厮磨时的那种柔软和坚硬,舌尖对于螺蛳的身体充满着欲念。对于螺蛳而言,无论是否在狭窄的壳中做起了道场,此刻,在舌尖热情的拥抱中它完成了一场虚无的盛宴,那是我们对短暂春光的觊觎。
说到螺肉,我曾经什么也不加清水去煮,但似乎并不美味,可如果加上料酒和酱油,或者放上一小撮的盐末,它的味道几乎是一种人间清欢的至味。它的味道其实是通俗的,并不那么惊艳,但却在我们的生活中,勾勒出日常生活的景象:
我们也不过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里,腾挪、呼吸、出生,以及消逝。
我看到鱼吞下一枚螺蛳,又完整吐出,它无法咬碎螺蛳的盾,但我们可以,如果我黄粱一梦,化身为螺蛳,想必就是得过且过、小富即安的场景。
湖泊、池塘、水田和缓流的河溪中,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都可以看到螺蛳的影子,它和这些栖身之地大抵合而为一,低调到了可以忽视的地步,它是沉默的大多数,却并不深沉。
于它,这无非是生活的一种。记忆里,我总觉得应该有写螺蛳的诗,像热爱美食的苏东坡,但翻了一些资料,终究被一个现实所照亮 :它是沉默的,它的浮生不被记载。
而舌尖吮吸它时的愉悦是那么的真实,很多时候,我们记忆里的梦就这样被放下,然后从我们的指缝间飘走了。
螺蛳的美味□李郁葱
童年的时光,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每一次回首往事时,便会忆起童年。就是连那些大师级的人物,也有着天真无邪的童年记忆,他们的童年,也是直率纯真,不带有一点杂质。
鲁迅的童年苦多于乐,但他一直对穷苦人抱有同情心。鲁迅出生于一个地方望族,能够自由阅读一堆杂书。在夏天的夜晚,他能够躺在大桂树下的小饭桌上,有特别疼爱他的祖母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等等。在母亲有空闲的时候,还可以跟着她去农村的外婆家,因此,童年的鲁迅是可爱顽皮的。也可能正因为这样的童年,鲁迅一生都没有放弃对底层人民的热爱。
钱穆儿时记忆力极佳,每篇文字大约读过三遍就能背诵。他最爱看《三国演义》,9岁时便能背诵。钱父的一位朋友听说后,便当即考他“诸葛亮舌战群儒”一节,钱穆居然一字不落地当众背了出来,众人惊为神童。钱穆也沾沾自喜。第二日,他随父亲出门,经过一座桥时,父亲指着桥问他:“你认识‘桥’字吗?”钱穆答认识。父亲问:
“用木字易马字旁,是什么字?”答:“是‘骄’”。父亲接着说:“骄字何义,知道吗?”钱穆点头道:“知道。”到这时钱穆才知道父亲的真意,脸一下子红了。父亲的教诲,钱穆从此一直铭记在心,读书时绝对不能有骄傲的情绪。
傅斯年自幼聪颖。他读书极为用功,遇到不懂的字、词便记下来,随时向师长请教,有时找不到纸,便写在手上、胳膊乃至大腿、肚皮上。夏天一到,弄得浑身是墨迹。他在同窗中年纪最小,但比他大的同学都向他请教。同学中有写不出来作文的,便时常请他代笔,酬谢是一个烧饼。傅斯年常常写完自己的作业后,还能为同学写出几篇完全不同的文章来,但先生却知道肯定是傅斯年代写,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傅老大(傅斯年排行老大),你这次有没有换两个烧饼吃啊?”傅斯年听罢窘迫不堪。
沈从文儿时个子小,人很精瘦,非常机灵,滑稽有趣,常常逗得寨中老少捧腹大笑。沈从文爱逃学,常将书篮藏到土地庙里,然后在城里城外闲逛。逃学被发现后,沈从文总会被大哥责打,有时还要罚跪。跪着的时候,沈从文便想着外面的世界,“按照天气寒暖,想到河中鳜鱼被钓起离水以后拔刺的情形,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中啼鸣的黄鹂,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想着这些,他就忘了被处罚的痛苦,忘了时间,被叫起来之后,他也不觉得委屈。他说,他应该感谢这种处罚,给了他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
童年是最柔软的回忆,是每个人最丰饶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