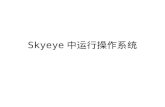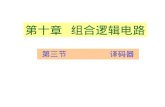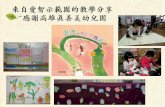DE-Nano Sales Training - · PDF file编译器 – Microsoft® Visual Studio编译器或者GCC
——《小王子》译后 再读普希金 -...
Transcript of ——《小王子》译后 再读普希金 -...

37责任编辑:王 杨 2017年2月13日 星期一外国文艺
[
[
刘云虹,南京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外国语
学院副院长,南京翻译家
协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翻
译与翻译研究,著有《翻
译批评研究》等,译有《小
王子》《娜侬》《塔吉尼亚
的小马》《我最美好的回
忆》《批评与临床》《知识
分子与法兰西激情》等。
天涯异草
为什么要重译《小王子》?这似乎是个绕
不过的问题,从动笔翻译开始,我心里就始终
在问自己。答案很明了:法国飞行员作家圣埃
克苏佩里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而他的《小
王子》——一个充满人生哲理的童话故事,不
仅深受全世界小读者的喜爱,也一次又一次感
动和迷住了我。答案也可以很简单:《小王子》
自问世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保持着广泛而
持久的阅读和接受,在中国也拥有数量众多的
译本,对于这样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学经
典,我渴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翻译版本,用
自己的声音再讲述一遍小王子的故事、讲述他
带给我们的人生思索。答案还可以更学术一
点:多年翻译理论的研究与翻译实践的感悟,
让我对翻译活动的创造性有了深刻认识。理
解与表达,这既是翻译过程中的两个核心环
节,也体现着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的双重创
造。可以说,每一次严肃的翻译都是对原作生
命的一次丰富与拓展。
虽然这些理由不能说不充分,也一定是真
诚的,但隐约间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我知道,
那是关乎心底里埋藏最深的记忆。人们总爱
用“缘分使然”来注解那些美好的邂逅,我和
《小王子》的相遇似乎也是冥冥中注定的一种
缘分。就像圣埃克苏佩里所说,“所有的大人
一开始都是孩子”,最初和小王子“建立联系”
的不是在翻译中或感动或沉思的我,而是20多
年前在南京外国语学校法语专业求学的懵懂
小姑娘。对我而言,能够成为“南外人”就是缘
分使然。当时,由于小升初考试前临时转学的
缘故,我在旧学校和新学校都没能获得报考南
外的推荐名额,于是,对南外的向往让妈妈和
我决定孤注一掷,我们带上各种奖状、证书和
期刊上发表的习作,鼓足勇气去南外毛遂自
荐。那天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日子之一,我们
一进南外校门就遇见了学校当时的教学处主
任(后来得知他就是一位法语老师)。一番自
荐之后,我们开心又激动地拿到了南外入学考
试的报名表。再以后,我顺利通过考试,幸运
地成为了南外法语专业的学生。
因为初中就开始学习法语的缘故,接触法
国小说和法语原著的时间都比较早,其中有两
部作品在我心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一部是
都德的《最后一课》,它让我对优美的法语多了
一份真诚而纯粹的热爱;另一部就是圣埃克苏
佩里的《小王子》,它让我在美丽的童话故事中
真切感受到人生中可能的欢喜悲愁,“责任”、
“忠诚”、“孤独”这些和“人生”一样意味深长、
一样充满神秘色彩的词语也牵动了少女的青
春思绪。其实,喜欢一本书或一个作家的理由
可以很简单,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初喜欢
萨冈、喜欢读她的作品,完全没有什么说得清
的原因,就是因为执著地迷上了“忧愁”这个
“美丽而庄重的”字眼儿。也许,语言就是这样
神奇,一词一语都可能充满魅力,甚至充满魔
力,让人无法抵抗。
对我来说,《小王子》不仅是青春记忆里弥
足珍贵的一部分,在后来的人生中,它就像一
位老朋友,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研究生毕业
后,我留在南京大学法语系任教,有机会在课
堂上和学生一起阅读和讨论文学经典。不知
是巧合,还是执著,或者真的有一种缘分,我在
阅读课上跟学生们讨论过的文本大都已经记
不得了,而都德的《磨坊书简》中很有意思的那
篇《塞甘先生的羊》和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
子》仍然清晰地留在记忆中。除了讲授语言的
运用、分享语言的魅力,我也在教学中和学生
一起揣摩作品蕴含的深意。如果说塞甘先生
的小羊让我感受到对自由的执著的渴望,那么
小王子让我体会到的则是爱、忠诚与责任的可
贵。再以后,翻译研究成为我在教学之外的另
一项工作,《小王子》的翻译作为文学经典复译
的典型代表,常常在文学作品经典化、翻译忠
实性和文学经典复译等关于翻译的重要问题
上带给我许多思考和启发。
无论是文学的体验,还是学术的思考,阅读
《小王子》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常读常新的感
觉。翻译《小王子》无疑是一次最深刻的阅读,
它带给我许多新的感悟。《小王子》在全世界拥
有数不清的读者,可以说,那个寻找朋友的孤独
男孩是每个人童年的影子,那个静谧中繁星闪
烁的夜空就是每个人心中的向往。而在我心
里,小王子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简单和快乐、关
于责任和幸福的故事。“本质的东西,眼睛是看
不见的。”“如果有个人爱上几百万几百万个星
球上惟一存在的一朵花,当他看这些星球时,他
就会感到无比幸福。”是的,“我的花就在那里”,
拥有幸福只需要这么一个简单而纯粹的理由就
足够了。对玫瑰花付出的时间让它成为小王子
心中的“独一无二”,这“独一无二”既是忠诚,更
是一种无法割舍的牵挂、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正
是这责任与牵挂让小王子决心踏上归途。离别
必然是沉重的,回归也必定经历痛苦,然而,小
王子义无反顾。幸福,不在于拥有五千朵玫瑰
花,而在于这世上有一朵玫瑰花,它藏在你的心
里,像灯光一样照亮你的心灵。我愿意相信,那
个找到了朋友、找到了归途的小王子,一定也找
到了一份简单的快乐、一份踏实的幸福。
从初次与《小王子》相遇至今,不经意间20
多年的时光已经匆匆逝去,我也从懵懂的小姑
娘变成了一位小姑娘的妈妈。回头望去,《小
王子》真的就像一位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时时
陪伴在身边,深深印刻在心里。我想,关于重
译《小王子》,那个隐约间无法言明的缘由,正
是关乎这样一种感觉。法国当代翻译家、翻译
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曾说过,翻译是“对原
文的一种馈赠”,对我而言,这种馈赠不仅寄托
着一份相识的情谊,也承载着一份对岁月和成
长的纪念。
最近为一台纪念普希金逝世 180 周年的诗歌音乐晚会撰写脚本,便又重读了普希金的两本传记,一本是列昂尼德·格罗斯曼的《普希金传》(王士燮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本是亨利·特罗亚的《普希金传》(张继双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列 昂 尼 德·格 罗 斯 曼(1888-1965)是苏联著名语文学家,他为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杰出人物传记丛书”撰写的这部《普希金传》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多次 再 版 。 亨 利·特 罗 亚(1911-2007)是法国著名作家,与茨威格和莫洛亚并称为“20 世纪世界三大传记作家”。特罗亚出身俄国化的亚美尼亚富商家庭,原名列夫·塔拉索夫,8岁时随全家流亡巴黎,后成为法国作家,曾获包括龚古尔奖、荣誉骑士、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等在内的多项殊荣,但俄国始终是他魂牵梦绕的文化记忆,俄国作家传记是他写作的重要构成之一,除普希金外,他还先后为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俄国作家作传。1945年,特罗亚偶然从在决斗中杀死普希金的法国人丹特斯的孙子手中得到两封普希金写给丹特斯义父盖克伦的信,这成了他写作《普希金传》的直接动机。
格罗斯曼和特罗亚的这两本书书名相同,写作年代也相距不远,格罗斯曼的《普希金传》1939 年初版,特罗亚的《普希金传》1946年初版;两书写法大同小异,均为对普希金由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的完整交代,对普希金文学创作活动的系统评介,甚至连书中引用的书信和资料、被当作分析对象的普希金作品引文等也大体相同。然而,两位《普希金传》作者,一位是苏联犹太裔学者,一位是法国俄裔作家,两人的生活经历和写作语境、作者个性和文字风格均有很大差异,这就使得两书在作者视点、叙事立场和叙述调性等方面体现出很大不同。就整体而言,格本是颂歌体的,是在神化一位诗人,在努力建构一个作为民族文化图腾的普希金形象;而特本则是故事体的,在人化一位诗神,在努力揭示一位神一样的人物的生活真实。前者以普希金自由思想的生发和成熟作为主要线索,追溯普希金作为自由战士和民族英雄的“战斗一生”,正如作者在《作者的话》中所说明的那样,他“对伟大诗人生平的叙述是以当时的政治事件和文学史为基础”,目的在于“有可能彻底发掘出伟大创作的这些源泉——诗人同人民的压迫者所进行的战斗,他为了争取自由、理智和缪斯的胜利所付出的巨大劳动”(第1页);后者则以普希金诗歌天赋的发展和表达为经纬,在普希金花天酒地的生活和严肃认真的创作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在普希金诗歌天才的发展史中发掘“故事性”,就像该书译者在《译者的话》中所写的那样:“在写作技巧上,《普希金传》摆脱了传记作品的刻板模式,写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有很强的可读性,简直如同一部写技高超的小说。”比如,格罗斯曼的《普希金传》为尊者讳,反复强调“普希金并不像他同时代人所描写的那样好追求女色”;特罗亚的《普希金传》则言:“他的一生就游荡在爱情和诗歌之间。更确切地说,对他来说,爱情和诗歌是同一种天才的不同表现形式……他的‘纯非洲式’的色欲叫人吃惊。”格本通过对《乡村》一诗的分析表明:“普希金是民族的伟大代言人,是准备同人民的压迫者进行决战的整个社会的深刻的人道思想的表达者。”特本却津津乐道于普希金的“双重人格”:“普希金有着双重人格,他一直就是如此。一方面他是个大顽童,贪恋女色和杯中物,喜欢击剑、赌博和写情书;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严肃的高产诗人。”“他在思想上是个成熟的男子汉,但在感情上却是个顽童。”格罗斯曼的《普希金传》在结尾写到普希金的葬礼上出现几个看热闹的农民:“他们仿佛是被不自由的人们派到被人杀害的诗人坟头的。正是人们用他们的传说丰富了诗人的创作,并且永远把普希金的名字藏入记忆里,以便把它带到遥远的但必定要来到的解放的时代。”特罗亚的《普希金传》在结尾则这样描写普希金的葬礼场景:“那里只剩下普希金一人,躺在黄土里。雪仍在下,风仍在吼。”很难说,这两种不同的叙述调性、不同的阐释线索究竟哪一种更合理,更吻合普希金的一生,但两者显然都是自成一家的,贯穿始终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服其读者。
奇怪的是,在读了这两本调性不同的《普希金传》后,我所获得的两个普希金形象却又是大同小异的,至少,这两个形象在我的心目中是相互重叠、相互补充的,并未构成矛盾。这或许因为,关于普希金的生平和创作,我已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再读普希金所获得的印象无法从根本上修正我业已形成的认识;但这或许更因为,任何一种关于普希金的阐释,说到底只不过是一个参照系,每个阅读普希金的人都应该获得一个自己的普希金,也就是茨维塔耶娃所言的“我的普希金”,其中既包含自己所采集的关于普希金的各种史实和观点,也应渗入自己的诗歌观和世界观,如此说来,任何一次对普希金的阅读,实际上也都是一次自我丰富的过程,就这一意义而言,对普希金的阅读应一直持续下去。读不尽的普希金,普希金读不尽,其实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精神世界的填充和拓展是永无止境的。
再读普希金
再读普希金
□□刘文飞
刘文飞
译介之旅
一湾心灵的泉水一湾心灵的泉水——《小王子》译后 □□刘云虹刘云虹
西山晨语
我曾浏览过罗马台伯河岸的夏夜书市,伴
着近旁流水与意大利红男绿女的轻歌曼舞,但
总觉得它不及塞纳河畔旧书摊特有的异趣。
几十年前我初到巴黎,立时被塞纳河边一
排排绿色木箱连环的旧书摊吸引。从右岸卢浮
宫码头启程,过圣路易岛的玛丽桥,再踱步到
左岸杜赫奈尔和伏尔泰两条沿河走道,全长约
4公里。对这一奇景,法国作家让·迪杜尔描
绘:“塞纳河是独一无二在两排由书籍筑成的
堤岸中淌着的水流”。“旧书商文化协会”主席
热罗姆·嘉莱也表示:“分列塞纳河两岸的长排
书籍有若两道江堤一般”。
确实,塞纳河畔是一处世间淘书宝地。有
心人甚至可以在此找到各类弥足珍贵的文学
典籍。譬如,笔者在贡蒂沿河道上曾见过套着
纸板书壳的19世纪原版《拜伦勋爵全集》,觅
到早年精装的查理·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
华》、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和热拉尔·纳荷华
的象征派文学杰作《火女》等等。历史类方面,
仅巴黎圣母院后边一处书摊就有将近400种
关于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书籍,林林总总,
各有其历史价值。自不用说其他封建王朝的编
年史,以及1791年9月3日颁布的《法国宪法》
的原版,标价150欧元。
杜赫奈尔沿河道35号对面的让-玛丽·卢
基耶书摊,被业内人士称作“孩童书苑”,有多
种“童子军”书籍,专供家长领子女光顾。至于
文化艺术类,则有在他处难以找到的木版、铜
版或石印绘画、音乐著作,尤其是法国野兽派
马蒂斯,印象派马奈、莫奈、米耶,以及马克·夏
加尔的画作和欧洲各国的艺苑撷英。
我最感兴趣的是人物传记,譬如路易丝·
米歇尔这位“红色圣女”,中国在晚清时代就介
绍过。《天义报》于1907年刊出“情僧”苏曼殊
在日本所撰奇文《露伊斯美索尔遗像》。曼殊法
师偶于故纸堆中得英国人祖梨手馈路易丝·米
歇尔肖像,感其“英姿活现”,叹曰:“极目尘球,
四生惨苦,谁能复起作大船师如美氏者耶?”
我碰巧淘到书纸已泛黄的《路易丝·米歇
尔坦荡一生》。诸多米歇尔传略中,这大概是最
早的孤本,得之真是喜出望外。更令人兴奋的
是,几年后我在圣米歇尔旧书丛里找到了一册
《第一国际会员及巴黎公社社员与卡尔·马克
思通讯集》,其中有一封俄罗斯女郎伊丽莎白·
德米特里耶娃于1871年 4月 24日自巴黎托
人往伦敦捎给马克思的秘密信札。信中谈及巴
黎公社面临凡尔赛分子准备发动总攻,急待伦
敦方面支援,而她自己则已决心战死在街垒
上。依据这一珍贵历史文献,我给《瞭望》杂志
写了报告文学《马克思的秘密使节》。继之,我
完成了长篇小说《夜空流星》。
由是观之,塞纳河堤岸的旧书摊不仅有供
外邦游人欣赏的异域风情,更是一泓汲取智慧
灵感的不竭源泉。塞纳河堤岸的旧书摊始于
16世纪,历史悠久,徽记为一
只蜥蜴注视利剑的图案。蜥蜴
标志旧书摊主追求阳光,利剑
象征他们酷爱自由。1789年法
国大革命没收大量封建贵族的
藏书,成了旧书商创业的契机,
到拿破仑时代得到巴黎当局认
可合法化,在伏尔泰沿河道和
新桥一带驻守发展起来。1891
年,摊主们获准将绿色书箱固
定在堤岸护墙上,夜间不需要
搬运回家。1900年世博会时旧
书摊达到200家,每家四个书
箱,占据十来米长的砌石栏杆,
摊主随意作息,只有雨天才自
行歇业。经营者自备书箱,无须
缴纳任何租金和税款。1930年
旧书经营真正趋于稳定,到
1991 年,塞纳河堤岸边千余
“绿箱”中的古旧书籍总数达30万册,规模空
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
产”,渥太华、东京等城市起而效仿。自2014年
起,这里开始举办“塞纳河堤岸书摊节”,届时
由50家书店联袂,竞相推出最佳古旧书刊给
读者,并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稀有书籍和手
迹沙龙”。
在塞纳河边设摊,须得向巴黎市政府提出
申请,申请人要具备足够的文化知识和从业特
长,历史清白,无犯罪前科。2010年,申请者逾
百家,但获准的仅23人。另外,市政府还规定,
每个摊位的长度最多不得超出8.6米,高不可
越出2.1米,以免妨碍塞纳河岸自然景观。
斗转星移,旧书摊经营队伍不断壮大,从
1606年在新桥起始的 24户,迄今已扩充至
250家。冬去春来,他们恪守传统,像哨兵一样
守护在旧书丛的岗位上。凡陈列于摊上的书
刊,均用透明塑料薄膜包裹,防止渍水,保障毛
毛雨天里也能照常营业。据老人们说,当年旧
书商冬日坚持守摊,都习惯在外衣里铺填好几
层报纸,那是最有效的御寒办法。
旧书摊主最珍视的是自由。热罗姆·嘉莱
表示:“我们有自己的工作时间表,按个人意愿
安排,不受任何拘束”。人们一般不知道,从传
统上看,塞纳河畔的旧书商群体始终抱有“无
政府”理念,蔑视主宰社会的权威,更不相信有
什么“救世主”,坚定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尊严。
这一特征,在旧书商出身的让-雅克·玛吉斯
处显示得尤为鲜明。我是上世纪70年代末跟
他在圣米歇尔喷泉结识的。让-雅克的父亲崇
尚自由,不甘受雇佣关系羁绊,选择到塞纳河
畔摆书摊,清平一生。老玛吉斯去世后,其孀妇
携子继续打理绿色书箱,让-雅克由此与书本
结下不解之缘。他向我表白:“我承继父业,选
择这行至今,是因为它自由”。正是为了法兰西
民族的自由,他在二战时参加了抵抗德国纳粹
法西斯的游击队。然而,巴黎解放后,他又回到
塞纳河的圣米歇尔堤岸,重新摆起旧书摊。
我深为他的品格所动,一直难忘二人的头
一回接触。那一年,我到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工
作,甫抵巴黎即去圣米歇尔堤岸找寻列昂·克
拉泰尔的小说《伊纳赫依》。这是一部描写巴黎
公社的作品,完稿于1887年。由于公社惨遭血
腥镇压,该书直到1931年才得以由法鲁瓦书
局印行面世,现今早已绝版。玛吉斯听闻一位
中国作家在苦寻此书,自己专门从旧书商联络
网中淘得,欣然将这本绝版珍籍免费赠送给我
这个素昧平生的异邦人,令我感动至极。他坦
诚地说:“我是个书商,但做买卖不是我生活的
理想”。
现今,游客每天在圣米歇尔旧书摊前川流
不息,但绝少会有人想到,老迈旧书商中间竟
有如让-雅克·玛吉斯这样怀抱理想的超凡智
者。他们以传播人类文化知识为天职,不屈服
金钱和权势,安于清贫,仅靠出售旧书所获的
微薄收入逸然度日。实际上,这些旧书摊主才
是“人类文化遗产”真正的优秀传人。
正基于此,他们对塞纳河堤岸文化目前面
临的“认同危机”感到忧虑。从20世纪末叶起,
旅游产品逐渐充斥巴黎的旧书摊
市场,形成塞纳河畔的雾霾,大有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当地市府
规定,每个摊位销售旅游纪念品
的比例不得超过25%。可是,按一
个摊位出售旧书可获100欧元计
算,如改卖旅游纪念品,其营业额
却可以翻上5倍,这对不重视书
籍价值的常人显然有着极大的诱
惑力。
针对近年出现的形势,巴黎
电视三台记者让-克洛德·伽利做
了一番现场调查,见证一些摊位
上堆满塑制艾菲尔铁塔、巴黎街
道牌和钥匙链等小玩意儿,令书
籍退位,几乎变为一种门面装饰。
这种现象,用汉娜·阿伦特的“大
众文化危机”之说,从供求推销术
审度,并不难理解。然而,接受记
者采访的旧书摊主却对之愤慨不已。50岁的
玛丽在塞纳河畔专营艺术类古旧书籍,已经有
20多年,她愤愤表示:“这是旅游纪念品入侵!
人们来此不再为买书。我大概在进行一场过时
的搏斗。”玛丽的同行让-米歇尔在梅吉斯里沿
河道也有15年从业经历。他声斥那些在堤岸廉
价贩卖伪劣旅游产品的经营者:“这些人怎能
算是书商,他们根本不懂书籍,十足的一伙盗
贼、流氓!”我的法国朋友让-雅克·玛吉斯则干
脆断言:“大众旅游简直成了一种污染!”
依笔者所观,这是一些不随流俗,似乎
“迂腐”的人。让-克洛德·伽利在结束其调查
后描述:“他们预感到巴黎天空的风云变幻。
阵雨过后,又一如既往,以惯常的坚定,打开
摊位的绿箱,从里面取出几分钟前避水保护
完善的古旧书籍和以往的时代版画,呈现于
世人眼前……”
塞纳河畔的堤岸文化塞纳河畔的堤岸文化□□沈大力沈大力
作者与玛吉斯夫妇一起参加作者与玛吉斯夫妇一起参加““兄弟宴会兄弟宴会””
坚持守摊的旧书商坚持守摊的旧书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