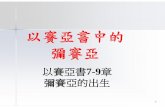“其争也君子” · 儒家所追求的是推行仁政与王道,“君子谋道不谋食”,虽掌握军事才能却并不 以此为生,也不愿被视为这一类的人才,便以“不知”为托辞。
2014 11 19paper.dz · 非的视民众为国家的耕战工具、君主的耳目...
Transcript of 2014 11 19paper.dz · 非的视民众为国家的耕战工具、君主的耳目...

2014年11月19日 星期三
热线电话:(0531)85193817 Email:[email protected] 9
□ 责任编辑 马清伟 王敏超
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法治”与“德治”思想,较完整地体现着兼容并蓄、综合创新的中国文化底蕴,其“中国特色”的本质可以追溯于先秦时期“儒法互补”的齐鲁文化,印证于“阳儒阴法”的中国社会治理传统,启发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进步。
建立在齐法家、鲁儒家基础
上的齐鲁文化,构成了秦汉之后
社会治理中的中国特色法治传统
早在汉代,贾谊就作过“商管”别论,将先秦法家分为“管仲晏婴”一系的“齐法家”和
“商韩李”一系的“三晋法家”。他说,管仲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是“知治体”的“法治”,与孔孟儒家后来提倡的“德礼之治”和
“王道仁政”颇多契合,与西方“法治”传统中的“自然法”(强调道德正义)与“实证法”(偏重条文强制)的融合,有许多相互借鉴说明之处。西方亚里士多德首创“法治”必为“良法之治”,与齐法家、鲁儒家的“德礼之治”并无本质区别。而“三晋法家”如慎到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以及韩非的视民众为国家的耕战工具、君主的耳目爪牙,则颇可类比古罗马查士丁尼的“凡君王满意的就是有效的法律”,其与中国儒家之
“德治”“仁政”社会治理思想相去者显如天壤。然而,齐法家“兼重礼法而顺应民心”,“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及“和而不同”、“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政任贤,其行爱民”等,与近邻鲁国孔子倡导的“仁爱”、“德政”、“贵和”,以及孟子所呼吁的“王道仁政”、“民贵君轻”等政治伦理,形成和谐无碍的互补,并成为秦汉之后中国社会治理“阳儒阴法”的思想特色。
建构在“儒法互补”基础上的齐鲁文化,不论其以“法治”、“礼治”、“人治”还是“德治”的形式出现,其在中国秦汉之后的社会治理中都体现为中国特色的“法治”传统。齐法家的“法治”思想,因为有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政治伦理性质为其砥砺和参照,而成为中国式的“良法之治”。其礼治中的“礼义廉耻”、人治中的“圣贤人格”,与西方传统法治中的“条文规范至上”、人治中的“君主个人意志至尊”正相反对。齐鲁文化中的“德治”是用道德规范引导条文规范,人治是用圣贤人格约束昏君霸主。这两点,孔子曾有经典的表述:一是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一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儒家政治伦理中的德政和德礼,是其“法治”思想中伦理基础和制度规范的统一,也就是孔子认为齐鲁社会应当以之治理的原则,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是也。因此,从“齐鲁文化”不仅可以解析出“儒道互补”的精神,而且可以解释中国社会治理的传统为何有
“法治”与“德治”并行不悖、相互增益的特色。反观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如果没有“自然法”对道德价值的偏重,则无法克服“实证法”的个人专断,希特勒的《重建公务员队伍法》和南非的《种族隔离法》都是因为没有道德的约束,而使法律沦为“恶法”,成为破坏民主和
侵害人权的工具,导致“法的非法”悖论,一如中国“三晋法家”身受其祸的“为法之弊”———商鞅作法自毙,韩非死于秦政下的冤狱,秦政则速亡于仁义不施、刻薄寡恩的“繁密法网”之中。以致汉初仅以“约法三章”加以纠谬,成为齐法家“礼治”和鲁儒家“德治”的反向论证案例。
以齐鲁文化的精神而论,“德治”“法治”必然是兼容而互补的,其道理早已为贾谊所阐明:“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这倒不是说“刑罚”没有任何意义,只是说它不能代表社会理想的价值取向。法令有“驱民”的功效,是教民的必要底线,但它必须以“德治”的价值理性为取向,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只有“善”、
“法”并举,德治与法治互相补充、兼容并蓄,才能实现孟子所劝告的,治理社会者“与民同乐”、“得道多助”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
“齐”是“制度典范”,“鲁”是
“思想典范”;前者以“管仲晏婴”为
代表,后者以“孔子孟子”为代表
自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尽管有些历史片断表现为社会动荡、民族分裂和国家的积贫积弱,但从人类社会的大格局看,基本上是统一、稳定和持续发展壮大的,故而有“希腊罗马有古无今”、“英美法德有今无古”、“中华天下亘古亘今”之通议,冯友兰先生常以《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标而出之,以其政治伦理为“天命靡常,唯德是辅”。具体讲就是:中国社会的持续生命力正涵养于其“天下为公”的政治道德之中。西方人称其近代文明得益于“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其潜台词是借鉴古典“希腊的思想和罗马的制度”,以为近代英国“工业革命”,美国、法国“社会革命”,以及德国“思想革命”的精神资源和制度基础,从而赋予其文明传统中的法治、人治、民主、理性、共和、民族、政教分离等思想和制度观念以新的时代意义。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法维新、当代社会的改革开放以及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也都逻辑地蕴含着中国特色的
精神资源和制度基础,这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兼蓄道法名墨兵农商”的诸子百家,和汉唐盛世以来的“天下制度”。前者是中华文明中“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精神资源,后者是
“协和万邦”的制度基础。如果我们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进步化约为对“希腊罗马”的继承创新,那么,我们亦可将改革开放以来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实践,化约为对齐鲁文化的继承创新。因为“齐”是中华文明传统中的“制度典范”,即“齐法家”指导下形成的持续性制度;而“鲁”则是中华文明传统中的“思想典范”,即“鲁儒家”指导下形成的持续性思想。前者以“管仲晏婴”为代表,后者以“孔子孟子”为代表。
齐鲁文化中齐在“法治”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之所以具有典范意义,是因为管晏法治思想中蕴含着鲁儒家的“德治”思想的某些重要因素,成为中国社会治理传统中“阳儒阴法”、“明儒暗法”或“德法共治”的重要内涵。而其富国强兵形成的霸主地位,贯穿于“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两个阶段,居“五霸”之先,殿“七雄”之后,是五百余年春秋战国历史中最稳定的诸侯国,虽最终灭于强秦,然强秦的帝国国祚不过十四年,之后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汉承秦制”则并非形式上的“秦制”,而是以尊贤尚功、尊王攘夷、“尚武、尚仁、尚侈”的“齐制”因素居多。因为齐、秦各为春秋战国时代东西方两大诸侯强国,齐之“恒强”与秦之“暴亡”形成鲜明对比,故而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也正是从“齐制”和“秦制”的政治伦理角度,对“恒强”与“暴亡”所做的制度性质方面的总结。
显然,如果“汉承秦制”不从制度的政治伦理——— 仁义方面总结,则难以解释汉唐盛世何以成为中华社会治理历久弥新的典范,而秦政暴虐与隋政骄淫何以成为“霸道暴政”、“强横必亡”的政治宿命。因此,中国社会治理中的“汉唐盛世”也可以说是具有“儒法互补”性质的齐鲁文化的政治现象,其意义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所总括者:“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
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不过,我对陈先生的总括还要做点修正,即真正进入中国汉晋法律体系、至《唐律疏议》蔚为大观的,应该是齐鲁文化中的“齐法家”与“鲁儒家”的交互融合,而非形式上的荀卿李斯之师门嫡传。
“德法”分则两败、合则两利,
中国两千多年的相对稳定,就是
建构在儒家价值理想与法家工具
效能之间的平衡上的
回顾现代世界较为成熟的法治体系,“法治”是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也就是高尚的道德理想和基本的治理规则的结合,其中道德理想是永恒的目标,治理规则是追求理想目标的有效工具。就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而言,这种辩证关系在齐鲁文化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思想基础,尽管中国历代统治者个性意志差别巨大,有中兴之主,有亡国之君,但其社会治理成败无不受制于齐鲁文化所揭示的法治德治关系的影响,“德法”分则两败、合则两利。宋代的才子苏东坡曾有诗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就是强调法律在治国养民中的底线作用,这是法治的确定性和功效之所在。但此底线毕竟只备有工具和技巧的意义,它不能自然养成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这是“德治”和“政治人格”的象征,无此,则会大大消解法律规则的社会功效,中国人说“法不责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就是通俗的印证。反过来讲,法治所蕴含的辩证关系也明显地显露在诸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或“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之类的俗语中。其中“天”代表了儒家神圣的价值理想,“法网”代表了法家的工具效能,“天”在“法”之上,是其神圣性和合法性的根据,它们的结合与互补是由它们的“入世”哲学所决定的,因此也逻辑地说明了,中国两千多年相对稳定的制度,是建构在儒家的价值理想和法家的工具效能之间的平衡上的。
过去,由于只是孤立地看待“汉承秦制”、“独尊儒术”、“批儒评法”这些历史表象,似乎儒法完全是对立的。而依赖一个片面的价值理想或法制方略,就能维系一个庞大政治体系垂二千余年而不溃,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根据的。合乎历史和逻辑的解释是,价值理想和法制方略相互补充、统一的“法治”,才能维系社会体制的平衡发展。中国社会治理中比较稳定的“阳儒阴法”传统,以及作为其思想基础的“齐鲁文化”就是明证。就中国制度的传统而言,这种平衡发展就体现在儒法互补方面。它的历史轨迹是,春秋的“齐法家”是“正”,战国的“三晋法家”是“反”,“苛暴秦政”是“反”之极,汉律和“独尊儒术”是“和”。所以,区别春秋时期的“齐法家”和战国时期的“三晋法家”是为了解释暴秦与汉承秦制、独尊儒术之间的矛盾。而发扬“德法合治”传统所体现的社会治理层面的“中国特色”,对于理解“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建立现代化法治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是不乏深意的。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齐鲁文化与中国特色的法治□ 单 纯
当下有一种倾向,即不少艺术家
在享用市场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又把
创作中的问题推给市场。
事实上,文艺与市场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老问题、大问题、难问题。
文艺与市场的问题,其核心是文艺创作与市场的问题,这已成为当下文艺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其背景就是文艺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并且发展迅速。去年全国电影票房达200多亿元,今年预计300亿元左右;艺术品市场的总成交额去年已达4000亿元,工艺品交易达1 . 2亿元;再加上网络消费、教育、新闻出版等文艺市场及其产业链条上的营收,预计文艺市场及其延伸链条上的市场规模,保守估计已达几万亿元的规模。另外,随着我国人均GDP的增长,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已进入快速转型期。到去年年底,我国人均GDP已达8700多美元,预计到2020年,人均GDP将超过1 . 27万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与此相对应,文艺及其作品的消费需求也会迅猛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如此巨大且增长迅速的文艺市场,如果文艺界及文艺学的研究忽视、忽略了这一板块、这一领域,那将是新形势下文艺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大缺憾。
当然,文艺与市场问题被引起广泛关注与重视,还有一个关键事实,那就是市场已成为评价文艺活动与作品的一个重要力量,
很多时候甚至被误当做一个主导性的力量。人们往往把那些市场收益大、消费价格高的作品视为价值高的作品,由此出现了一些价格决定价值的片面现象;而一些思想性、艺术价值比较高的文艺作品,由于缺乏相应的市场运作与消费的引导,市场收益差、消费价格低,反而社会效应与评价都不高。这些“扭曲”现象的存在,其实是在反复提醒我们,一定要正确、全面地处理文艺与市场的关系。
首先要面对现实,承认市场的建构力量已介入文艺评价与文艺价值建构过程中的事实。我们不要主观上排斥市场,市场也是我国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话来说就是:“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这集中阐释了在当代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参与到艺术价值评价过程与建构过程中的基本现实与迫切要求。其次,我们要花大力气去研究、分析、引导文艺市场,以前不熟悉、不擅长的领域,我们一定要通过学习、研究、实践去把握,只有认识了市场,弄清了其发展的规律,我们才能将其作为建构我国文艺发展的有生力量,而不是视其为规则与规范的破坏者,人为地远离与排斥。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文艺需要批评,文艺市场更需要批评。最后,我们要重视文艺与市场关系的研究,通过研究,把握市场建构力量介入文艺评价与文艺价值建构
的态势、互动机制、发展规律与路径等,为文艺与市场共生生态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理论与政策支撑。
在文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或是乱象,特别是文艺市场领域,原因虽然很多,但有不少是我们对文艺与市场的关系研究不够、了解不深,特别是对其内在的机制与规律研究学习缺失所造成的。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一些问题进行一下厘清。
首先,不要把市场与创作对立。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市场对文艺创作的巨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克服市场有可能带给创作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当下,我们尤其要注意一个倾向,即不少艺术家,在享用市场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又把创作中的问题推给市场。所以,文艺创作界要勇于在创作本身找问题,文艺管理部门要多从管理的理念、体制与方法上找问题,特别是在创作能力、质量水平及文化精神的追求等诸方面,做建设性的行动与反思。
其次,市场从来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文艺市场也不例外。文艺市场首先是由人民大众构成的市场,市场需求也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文艺及精神需求。我们要特别警惕把市场与人民大众对立,把人民大众排斥在市场之外的思维;特别是不要把满足人民大众多层次、多样态的文艺与精神需求,与市场的健康需求相对立。我们知道,市场中最为核心的是“供”“求”关系,在很多时
候,健康需求的建立与培育,离不了丰富多样的正能量文艺作品的有效供给,这种供给就是一种最好的引导手段。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要把人民大众、民间文艺创作队伍及其作品排斥在文艺创作或是文艺市场之外,在我看来,他们更接地气、传播面更广,影响更大,更应成为文艺创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更应成为文艺作品的重要供给方。
再次,不要把市场机制与市场化混为一谈。市场机制的核心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自由、公平竞争的机制,其本质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或是社会工具,而市场化虽然是以市场机制的发挥为基础,但它的目标却是市场利益最大化。这种本质性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在文艺创作、市场的管理上强调市场机制,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其市场化。
最后,文艺市场繁荣是文艺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持久发展繁荣的动力之一。文艺市场的混乱是对文艺的最大伤害,但对于混乱的原因,我们要客观、系统地分析创作与市场两个方面的原因,做到实事求是。同时,我们还应继续重视市场,积极探索国家意志、文艺导向与市场机制的有效融合、整合问题,这也是新时期文艺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作者系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文艺与市场不能简单“对立化”□ 西 沐
每个曾经被挖或出走的教授,都是有故事的
人。
1929年夏天,时任职南开的何廉对于身边同事纷纷跳槽深感伤心,不禁惋惜道:“许多工作多年的关键的教师,包括萧遽、蒋廷黻、萧公权和李继侗一起离开南开去清华了,这对教学工作和学校的名声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高校间人才循环流动,学者们自谋发展天地,本是再自然不过之事。然虽皆是另攀新枝,每位教授之隐衷又各不相同,甚或尚有一把辛酸泪存其心中。故针对境遇迥异之教授,高校挖人手段可谓花样迭出。
不妨还是从何廉的二位同事蒋廷黻与萧公权讲起。蒋氏29岁赴南开任教,六年内发表的诸如《现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观》《统一方法的讨论》等论文,在学界反响颇大,实属冉冉升起之明星。当时罗家伦执掌清华,准备打造一支文科航母与北大相颉颃。所谓“航母”,无非广揽名角,形成规模优势,而带头人则显得愈发重要。放眼国内,罗氏认定年仅35岁的蒋廷黻独堪此任。于是其亲赴南开挖墙脚,来到蒋宅,劝其改投清华。蒋本来在南开干得好好的,不想离开天津。无奈罗施展软磨硬泡的功夫,“赖功”一流,坐着不走,整整熬了一夜。蒋廷黻终究拗不过罗家伦,答应赴清华任教。后来,罗更是不惜开罪德高望重的中国史大家、章门高足、自己的恩师朱希祖,将系主任一职让与初来乍到的蒋廷黻。对于此事,罗后来回忆道:“纵然得罪了我的老师,但是我为了历史系的前途,也不能不为公义而牺牲私情了。”可见罗对蒋的期望之高。蒋亦不负罗之重托,在人才延揽方面费尽心思,罗织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学者,使清华历史系成为海内第一流的学系。据其同事陈之迈统计,当蒋于1935年离开清华时,历史系的阵容是:中国通史及古代史为雷海宗,隋唐史为陈寅恪,元史为姚从吾及邵循正,明史为吴晗,清史为萧一山,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为蒋廷黻,西洋史为刘寿民及张贵永,日本史为王信忠,俄国史为葛邦福(Michael Gapanovitch)。即使在今人眼中,此阵容也堪称梦幻级别了。
若蒋廷黻算被罗家伦“生拉硬拽”到清华的话,那么萧公权调任东北大学则属于“两厢情愿”型。初来南开,萧氏颇感惬意,享读书快乐之余,还深受友朋之乐。他与蒋廷黻、何廉、李继侗、姜立夫等同仁将学校百树村十号房改造成教员俱乐部。每到晚饭后,大家随意去那里喝咖啡,谈天,或作各种游艺,藉以稍纾一天工作的疲劳。娱乐一个小时左右,众人尽兴而返,“回家去继续作研究工作,或加紧预备教材”。孰料佳期如梦,好景不长,不及三年,矛盾接踵而至。先是教学任务过大,“一位教授负责的教学包括四门、每周三个学时的不同课程,每周总共12节课。要胜任这么重的教学任务,备课工作是极其繁重的”。这势必分散学者的科研精力。接着学校在加薪事件上略有不公,令部分教授心寒,其中萧之堂兄萧叔玉负气北走清华,这让其也萌生退意。恰好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高惜冰受文法两院之托来天津延聘教授,萧就在挖人名单之列,且萧也有到关外走走之意,于是二者一拍即合。只是东北大学亦有其自身的问题,最严重的便是高校衙门化,官气甚浓。一次,萧打算找院长商议公事,一名职员居然说:“拿名片来!”待萧将名片递给他,一看上面只印着姓名,并无显赫的头衔,这名职员便把名片往桌上一扔,口中甩出四个字:“院长不见!”普通职员对待堂堂大学教授竟毫无敬意,颐指气使。此情形,在当下的某些院校中是否亦似曾相识呢?萧氏自然受不了这股子官老爷做派,一年后便应燕京大学之邀,去北平发展。
萧氏在东北期间,曾遇到一段趣事。当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同在那里教书。东北大学的名誉校长乃少帅张学良。张见到林徽因这位女教授,顿时倾倒不已,嘱咐手下向她致意,并请其做家庭教师。二人本就是属于两个不同世界,奉系“少帅”自然非民国“女神”的菜,林婉辞谢绝。等到学期结束,林立即同丈夫离开东北,被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挖走。这也算是“退避三舍”型了吧?
高校聘教授,自然是为了教书育人,繁荣学术。但高校亦是江湖,派系林立,纷争不已,故有时领导挖人又难免带有几分平衡校内势力的考虑。民国学人朱希祖身不由己的遭遇即是显例。民初北大桐城派把持一时,为彻底打击此势力,北大校长何燏时从教育部将朱希祖挖来。其后朱利用同门情谊,陆续将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诸人聘至北大,章门弟子齐聚首,将桐城诸老之影响一扫而空。只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有风骚三五年,五四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人渐成规模,至上世纪30年代已呈取章门而代之势头。此时朱希祖之处境便异常尴尬。1930年底,北大史学系学生出现要求朱辞职的风潮。迫于无奈,朱只得请辞。落魄失意之际,朱曾经的学生、时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负责人傅斯年伸出援手,力邀其加盟史语所担任专任研究员。不过傅尚有一条件,即朱必须完全与北大脱离关系。然朱对北大仍有感情,于是保留一个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之虚衔。即使如此,傅却不依不饶,声称朱未践前诺,将其转为特约研究员。这相当于宣布朱希祖并非史语所正式人员。而此际,朱一没有在北大复职,二没有再去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兼职,三也未收到史语所正式聘书,真真正正在北平下岗了。其实傅将朱挖过来之本意,在于彻底肃清太炎弟子在北大文科之势力。又怎能容忍朱同北大还留有一丝联系?直到1932年10月,朱不得不接受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聘请,南下广州任教授。至此,朱方走出学术低谷。
其实,对于高校而言,人才流动实属平常,但落到个人身上,却往往不平常,其间的缘由并非皆足与人道。是故,每个曾经被挖或出走的教授,都是有故事的人呐!
高校如何挖教授□ 王学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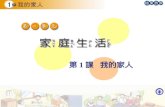



![[ 我 家 養 的 兔 子 ]](https://static.fdocument.pub/doc/165x107/56814d6c550346895dbab780/-56814d6c550346895dbab78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