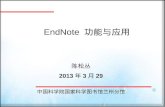陈家琪-中
-
Upload
wenyuan-shao -
Category
Documents
-
view
228 -
download
1
description
Transcript of 陈家琪-中

�年五月号 书城·二 一一 ·
封面用图:《小景》[英]斯潘塞
 版权声明:所有图文版权均属本刊所有,未经本刊书面允许不得转载,
本刊保留一切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主办单位: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
协办单位: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出版社
编辑出版:《书城》杂志社
编委会成员
以上按姓氏笔画为序,带*者为执行编委
编委会主任
陈启甸 黄育海
名誉主编:余秋雨
主 编:黄 韬
执行主编:黄育海
责任编辑:齐晓鸽
陶媛媛
美术编辑:高静芳
发行部
电话:021-54960808-210 203
传真:021-54963899
国内统一刊号:CN31-1662/G2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5-5541
广告经营许可证:3101034000017
印刷: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国内发行:上海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邮发代号:4-516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公司(北京339信箱)
零售价:人民币12元
出版日期:每月5日
吴 彬
陆 灏
高希均
王安忆
余 华
范景中
彭 伦*
王晓明
陈子善*
郝明义
葛兆光
苏 童
陈平原
贺圣遂
褚钰泉*
李庆西*
陈思和
骆玉明
蔡 翔*
吴晓波
陈 斌
钱理群
戴 燕*
从西天到中土(中)
陈家琪
我这人读书、写书评有两大改不了的习惯,
一是要么不写,要写就专写那些我觉得“好”
的方面,或者把本没有那么“好”的东西也按
自己的理解“写得更好了一些”,总之立足于自
身的切身感受与价值取向,偏向于在“同情的
理解”中看待对方;于是也就很可能只看见了
自己想看见的东西。现在,我确实已经很少能
写出批判、反驳、揭露的文章了,这大约与自
己在“文革”中写了太多这方面的文章有关,
也可能和自己业已麻木了的心灵有关;二是总
要摆出一副做学问的样子,喜欢引述别人(特
别是大家)的话来说自己想说的话,要是找不
到别人类似的话,自己就宁肯不说,于是大量
时间就都耗费在寻找所谓的“引证”上。
这一节涉及三位印度学者,我所关注的主
题是政治与文化的关系。
三、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在中国学界,杜赞奇也许是这八位印度
学者中最为我们所了解的一位,因为在此之前,
他的一些著作或文章就已经译成了中文,而且
所讨论的也大都是中国问题,我这里就有他
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的中译本,经他
之口,我们国家权力的“内卷化”特征(state
involution)一时间竟成为了许多人的口头语,
《南方人物周刊》上似乎也有过对他的专访。
在他的《读本》中,我最关注的是《中国
与印度现代性的批评者》一文,关注他对甘地、
尼赫鲁与毛泽东的比较,当然同时也就更为注
意到了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这几位人物的
命运(学说与行径),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在
另外一种环境下,上述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甘地
的角色。”(第 100页)
首先一个问题,亚洲几个主要国家都对来
自西方世界的现代性持有疑虑,而且又都在疑
虑中迈出了各自不同的现代性步伐。对印度来
说,完全无法接受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用后
面将要讨论到的阿希斯·南迪的话来说,印度
作为多民族国家存在了三百五十多年,“只要
民族国家的体系继续存在,这项世界纪录就
不可能被打破”,但“印度的后殖民时期国家
的直接表现形式是一种现代的自由民主政体”
(查特吉,第 121页),他们正是在此基础上反
抗西方的现代性的;也正是这种体制使任何形
杜赞奇(PrasenjitDuara)

BOOK TOWN�
BO
OK
TO
WN
�年五月号 书城·二 一一 ·
式的(思想)反抗都成为可能,而且一定会开
花结果。
对日本来说,他们的神圣信仰、彼岸信仰
就建立在日本天皇的世系与血缘上,而且天皇
的“神性”与“绝对性”绝非任何“神祇”(无
论是耶稣、穆罕默德还是释迦牟尼)所能取
代,遑论人间神圣,因为天皇本来也就不过
问人间俗世(尽管二战最后日本的投降书要出
自天皇之口才真正算数);与此相关,在日本,
既然有了象征日本政治权力高度统一的天皇,
那么“废藩置县”(铲除幕府势力)与“走向共
和”就成了日本维持这种表面统一的可能取
向。这看起来与中国秦统一后的“封建”、“郡
县”之争类似,但有两点与我们不同:一是日
本由于始终未能采用唐朝以来的科举制,所以
也就始终保留着政治贵族(有自己的庄园和守
护庄园的卫队,即后来的武士,享有苗字权和
佩刀权,即有姓有名,一般的人则只有名而无
姓,这就涉及到了某种具有特权性质的法权
观念是如何深入人心的,对印度的种姓制度也
应作如是观;当然,天皇本身则为法权外最大
的政治贵族)的身份地位,而这些政治贵族
之间的权力制衡不仅需要天皇作为他们一致认
可的公共代表(类似于某种契约论授权),而
且似乎也只能采取某种共和的形式才能维持
住政治贵族间利益的平衡。可见实力强大的贵
族集团实为限制王权或皇权独大的必要前提。
二是在统一基础上的扩张。樱雪丸在其所著的
《日本明治维新》(凤凰出版社 2010 年版)中
就写到:日本人那时就是相信实用主义,在西
方走了一圈,从英到法再到德,终于找到了知
音,“会晤结束时,俾斯麦一把抓过岩仓具的手,
很深情的地说道:‘你我两国都尚且处在黎明,
让我们共同努力,迎接属于我们的太阳吧!’
据说大久保和伊藤两人就差在下面高呼
日德友谊万岁口号了。”(参见该书第 247 页)
日本与德国一拍即合,从杜赞奇的角度
来看,显然交织着文化与政治的共同需要:早
在赫尔德那里,就强调民族性格的多样性,企
图用“文化”的观念来抵制进化论意义上的英
法美“文明”;到黑格尔,如果“文化”可以等
同于历史,那么德国就可以找到一条既与英法
美的“文明”不同,但同时又能接受进化论的
另一种形态的现代性,—请高度注意“另一
种形态的现代性”这一说法,马克思的学说即
为一典型代表。
就如“民主”对印度来说,只是一种的“后
殖民的遗产”一样,日本的“共和”也不是向
西方学习的结果,而是出于自身的无奈(天皇
与政治贵族二元化的权力结构);然后再用武
力和征服来对抗西方的现代性,这其实就是为
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日本明治维新。日本入侵中
国时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其实就代表着
他们对建设西方之外的“另一种形态的现代性”
的社会政治理想。
这种现代性显然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
的,不但在当时为日本与德国所需要,而且也
可能为其他亚非拉“强调文化多样性的国家”
提供另一种思维模式。
其次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现代性是所
有亚洲国家(比如中、日、印)都不拒绝的一
个目标,分歧或差异只在实现的途径或方式
上,那么这其实就已预先接受了西方的线性历
史观(与“进步”这一概念密不可分的历史目
的论或历史决定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认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
一部线性的历史,就不可能成其为国家;而德
里达则告诉我们西方形而上学的第一原则就体
现为这样一种线性的历史观,而如何处理历史
中事实与逻辑的关系,历史与翻译、再现、本
质、书写等一系列问题又是印度学者所最热衷
于讨论的问题。
杜赞奇认为中国存在着两种形态的保守
主义,一种是以章炳麟、刘师培为代表的“文
化理想守护派”,他们认为应该把政治与文化
区分开来,守护文化就是守护价值,他们并不
反对现代性,不反对政治改革与富国强兵,只
是认为就我们民族与个人生活的理想而言,仅
有这些显然不够,东方文化自有它高出于西方
文化的独特价值;后来的梁启超就成为这一派
的最大代表。另一种形态的保守主义则认为
政治与文化不能分,也分不开,我们不仅要在
文化上,而且要在整个社会的管制机构上维护
自身的统一性,比如在康有为、梁漱溟等人看
来,儒家学说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化观念,它
涉及到西方的科学、历史、理性都无法作出评
判的真理领域。按这一派的思路走下去,儒家
学说就相当于中国人的宗教,它与人的心灵有
关,如果再和佛学结合起来,所要回答的就
是全人类的平等、博爱等方面的问题,而不仅
仅只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无论是康有为还是
梁漱溟,都接受过进化论,所以也就都相信
有进步,但这种“进步”并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
而是每一个都在不同境遇下关注着同样的问
题。我看梁漱溟写于上世纪初的《印度哲学概
论》,一开始在“绪论”中就说“印度土沃气暖,
谷米易熟。其民不必劳于治生,辄乃心游于远,
故兮富于哲学思想。……其思想之自由,尽慧
悟之能事,辩难证诘,妙穷理致,古今各国罕
有其盛者。”所以在这些人眼中,如果谈文化,
文化就是精神,精神就是心灵,心灵就是安顿,
安顿就是一体,这与西方的个人主义、自我意
识、自由竞争显然格格不入。
但政治呢?我们总不能忘了我们生活于其
中的政治生活。所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
都想用传统的乡约、民俗来重建社会,就如日
本明治维新时日新馆的“校训”就是“不可为
者则不可为”,而当时的私塾(寺子屋)里所
用教材也几乎全是《庭训往来》、《商卖往来》
之类,体现着从孔孟思想那里来的尊老爱幼、
尊师重教(包括不说谎、不做假、不欺小、不
违约等人伦常识,而这些常识在今日日本所起
的作用已让我们惊叹不已);中国的留学生当
时到日本参观,感喟中国“民智未开”,其实
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丧失或割裂了自身传
统的思想教育资源。
《杜赞奇读本》
[美]杜赞奇著
“从西天到中土:印度新思潮读本”丛书之一
丛书主编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等
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BOOK TOWN�
BO
OK
TO
WN
�年五月号 书城·二 一一 ·
总之保守主义更重视的是人类生活,生
活中的情绪、信仰、怀疑、神秘主义这些非理
性的因素,于是就牵扯到传统、习俗的合理性,
而且必须思考这些合理性中文化与政治因素所
具有的特殊意义。
杜赞奇以印度十九世纪思想家查托帕伊
(Bankin Chandra Chattopadhyay,1834-1894)为
例,说明他并不反对改革,“但是,他认为,变
革应以即将从民族文化或他更愿称之为民族宗
教的复兴中诞生的新的道德共识为标准。因此,
就像对梁漱溟来说一样,政治与文化从来也不
可能真正分离:宗教与道德的远见必将贯穿在
希冀实现的理想社会的图景之中。”(第 80页)
具体到甘地、尼赫鲁、毛泽东这三个人,
杜赞奇认为甘地反对政治与文化的分裂,他
攻击的是西方的整个文明,认为这种文明会使
人成为奢侈欲望与贪图享乐的俘虏;他既然
反对生产力的解放与生产工具的改进对人类社
会所具有的意义,当然也就反对与之相适应的
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巨大变革(这是马克思
的理论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原理)。他的心
目中其实就只有一个自给自足的乡村乌托邦的
社会理想,他自己称之为“自治公社”或“王
道乐土”。在甘地心目中,统治者的高尚、家
长制的和谐、种姓化的组织形式、互惠而又
无竞争的社会系统,加上超越性的宗教权威,
足以对西方社会的政治与文化构成足够强大
的挑战。
毛泽东也反对政治与文化的分离。杜赞
奇说,毛泽东与甘地一样,“两人都在寻找不
同的社群形式,寻求其解放理想中所包含的可
替代竞争型社会的模式,尤其是可替代市场经
济的模式。尽管毛泽东坚持经济发展的观念,
但他们对于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封闭的公
社的共同关注,对于城市占据主导位置的厌恶,
对于技术专家的不信任、对天然自治的社区较
之于代议制—无论是政党还是议会—优越
性的重视,都确认将政治从属于共同体道德,
以及将道德的真实性与政治融合在一起”(第
84-85 页)的必要与可能。
这里出现的毛泽东已经与我们(特别是我
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毛泽东有了很大的不同。
我们想象不出如果甘地手中握有了巨大到可以
翻天覆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
政治权力他会怎样,但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并不
满足于“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封闭的公社”,
他要实现世界革命,不是抵制西方世界的政治、
经济与文化,而是要超过、要打败他们;所以
要实现的目标也就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目
的论,而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历史目的论,
所以他也并不想恢复中国的传统道德,而是要
造就新人,一种具有无限忠诚和献身精神的、
不怕苦、不怕死,以苦为乐、以死为荣的“新
人”;而这一切又并不建立在甘地式的宗教的
超验基础之上,而是通过不停顿的社会运动,
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使人既无暇也不
敢、更无法顾及“自我”(除了不间断地斗私批修,
狠斗私字一闪念外)的“新人”。这是一种充满
动态的、从而也就无法凝固的社会共同体形式。
如何认识毛泽东这个人,仅就这一话题来说,
在我们国家还很陌生,但杜赞奇通过对毛泽东
与甘地反对将文化与政治分离开来而进行的比
较,还是促使我们在理论上(注意:仅仅是在
理论上)想到了更多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
命的问题;就对毛泽东的政治理想与社会实践
的重新认识而言,如何从理论上(先要把毛泽
东视为一个具有远大政治 -文化理想的政治
家)看待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无
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问题。
尼赫鲁是主张文化与政治的分离的,这一
点与二十世纪初印度的极端派(通过政治煽动
立即实现独立)与稳健派(通过渐进的宪政方
式从英国人手里获得独立)之争的背景有关。
要尼赫鲁还是要甘地?要尼赫鲁就意味着要西
方化了的现代性(也就是今天的全球化)之远
景,要启蒙,要一种类似于中国式的从“强敌
入侵”到“五四运动”的线性叙事。杜赞奇说,
但尼赫鲁从未走到过“五四运动”那样与传统
决裂的地步。尼赫鲁相信进化论,也就相信生
物性的生长、发育、成熟、衰老,所以他认为
印度文化既然有过辉煌,也就势必会有衰落。
这套想法在逻辑上又会导致两个结论:一是
相比于西方世界的发达,印度文化现在是不
是处于衰落期之中?造成这种衰落的原因是什
么?二是需不需要启蒙?启蒙的主题不应该是
单纯歌颂自身文化曾有过的辉煌(阿 Q :“我们
的先前,比你阔的多了,你算是什么东西?”),
而是着眼于政治,宪政改革与独立诉求,在此
过程中要把政治与文化分离开来,“而且相对
于启蒙历史而言,文化居于次要的地位”(第
82 页),就如民族文化可以作为时代的最高理
想长期蕴藏于人们心中,一旦有了适宜的土壤
就会蓬勃而出一样。这又让我想起了黑格尔的
那句名言:“密纳发的猫头鹰,要到黄昏到来
才起飞”。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一下:在马克思那
里,历史是一个具有客观性的、自动展开着
的必然过程;在毛泽东那里,加上了人的意
志,个人对历史的创造性,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认为这可能会使毛泽东背离历史目
的论,而将其改变为人心的目的论,于是“人”
也就很可能成为了“仁”,道德共同体也就取
代了经济共同体。毛泽东与甘地的不同,在于
他既不反对启蒙,也不反对现代性,他的道德
共同体更不具有任何超验性;毛泽东与尼赫鲁
的不同,在于他既不赞成渐进的、宪政的民族
独立形式,更反对他把政治与文化割裂开来,
因为文化在毛泽东这里已经具有了意识形态的
巨大功能,但又不是“仁”,而是社会结构的
不断变革,因为他相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说到这里,杜赞奇引用了林毓生先生的
一段论述来解释辛亥前后的中国:如果中国的
文化、道德、以及更广泛的社会领域都靠政
治制度来获得合法性,如果道德秩序与政治
秩序是整合为一的,那么政治秩序的崩溃就
可能导致道德秩序的崩溃,并进而使得对传统
秩序的全盘否定成为可能。于是,我们必须重
新思考政治秩序与文化或道德秩序的关系。
要尼赫鲁还是要甘地?杜赞奇把这个问题
提给了我们中国人。
阿希斯·南迪(AshisNandy)

BOOK TOWN10
BO
OK
TO
WN
11年五月号 书城·二 一一 ·
四、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
泰戈尔首先称甘地为“圣雄”(Gandi
Mahatma),杜赞奇这样问道:“到底是什么使
甘地这样的人物及其思想能够在印度社会和历
史中占据最为重要的位置?”(杜赞奇,第 86 页)
南迪在他的《最后的相遇:甘地遇刺之
政治》中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南迪的《读本》中,首先吸引我的一个
概念就是“低幼化”(infantilization),这个概
念可以和康德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叫
启蒙》中所提出的“不成熟状态”(immaturity)
相互加以印证;康德所要强调的是那种“自己
强加于自己”(self-incurred)或自己认为自己
的 “不成熟”;南迪所说的“低幼化”指一种
普遍化了的社会现象:你如果对某种社会现
象不认可或表示惊讶、不可思议,那就说明你
还很幼稚,很不成熟。康德的意思是:所谓启蒙,
就是告诉你,你本来就可以走出自己所强加以
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南迪的意思是:正因
为你们还不成熟,所以才需要社会的引导、教
育。“童年”如果被定义为人的一生中尚不成熟、
还不完美的一个阶段,那么就会失去童年本该
享有的许多乐趣与光彩,“大人”们就会用自以
为成熟、完美的标准去教育孩子。这在我们的
当前,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所谓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是拿人生中
虚无飘渺的“终点”(代表着成熟与完美)来
要求我们的孩子。当然,“低幼化”的更多的
表现形式就是远离政治,把这些事交给老成了
的政府或官员去办,而自己只消满足于吃喝玩
乐即可。一方面是在民主政体中把幸福公民“定
义为可以自由投票、消费、旅行、娱乐至死的人”;
另一方面就是在非民主国家中,“让政府的管
制进入了一个可称之为快乐产业的范畴中。这
帮助政治成为了一种‘可控景观’,让它进入国
民的客厅里,把它们变成单向信息的接收者,
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一个虚拟政治世界的俘虏,
那里承诺要放逐所有的死亡和政治苦难。”(第
42-43页)我其实在几乎所有的大型娱乐晚会
(包括春晚)上都能强烈感受到自己“被低幼化”
了的耻辱。唯一的逃避就是不看;但南迪同时
告诉我们,“低幼化”对我们时代中的暴力与
苦难已经变得如此重要,哪怕你视而不见或装
作不知道,“那么上千万人所经历过的痛苦就
将只能存活在人类的意识边缘,就像往常那样,
成为代代相传然而渐渐褪色的回忆”。(第 44
页)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梳理一下甘地的思想
以及他被刺杀的原因。
我们在电影和书本中所知道的甘地其实
与印度学者们所了解的甘地有很大的不同。从
南迪的文章中,有这么几点是较为确定的:
第一;甘地的政治建立在诸如相信灵魂
的力量、内在的声音、绝食、祈祷、非暴力、
心灵净化等具有“迷信”色彩的反抗形式上,
这使得许多人并不相信其实际上所可能取得的
效果。于是,如同清末专行暗杀活动(定点清
除)的一批英烈一样,他们甚至也相信梁启超
等人的书生意气不过是为“满酋造奴隶者也”,
于是就有了以暴抗暴、以牙还牙的暗杀行为,
而且专杀那些开明的、主张改革的满清官员,
认为正是他们在延缓着满清的灭亡,阻止着革
命的爆发。“文革”时我们大批“清官论”,认
为“清官”比“贪官”更坏,就是因为他们用
自己的清廉来为满清统治者涂脂抹粉。类似的
逻辑其实也正是行刺者高德西(Godse)在最
后一次讲话中为自己所做的辩护。
第二,南迪说,甘地本人既非保守主义者,
也非改良派人士,他只不过在用自己独特的方
式(既简单而又看起来不具有任何威胁性)来
表达自己的态度而已;但他的方式却同时威胁
到了印度主流的权威制度,这就是首先,甘地
改变了印度社会关于中心与边缘的界定:知识
分子、中产阶级不再被认为在宗教典仪上具
有更正宗、更纯粹的首要地位;相对于对意
识形态的理解,这一点与毛泽东也很近似,毛
泽东也一直认为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比工农大众
更懂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们也都并不是要“去
知识化”(毛泽东倒是真的想到过废除大学、
特别是文科大学的问题),而是要让知识分子
工农化,或者下层化,因为在甘地心目中,印
度教的真正精神就体现在社会底层的、非婆罗
门的、农民们的身上。这里面体现出一种粗糙
的、甘地式的社会正义论,今天的许多年轻人
之所以认为毛泽东时代才有社会公平,大约也
和那个时代改变或颠倒了中心与边缘的传统
界定(比如官、士、农、工、商)有关。其次,
甘地改变了印度传统文化中关于男性阳刚气质
与女性阴柔气质的界定,“他情愿透过外表脆
弱、虔信宗教、非常传统但却充满自信的强大
母亲来确立自我形象;显然,母亲是甘地所知
道的第一位非暴力不合作者,并目睹她在家族
父权的约束下采用绝食等自罚手段获取和行使
女性权力。”(第 50 页)甘地与父亲之间有敌
意,对母亲却充满敬意(这也与少年毛泽东的
情感经历近似),在印度的殖民文化中,殖民
者一般也将男权认同为统治者,女性则是服从
者。富有攻击性的男性阳刚之气让甘地感到了
内疚,而印度人格中对女性的天然惧怕(一般
来说,奉行专制的男性恰恰具有对性的恐惧,
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南迪本人就是一位
临床心理学家)又被他巧妙地转化为敬畏。在
甘地看来,荣誉普遍属于受害者,女性作为“受
害者”恰好同非入侵性、养育性、非操纵性、
非暴力性、非自我强调性结合在一起。刺杀甘
地的高德西恰恰第一,属于要被甘地边缘化
的、原来的“社会中坚”,他来自婆罗门势力最
为强大的马哈拉施特邦,认为只有自己才是能
结束英国殖民统治的社会精英,因此也就特
别忌讳具有女性气质的柔弱,希望能通过一种
惊天动地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 恰
好,南迪告诉我们,在这个密谋刺杀甘地的小
团体中,有同性恋者,有对女性产生近乎厌恶
心理的禁欲主义者,也有沉迷女色之徒,总之
这些因素也应该视为讨论甘地被杀案的另一
角度。
第三,在南迪这篇文章开始的地方,引用
了马哈德万(Mahadevan)的一段话:“恨比爱
更具备无限的共容性。爱使人的视野变得平庸
无趣,恨却使其愈加敏锐。”“爱”在我们国家
曾是一个被禁止言说和表示的的词语,那时人
们更愿意通过“恨”来证明自己的立场坚定;
但现在,当“爱”已经说滥、唱滥并充斥着我
们的周围环境(有一个电视广告竟一连说出六、
七个“爱”字)时,其效果就如前面所讨论过
的“低幼化”一样:“低幼化”对我们时代中的
暴力与苦难已经变得如此重要,哪怕你视而不
见或装作不知道,“那么上千万人所经历过的痛
苦就将只能存活在人类的意识边缘,就像往常
那样,成为代代相传然而渐渐褪色的回忆”。
重提“爱”与“恨”的问题是为了讨论甘
地的死亡与高德西的暗杀。
甘地与高德西在四个方面一致,在四个方
面不一致。一致的地方是:他们都是坚定的民

BOOK TOWN12
BO
OK
TO
WN
13年五月号 书城·二 一一 ·
族主义者,而且都认为印度的问题主要是印度
教徒的问题;他们都主张一个不可分割的自由
的印度;他们都认为苦行是政治活动的必要组
成部分,甘地的形象我们在电影中已经看过了,
其实高德西也一样过着隐士的生活,睡木板床,
冬天只穿衬衣,不嗜烟酒,终生不娶,过着严
格的独身生活,希望死后按萨拿塔那教义火化;
而且,高德西支持甘地去种姓化和实行民主政
体的主张,甚至赞美他为了与印度穆斯林团结
起来而出让某些领导权的做法。两人不一样
的地方是:高德西身上有西化的高级种姓家族
传统,其阶层曾是印度政坛的主导力量;他相
信政治是一种此消彼长的残酷游戏,像甘地
那样大讲政治伦理、灵魂力量是完全不切实际
的空想;甘地认为印度教的自救在于开放,不
再作为宗教性团体存在,而是成为一个不断容
纳新的生活方式的普世伦理的一部分,高德西
恰恰相反,认为印度教的救赎只能通过放弃
开放与宽容,走更加严密化的组织路线,通过
竞争和“自卫”来成为一个单一的社群与国家,
就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曾有过的形态一样;
而且更重要的地方在于两人对“历史”的理解
是完全不同的:甘地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的观念),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对历史作
出今天所需要的解释,所以他主张宽容,甚至
想通过忘却来弥合过去的痛苦;而高德西则
把历史视为真实事件的时序排列,穆斯林与基
督徒对印度的上千年统治是无法忘却的,印度
教徒的耻辱只能用鲜血得到洗刷。
必须承认,这四个一致与四个不一致对
我们的今天来说都很现实,而甘地与高德西
就如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某个人物一样,特别是
当我们就某些问题展开辩论时,他们的立场以
及所依据的理论其实都在我们的“同情式理解”
之中。对甘地,我们容得下他的作为(苦行主
义)却容不下他的思想(普世价值),对高德西,
我们容不下他的作为(暴力行为)却容得下他
的思想(立场坚定)。当然,对他们二人来说,
最后的结果依然是高德西开枪打死了甘地,然
后昂然走上绞架。
中国自古以来暗杀者和被暗杀者不计其
数,从《史记·刺客列传》开始记述其人其事,
一直到清末民初,到抗战时期,吴樾、徐锡麟、
汪精卫,还有遭暗杀的陈英士、廖仲恺、宋教
仁,但我们有如南迪这样分析过他们个人的政
治见解、心理背景吗?我们总不能单以好坏对
错论处,然后就说些“此其义或成或无成,然
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之类的话就打发了吧?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确
实既明又不明。
有些细节也很有意义:一是甘地在生命
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已经看到了印度教徒与
穆斯林教徒的水火不容,这与他全部的灵魂(反
对将印度教与伊斯兰教视为两种敌对的文化与
教义)是完全无法相容的,同时也说明了他的
宽容、理解、祷告、政治伦理、和平主义、心
灵力量的破产,于是他想到了死,觉得只有死
亡才能成就他最后的胜利,使他成为真正的“圣
雄”,伴随着自己健康的急剧恶化,他似乎已
经预感到了被谋死就是自己最好的结局。而高
德西,在向甘地开枪前先向他深鞠一躬,感谢
他对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连开四枪后并不逃
走,而是大声喊来警察。甘地死后成为全体印
度人心目中无可替代的“圣雄”,但这并不妨碍
高德西的著作《暗杀甘地:我所但当的任务》
和《为六亿五千万人牺牲》成为了所有想了解
印度的政治与文化之关系的必读书籍。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就是甘地的普世政治
道德(非暴力,不抵抗)也有一个具体的、恶
名昭著的个案,这就是他曾建议欧洲的犹太人
以非暴力的方式消极抵抗希特勒。南迪在一
个注释中解释了这一点:“当然,甘地专注的
是人类的常态而非异态。”(参见注释 20)但
到底什么是政治的或道德的常态,什么又是政
治的或道德的异态,我们各自都是凭什么做出
了各自的判断,同时又相信这一判断本身就是
“常态”或“异态”的呢?
五、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
(Tejaswini Niranjana)
尼南贾纳是这八位印度学者中最年轻的
一位,生于一九五八年,她曾在孟买大学获英
语与美学硕士,但她说,与第三世界社会之间
的真实差异的接触,“迫使我们把注意力从美
学转向政治的维度”,“让我们不在诗学的形式
中,而是在文化、政治和历史的领域中寻找一
致和不一致”(第 45 页)。
但她同时质疑“第三世界”这一概念,质
疑任何意义上的“比较学”,如“比较文学”、“比
较哲学”等等,因为所谓的“不发达”或“欠
发达”,到底是相对于谁而言的?就是“民主”、
“现代性”这些概念,是不是也专指那些在“第
三世界”中少数有资格成为“公民”的人而保
留的一个领域?而且,任何“比较”都预设了“共
通的人性”,相信世界人民在根本上是同一的
或趋向于同一的,而这其实来自于某种居高临
下的论断;而这一论断,从一开始就把“第三
世界”放在了较低的层次上。也许《共产党宣言》
中的一段关于“乡村屈服于城市、未开化和半
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
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
论述(见《马恩选集》第一卷)就为这一论断
作出了最好的注解。问题是:破除了欧洲中心
主义,除了第三世界的空间,我们又能到哪里
去寻找思想的资源?这大约也就是陈光兴先生
主编十年《亚洲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e
Studies: Movement)的一个初衷。尼南贾纳女
士说,我不认为我们能够消除第一世界的知识
结构或者可以完全不以“西方”为中介就能生
产出我们自身的主体性,但我们必须承认在我
们的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非西方
的政治空间和文化交叉,这种承认将导致我们
重写自身的历史。
尼南贾纳是在重写自身历史这一视角下讨
论翻译问题的,与翻译有关的两个至关重要的
概念就是实在(reality)与再现(representation);
她大量引用德里达、本雅明、阿多诺、列维纳
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Niranjana)在 2010
年第八届上海双年展“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
对话”作演讲

BOOK TOWN14
BO
OK
TO
WN
1�年五月号 书城·二 一一 ·
斯、艾略特、福柯等人的论述来质疑西方哲学
中的“实在”与“再现”这两个概念,认为“实
在”(把历史的东西表现为自然的东西)与“再
现”(殖民的权力关系在新殖民的状态下被再
生出来)其实不过就是“增益”(more)或添补
(supplement)的代名词。一八三五年三月七日,
英语取代了波斯语,于是贸易、行政机构、权
力、道德观和生活趣味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
语言所到之处,一个完整的“问题系”(涉及
到一个“场”中的一组问题,一种整体上的运
动、扰乱和置换,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跨语际
的过程)就被建立起来。作为个案,她以威
廉·琼斯(William Jones )和詹姆斯·穆勒
(James Mill)为例,告诉了我们他们笔下的印
度史与印度人是怎么一回事:英国人的到来导
致了印度人自家法律的正确贯彻和实施,结束
了“专制的”暴力和恐惧,而印度人本身就有
着不诚实、撒谎、背信弃义和惟利是图的品行
(第 79、81页)等等;而印度人随着对英语的
掌握与习惯,也就“自我殖民化”了。这里她
引用了葛兰西的观点,说明国家权力的统治是
一回事,而市民社会则是通过“共识”(consent)
来巩固权利,凭借意识形态的制造来确保“统
识”的(Its hegemony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ideology in civil society ,where it secures
its power through consent,这里的 power 应
译为“权力”而不是“权利”)。在后面的注释中,
尼南贾纳认为用“宰制”(domination)比用“统
识”(hegemony)更好,因为“统识”暗含着
所有阶层的同意认可(consent)。其实,“宰制”
也好,“统识”也好,总之说明了“实在”与“再
现”其实都是殖民者用语言制造出来的;既然
是语言的制造,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谴责制造者,
而应该看到其具有更多的、超出于制造者本人
意愿的“效应”。这里所涉及的就是一个当代
哲学解释学的话题了。尼南贾纳的一个特点就
是充分利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方法,从如
何理解翻译入手来“解构”西方自身的“实在”
与“再现”。因为历史观与翻译观密不可分(想
想我们自身的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翻译),
而无论是历史还是翻译,又都与先在、在场、
本原、本身这些概念密不可分;按照她的观点,
所有的抗争并不是为了“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
过来”,而是突出混杂性(hybridity)这一概念,
“把混杂性视为在指向一种新的翻译实践的同
时又颠覆了本质主义阅读模式的一种后殖民理
论的标志。”(第 109页)
我个人更感兴趣的还是她的《为什么文化
重要:重新思考女性主义政治的语言》这篇
短文。
文化对女性主义的重要是一个“实地性”
(女性实际所在地)的问题;相对于亚洲的女
性而言,政治的现实(我的一位同事张念博士
专门讨论了国家建构、革命、解放、平等、妇
道、忠诚、信任、爱、家庭、承认等观念的确
立与性别政治之间的关系)与对女性的界定密
不可分,而且它确实不大好用我们习惯了的“阶
级”这一概念加以论说。尼南贾纳认为,与西
方社会把女性主义问题纳入西方的自然与文化
的二分法(身体和女性特有的自然生殖功能使
女性从属于文化的思维功能,康德就表现得很
明显)不同,在亚洲,女性在历史上一直就被
视为文化的一部分,在印度,sanskriti 这个词
就是对英语“文化”这个词的翻译,而印度人
则用这个词来标识规范性的女性特质。在我们
中国,更强调人类文化与天命自然的合一,天
地、阴阳、乾坤、刚柔二者之间“其为物不贰,
则其生物不测。”(荀子),读《周易》,充满了
刚柔交错,柔来文刚之类的话,尽管所有这一
切并不一定与如何理解、处理社会现实生活中
的男女关系有关,但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就是
要把两种相反的力量合二为一。在这一意义上,
女性在非西方的文化讨论中确实占有核心的地
位,尼南贾纳甚至认为“女性越来越被看作‘传
统’与‘文化’的宝库”(第 123 页);对女性
主义文化的重视,不仅可以开启亚洲之多种现
代性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政治词汇如何变迁
以及如何翻译的问题。
在印度,有过一个声势浩大的“粉红内衣
运动”:二○○九年一月末,一个新成立的罗
摩神之军宣告他们将袭击参与二月十四日情人
节约会的青年男女;后来,他们果然袭击了一
家酒吧并殴打、驱逐了在那里参加活动的女性。
“情人节”显然是一个外来的节日,袭击者也
有许多义正词严的道理可讲(在我们这里是建
议用“七夕节”取代“情人节”),但就是这样
一件事,激发了印度全国女性的强烈抗议,并
由此发起了一个把粉红内衣寄给罗摩神之军的
运动;通过 Facebook 网,大约四万点击者都
在询问“如何寄上我的内衣?”;而收集中心则
遍及印度,他们把收集到的内衣扔到指定地点
以递送给罗摩军在芒格洛尔的总部。这次活动
的一个组织者说:我们只是想让那些看起来
强大无比的罗摩军男人显得荒谬而已。尼南贾
纳说,这次抗议的风格在印度女性主义政治
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绝大多数女性主义群体
都表示支持粉红色内衣运动和情人节的联盟,
而且许多从未庆祝过情人节的人也在那一天穿
上了粉红色的衣服,于是也就使“粉红色内衣”
进入了公共词汇,标志着印度女性主义运动在
话语方式上的一种转变:性别化的意向如何
表达、性与文化差异之间有着怎样的论述空
间、如何为被剥夺了基本话语权力的女性说话,
等等,所有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又超越了东西
方之别,彰显出的是某种性别政治中隐性与显
性之间的关系。写到这里,收到了陈光兴先生
从台湾寄来的大作《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
(台湾行人文化实验室,2011 年版),作者在“后
序”中也谈到了类似的问题,其中特别重要的
就是社会的阶序格局;而在这一格局中,最突
出、最显眼的又是性别格局。作者引用刘人鹏
的一段关于当男/女、阴/阳、动/静、上/下
的配置关系系之于乾/坤、天/地时,人间秩
序便被定义为宇宙自然的秩序。这个秩序,我
们可以用杜蒙(Louis Dumont)的阶序格局理
解。就是说,在高层次上,阴阳的统一是互补、
和谐的,被包含在太极的整体秩序当中;但是
在低层次上,阳高于阴,亦即阳支配、统治、
包含了阴;更重要的是,阴与太极整体的关系
不同于阳与整体的关系。就以《周易》中的“刚
柔交错,柔来文刚”来讲,金景芳老先生就说了,
它讲的是“阳爻是本是实是质,由阴来了加以
文饰。因为有柔来文饰,所以就变成亨了。”(《周
易讲座》,广西市褡出版社年半,第 188 页)
于是“去帝国”在这里也就有了“去男权”
(大男子主义)、“去汉权”(大汉族主义)、“去
×权”(大×权主义)等多种含义。
我想,这大约也就是尼南贾纳女士本来
的意思。